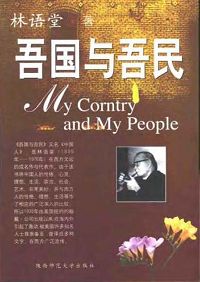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 作者:胡辛-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六神无主,胸臆间翻江倒海。是的,他还清晰地记得赤珠岭的冬夜,她没有欺骗他,“我说!我说!我曾是别人的妻子!我至今也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那撕心裂肺的喊叫声已烙刻进他的脑海。可是!可是!太子的情人有两只拖油瓶!还有一个婆母!这是不可思议的荒唐!滑天下之大稽!贻笑大方!
死一般的沉默,夜雨敲伞分外凄凉。她卑微地伛着背,心被掏空了般地难受,她还在等待,希望他说一句两句,哪怕是言不由衷的惋惜。可是,她绝望了。自尊支撑着自卑,她一步一步离开了这个男子。
一切就这样结束了。
“回来!谁叫你走的?”他狂怒地追了上来,一只手粗暴地扳过她的肩头,她竟软瘫地跌进他的怀中,失声恸哭!
“这是不可能的!凭什么你想断就断?!”被捉弄被羞辱的愤怒燃烧着他,是续是断为什么总由这个女子操纵主动?他毕竟是个有血性的男子。
她被他的愤怒震住了,抽抽答答求饶:“我……不能不告诉你呀……”
他的心软了下来,有缕缕幽香沁入肺腑,他又嗅着了她特有的清芬,他摩挲着她的秀发喃喃道:“这是不可能的。”他不能舍弃她,哪能刚开始就煞尾呢?
“那你说……该怎么办……”怎么办,自是指儿子与婆母。唉,她原来无法抗拒他,只不过是来讨“圣旨”?
“怎么办?唉,你决定好了。”他停了停,“我说过,我,不在乎的。”
渐渐地她止住了缀泣,他拥着这个处境维艰的弱女子,她依偎着这个总算可靠的强男子,雨巷又只属于他与她。
他却轻轻推开了她:“我得马上去情报室,任锡章出事了。”
就又回到了丑恶的现实中。
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十七 团圆的梦破碎得这么快
十七 团圆的梦破碎得这么快
任锡章,他是痛心疾首、恨其不争!
这二十出头的小九江,赤珠岭青干班学员出身,聪颖精干,又小有背景——其兄是战区的少将处长,交游颇广。结业后蒋经国调他到赣州国民经济对日绝交委员会当干事,并兼“仇货检查队队长”,也就是查禁各大商号店铺的日本货。谁知这任大队长竟敢贪赃枉法,案情直接捅到军统戴笠处!其时正是蒋经国建设新赣南、百废待兴、政通人和之际,万万没想到这得意门生,宠臣爱将居然给自己抹黑!不严惩,岂不让一粒耗子屎,坏掉了一锅羹!任锡章便下了大狱,钉了脚镣,不许家庭探视,赣州城中“任锡章即判死刑”已沸沸扬扬传播开。
蒋经国的左右:秘书黄中美、周百皆、高理文,特务室主任杨明,专署军法处军法官蒋善初等便出面讲情。
蒋经国却是一言不发,锁着眉头,咬肌拧成了麻花。只听门外一声“报告”,机要员推门而入,递给落经国两封加急电报。
一封是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拍来的:请将任案解送省保军法处审理”;
一封是军委会政治部陈诚部长打来的:“请将任案解送战区长官部军法处处理”。
蒋经国不看犹可,一看勃然大怒!一条血性汉子,又自视有扭转乾坤之魄力,平生最恨受人箝制当傀儡却又往往不得不受人挟持做木偶!他一拳砸在茶几上:“他妈的!任锡章非杀不可!”
就都不敢出声,高理文却不失诤友本色:“请你三思而行,万万不可意气用事!”
“胡说!”他脸红脖子粗,失去了自恃。两封急电想必是任锡章的哥哥四出求援的结果,可这岂不更扩大了任案的影响?!
“怎么叫胡说?!……”高理文也面红耳赤,据理力争,慌得众人敢忙劝阻,遂不欢而散。
只有蒋善初晚八点遵嘱又来到东院接任案的批示。
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章亚若出来看了几次,蒋善初也徘徊不已,但都不敢去惊扰蒋经国,只是隐约可闻办公室里翻阅案卷的沙沙声、踱来踱去的脚步声和沉重的长吁短叹。或许,任锡章的处置会有一线转机?
凌晨三点,蒋经国一声沙哑的呼唤:“蒋军法官——”
等得心焦的蒋善初整整衣冠应声进去,见着案卷中的朱批:“死刑”,蒋善初的眼珠子便直勾勾了。
“执行以后好好安葬。”蒋经国又叹息一声:“对他的妻室儿子要妥善安排。”这才疲惫地挥挥手。蒋善初拿了案卷退出,正撞见章亚若端着热腾腾的酒糟鸡蛋欲送进去,亚若忙问:“怎样?”
蒋善初摇摇头:“枪决。立即执行。”
亚若急了,进门只见蒋经国在这凌晨三点却戴着一幅墨镜!森森然透着阴寒之气。
她将碗放到办公桌上,顾不得斟酌字句,冲口而出:“不能判个‘死缓’吗?他是你的学生,只有二十一岁啊。”
“你懂个屁!”他又一拳砸在办公桌上,歇斯底里地跳了起来,碗也颤了起来,汤水淋漓桌上。
泪水如决堤之水涌出!可她不示弱地盯着这个操着生杀大权的男子。
他却透过墨镜读懂了她目光中的全部内容。他并非铁石心肠冷酷无情之辈,何尝不念师生情上下级之谊?他又何尝没动恻隐之心可怜跪在脚下的任的妻儿?他理解失夫之难丧父之痛。既然朝野皆知、拭目以待,他不挥泪斩这不争气的任某,何以平民愤?何以还击流言?何以向天下昭示他的“清廉公正”,“执法如山”呢?
默默流了许久泪水的章亚若只有让步,她拿起抹布,揩净桌上的汤汁,轻声说:“快吃了吧,都凉啦。”
他摇摇头,却一把扼住她的手腕,手心滚烫。
“哦,葛洛已平安离开了赣南。”蒋经国转换话题。
于是,他与她的心头都宽松了许多。
忽然,他像想起了什么,或许是急于弥补刚才凶暴的言行,他从抽屉里取出一叠钱,拉过她的手,欲放于手心:“喏,带给他们吧,他们都安排好了吧?”
像被蛇咬了般,她的手一甩,跳了开来:“不!我不要!”
钱便撒了一地。他皱起了眉头,自嘲般幽默一句:“这些钱可都是干净的。”
她冲动了:“我拿了可就不干净啦!我有自己挣的干净的钱!我养得起他们!”
“你怎么啦?”他站起来走近她,很有些不解。
泪水又冲缺了堤坝。她恼恨他突然将话题转到“他们”!这种时候这种场合这种氛围!像从火海中拽出又坠入冰河,像从死神中解脱又身陷黑夜的坟冢堆中,人生的苦难本来就多,为什么还要把这样那样不同滋味的苦难混作一锅煮呢?
这回,他投降了。他忙手忙脚给她拿毛巾擦泪,又终于取下了墨镜,求饶似地说:“我知道,是我不好。”
眼白又布满了血丝,但很善良,充满歉疚和不安。
她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她俯身将钞票一张张拾起,蒋经国又从口袋里掏出一纸证明:“你看,差点忘了。这是我介绍他们进难民小学插班的证明。”
她将钱放回抽屉,接过证明信:“谢谢。”
他又长叹一声:“唉,我知道,这太难为你,太难为他们了。”
她安顿他在值班室打个盹,便悄悄地离了公署。
第一抹曙色,将城墙脚下那片临时凑合搭起的乱七八糟的破烂芦棚夸张地抹上了旖旎的亮色,有炊烟袅袅、鸡鸣狗叫、起早担水的人影,急急上路的鸡公车叽嘎作响……五里亭刑场的热闹和枪声,并不惊扰他们贫困的生活。
她来到了这里。她的婆母执拗地带着孙儿住进了这里,离得她远远的,为她省钱为她减纷扰,却不知更添了她的负罪感!
她听见了嗡嗡的纺车声,不知为什么她竟做贼般蹑手蹑脚绕到西边的小窗前,偷偷将棚内的一切来张望。
罗纱帐垂下,她的一对儿子睡得正香!床榻前,她的婆母正摇着纺车纺棉线。硬朗的身板、黝黑的肤色、缀着补丁的衣裤,婆母与贫民窟的老妇全无二致!只有那依旧梳得齐整的花白的发髻、发髻上插着的碧玉簪,还有那标准的三寸金莲、裹着金莲的做工精细的绣花鞋,依稀可寻当年富家媳妇的影子吧?
就是这么一双小脚,拖着一对孙儿逃离了沦陷区,颠簸了千里路终与她得以团圆!
可是,团圆的梦破碎得这么快!就在婆孙到来的当夜……
“姆妈、婆母……你们还没睡?”她在雨地里蜘蹰了很久很久才回家,母亲和婆母却都在小房间里等着她。两个老人红眼红鼻,像是恸哭过,她不禁心惊肉跳。可转而一想,两个亲家母原本是闺中好友,离乱一载,叙旧话别,自会伤心落泪的。
“懋李,这年月女人要做上一份事真不容易噢——”婆母关切地开了口。
“哦,忙是忙,也不是每夜都要加班的,今夜真不凑巧——”她强颜欢笑,今晚唐突离家这么久,实在不合情理。
“懋李,婆母——她有话对你说,”章老太太刚说一句,又抽出腋下的手绢揩眼泪,那手绢,己像水洗过一般。“懋李,我,我把这一年的事……都实话相告你婆母了。”
“姆妈——”她睁大了眼,恐慌地看着母亲:是母亲出卖了她?还是母亲急于让她解脱?
“懋李,你娘和我做女崽时就结拜了姐妹,彼此知心知意。婆也从来把你当亲生的女崽看待,婆晓得你的艰难,婆也是……年轻轻就守寡到今的……女人,婆不愿你再走一遍这样的路……”
“懋李,你不要为难,我跟你娘商量过了,我还是带着大衍细衍另住别处——”
“大衍细衍长大了,怪惹眼的,不往来怕也不是办法,要不,”婆母这才哽咽了,“就让他们喊你……三姨?”
晴天霹坜!五雷轰顶。
她木然跪倒在两位老人之间。欲哭无泪,欲辨无词。
婆母就带着孙儿住进了这里,待一切安顿好,婆母才让她来看他们。
她不敢喊,不敢控门,将准备好的生活费悄悄从门缝底下塞了进去。
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十八 昔日的章懋李与今日的章亚若
十八 昔日的章懋李与今日的章亚若
亚若病了。虽说一般的伤风感冒,可因为心病连夜失眠,她病倒了。
人烧得昏沉沉的,可脑细胞异常兴奋,连阖下眼的念头都没有。下午蒋经国给她带来了这捧杜鹃花,见她烧得不低,又嘱专署查医师来给她打了一针退烧催眠,她却仍处于亢奋状态。
昔日的章懋李与今日的章亚若撕掳纠缠崩裂抗衡……
噼哩啪啦硝烟弥漫,爆竹声声中筷子巷又迎来了一个继往开来的喜庆日子——唐家婆婆娶媳妇啦!
披着彩带的几辆橡皮车到了,喜娘扶出个千娇百态的新娘子:
——白色的缎子旗袍长至脚踝,却短袖露臂,脚上还着一双白色的高跟皮鞋!最奇的是那一头黑鸦似的秀发上竟箍着薄若蝉翼、涌如浮云拖曳至地的白色婚纱!两个漂亮的小女崽乐呵呵地跟在后面托起才不至于拖地!
白皙清癯的新郎官却是老式打扮,颀长瘦弱的身躯着一袭黑华丝葛长袍马褂,脚着一双千层底黑布鞋,左胸襟别一朵硕大红花,正是东方式儒雅书生风范。轻盈的白色新娘子挽着他的手臂,好像一个早早地进人了酷夏,一个还迟疑地留在寒冬。
拜堂改良为三鞠躬,新郎新娘对鞠躬时,她见新郎紧张得汗在脸上淌成了无数小沟,她噗哧笑出了声。
她实在太小——十五岁的没成熟的小懋李。
他呢,大她三岁,空有雄赳赳名字唐英刚。
筷子巷快子,第二年她便生下儿子大衍,学名远波。婆母包下了养育孙儿,因为不放心这十六岁的女崽,只要她喂几顿奶,于是她除了烙刻下新生命从母体分裂时幸福又恐怖的巨痛外,她不过是一个懵懂的小母亲。
婆母从心眼里疼她,婆母守寡拉扯大儿子英刚和英武,就把她这长媳当女待,祖孙三代倒也洽和。白天,她或看书作诗绘画,或拨弄月琴;也绣花结绒线做衣服,也下厨做几样小菜;昔时女友来邀,也会嘻嘻哈哈上街瞎逛;活得闲适也无聊。黄昏倚门,翘首盼在监狱中做事的夫君归家,然而,唐英刚沉默寡言,似惜话如金。饭后,小夫妻相守一室,唐英刚就摇着缀有流苏的洞萧,呜呜咽咽吹上一阵,吹得满屋的凄凉萧瑟,她就晃晃他的手臂,放下箫,他又到桌前,铺开白纸,让妻研墨,自己抄录几首古诗词,字是一丝不苟的正楷;偶也自作一首,格律无可挑剔,吟来却味如嚼蜡;偶也什么都不做,只是静静地凝视娇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