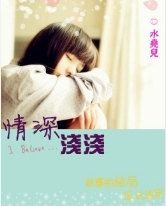深浅-第4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西:缺乏理性。《芳名》里面常常是一段感性,一段理性,这些东西产生了……
简:角度的变化?
西:互相破,你会发现,《芳名》里的〃你〃,实际上不是一个具体的人,我把她写得好像是一个女人,其实是以往的经验的一个集合…… 实际上其中有一节写的是我妈,〃要是〃什么的,我记不清了,是我母亲给我讲的她小时候的事情…… 那里面,有些描述,都只是一般性的描述。还没有特别的……
简:特别的也转化成了一般性的。因为我们对你这方面都知之甚少啊,所以这首诗一出来,朋友们都诡秘地微笑着…… 就这首诗而言,我是特别喜欢,也可能因为我没有受到太多的形式训练,所以我读作品的时候,任何一件作品,我要求一种能够跳出形式感的品质……
西:这个我以前没有意识到,92年以后慢慢意识到,就是从此不再想写一首好诗,以前总想着写一首好诗,句子要怎么样,结构要怎么样,节奏要怎么样……《芳名》这首诗,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太喜欢。一个是后头拖得太长了,另外一个,我听到一些说法,后半部脆弱感出现了,他们觉得我应该不脆弱,嗨,别人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反正我写完了,就那样!
简:当代文学里还没有一件作品这么写到一个女性形象,如果帕斯的说法是真实的,文学本来就跟色欲有关,那么一个时代的文学没有创造出有力的女性形象,应该是件丢脸的事。我那一天还跟顾晓阳说起这事,他的小说《洛杉矶蜂鸟》里写到了一个活灵活现的坏女人,我说写好一个坏女人就是一个好作家了,但是写好一个好女人仍然不容易,只有大师才能干那种活儿,比如托尔斯泰啊,陀思妥耶夫斯基呵。
西:你这话说得很好。而且这种好女人越来越不好写了,经过19世纪的正面写作以后,到20世纪是越来越不好写。你看本世纪的文学里出现的都是坏女人,从洛丽塔;到巴塞尔姆笔下的特别枯燥乏味的白雪公主……
简:可是《日瓦戈医生》中的拉拉……
西:《日瓦戈医生》不一样,那是在社会主义的环境当中,俄国的古典主义,他继承了19世纪俄国文学的传统……好女人是越来越不好写了,这的确是个问题,一写就写得非常俗气,已经不知道怎样着笔了。我记得张爱玲说过我不喜欢张爱玲这个人,但是我喜欢她说过的一句话她说好人都愿意听坏人的故事,从来没有人愿意听好人的故事。还是回到我们的话题,一般来说,我会处理我的个人经验,有时候也会露出一个角来,但从来不会太多。另外一个,个人经验也应该区分,有些是可说的,有些是不可说的,比如有些有审美意义,有些则没有。这时候,除了个人经验之外,还有对文学本身的尊重问题。
简:对,上次我与老车的谈话也涉及了这个问题,一个表述你还是得尊重公众原则。
西:我其它的个人经验就特简单了,就是从学校到学校……
您所在的位置:登陆网站>深浅>正文回目录
视野之内(四)
作者: 西 川
简:你大学毕业那年,有一次漫游的经历,这个后来进入了你的作品吗?
西:《哈尔盖》就是。还有一个我现在看来不太成功的作品,就是《远游》。这个《远游》不是直接写的漫游,主要是指精神上的,跟那次具体的远游好像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具体的远游使我一下子摆脱了学生腔,这是一个收获。我的参考系就变得非常大了,衡量一个作品的好坏就不止是其它的作品,可能一棵树、一座建筑、一片景色都可以成为作品的比照物。这里我跟你说一个经验。以前我写过一首跟晚清有关的诗,有一天夜里,一点来钟的时候,我从母亲那里回自己住处,路过天安门,我去了午门前面,当时就我一个人,一个大宅子,中国最大的大地主的宅子,周围黑黢黢的没有一点声音,我站在那里立刻想起了我那首写晚清的诗,就自己默诵了一遍,之后我就觉得那首诗的第二节写得还不错,第一节和第三节都写得不好。我之所以有这种感觉完全是因为那个建筑本身。在这样一个建筑面前,你读这首诗,读到第二节你一点都不心虚,而前头的和后头的你都会觉得不配在这儿读,所以我说远游对我的写作参考系起了作用,不仅仅是文本的参考系,还有自然界景观、人文景观对写作质量的压力。我记得海子当时也有这个东西,谈到他的写作标准,他说到几个文字的标准,他也说了其它的,比如说敦煌,也说了埃及的金字塔,还有其它自然或人文的景观,比如说蓝天白云。一个见过蓝天白云的人和没有见过的,写出来肯定不一样……
简:还有在玻璃上见到的……
西:对,玻璃上的反光,当然不一样。
简:你那首《母亲时代的洪水》,跟你自己的母亲真切相关吗?
西:有关系,那是我母亲跟我讲过的一件事。我母亲讲完以后,我一开始写了一首很短的诗,临时记下来些很粗糙的想法,那些东西是当时的灵感。但是慢慢地我就开始拿着这个灵感工作了,开始不断地丰富它……我不知道你的写作经验是不是这样,肯定有各种不同的工作方式,有些人是一个灵感来了,一下子就能写好,有些人是得到了一个灵感就不断地做工作……
简:我基本上也是这样,写一首短短的十四行,想法可能是几个月前的,写的时候也得忙乎一天,所以有时候常自卑自己怎么这么笨……
西:我也笨,你也别说咱们笨,我知道有些作家也是如此,比如说写了两节之后他就写不下去了,然后就放在一边,也可能过了一年再拿出来,哎,就很顺利完成了。
简:从《致敬》以后,你的诗歌中的确融入了更多的经验。但是你的作品中呈现的经验,特别不一样的是,充满了荒谬感。如果是别的诗人,比如说我自己吧,我可能会去写视觉上直接观察的东西,我愿意把它保存在作品里。但是你笔下的经验几乎都有一个……尾巴,尾巴一翘,把脑袋给缠起来了。我奇怪的是,这种荒谬感也可能非常切实,比如说《致敬》开始时,卡车上的牲口进城,它们怎么怎么难以安静,我们以为你会呈现一个它们嗷嗷乱叫的景象,但是你很快转过来了〃而它们是安静的〃这种东西产生一种很恐怖的震撼…… 就是荒诞在你后来的作品中成分越来越重……
西:首先我对荒诞有兴趣,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是非常荒诞的。这倒不是从存在主义角度所说的荒诞,就是你的现实经验。不需要读任何理论书,你就感觉到这个东西很荒谬。当然这个荒谬要往深处挖,很有意思,它实际上是思维的荒谬,因为这个世界是我们人的意志使它变成了这个样子。思维本身有荒谬的一面,比如说逻辑,为什么有的人总是犯逻辑错误? 他一旦犯逻辑错误,就意味着逻辑并不能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我把人的〃我〃分成三部分:除了逻辑我之外,还有经验我和梦我,逻辑出现裂缝的时候,就是经验我和梦我在作怪。人不可能抛弃掉经验我和梦我,必须这三部分合在一块才构成一个完整的我。我们以前在写东西的时候,尽量使自己关注逻辑我,我们害怕在写作中露怯,害怕在写作当中露出思维不过关的马脚……
简:也包括眼力不过关……
西:对,还有眼力不过关,我们害怕,但是我后来发现,如果我们关注一下别的,经验我和梦我,我们使语言符合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人生,语言本身就可能呈现这种矛盾性。另外,我还关心一个问题,以往所说的我和世界的关系,一般来讲指的是我和他的关系,我和你的关系,人们一直忽略了我和我的关系。这种我和我的关系肯定也影响到语言上的探索。我本来对这个东西没有感觉,后来我开始对语言本身稀奇古怪的一些走廊呵,通道呵,有了兴趣,我开始尝试一种矛盾的写法。比如说,我最近写了一首很短的诗,《中年》,有一句〃神,肯定了他的虚假〃,这句话就是一句矛盾的话。神,如果肯定他的虚假,那么神本身就不虚假……
简:这有点像逻辑学上那个著名的语言悖论…… 这个在你早期作品中是没有的。
西:比较少,我想与对事物看法的变化有关系。以前只看到杯子,后来看到杯子的影子。以前只写杯子,后来就必须写到杯子的影子,我甚至只写这影子,不再写杯子,就把原来那个目击的物体给让开了。这可能跟我整个观念的改变有关系。打一个比方,以前你只看到上帝的一张脸,后来你想使点坏,你想看看上帝后面长的什么样,后脑勺? 上帝的后脑勺可能也是一张脸呀!不管是什么吧,你就老想往上帝的后边绕,这种努力,跟你想把自己的写作与生活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有关系。但是有可能你绕不到上帝的身后,因为你绕不到自己的身后。我觉得这个有意思:一个人无法绕到自己的背后,永远看不到自己的后脑勺。但是在语言中是可以的,你可说我看到了我的后脑勺。所以语言有语言的现实,这种语言的现实从表面上看很荒唐,但实际上生活中有很多东西是与它对应的。所以我后来喜欢在写作中尝试这种语言的荒谬性,它与我理解的生活的荒谬有关。
您所在的位置:登陆网站>深浅>正文回目录
视野之内(六)
作者: 西 川
简:但是这种荒谬性有时候使得物体本身变得轻盈了,而不是更沉重,反而可以把握了。是这样吗?
西:因为这里面开始容纳废话。以前你恨不得你写的句句都是真理,这时你从那种句句真理的写作中退下来了,退到业余写作,准确地说,是开放的写作。退下来之后文学写作变成一件有趣的事了,别人读着它不仅有意味,还应该有趣。这时候你就开始不害怕废话了。有的人诗当中没有废话,干巴巴的,就像沙子一样,一点水分都没有,紧。后来我开始放开了,开始从某种大师的状态走了下来,不再按照大师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也很荒唐,我们中国作家一般来说读到的都是那种最成功的作品,一写东西我们就期望自己也能一下达到那种高度,所以那根筋总是绷得太紧。一旦你从这种状态中解放出来,你会发现文学还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件。
简:还要享乐?
西:的确有享乐…… 作品中容纳水分和废话也是我后来慢慢磨炼出来的。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度在哪儿,你不能满篇都是废话。实际上就是在紧当中掺上一点废话,缓和一下,我想可能跟电影或音乐相像,高潮或者快板完了以后肯定有个慢板,有个节奏感。另外还有一个东西,逼迫我不得不找到一个属于我自己的方式。写了这么些年头,我说得稍微傲慢一点,就是你背后总有一些人在跟着你,你搞出任何东西来,立刻,大家全都是,你一点辙都没有……
简:哈哈哈! 有一阵子,看到所有东西都像是西川写的……
西:这搞得我特别懊丧! 因为你费了很大的劲,你觉得应该怎么写,然后别人也这么写,因为每一个这么写的人实际都站在你的肩膀上,都会比你写得好……
简:也不亚于你?
西:一点也不亚于我……这时候我回过头想我自己,我想可能是我自己的写作里面缺乏我个人的东西……
简:不是,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我是这么想的,用这两个词,就是写作中的发现和发明是不一样的,一个认真工作的诗人必须同时做这两件事情,他必须发明一个东西去发现,因为他发现的时候得有工具,但是你发明的东西很可能你还没有怎么用,就被别人顺手抄走了……
西:对,当作工具拿走了……这搞得我真是懊丧,也逼得我不得不……
简:不断地新发明?
西:不得不自己往前跑。这也涉及我的一点隐私了,内心深处的一点东西,就是你在写作中,自己要不打倒自己,不推翻自己,别人肯定就要把你给淘汰掉。我92年写《致敬》的时候,看到别人写的跟我写的都差不多,我也并不比别人好到哪里去,那个着急呵!就有了一种自己要埋葬自己的愿望,所以就开始尝试写一种东西,也就是你一开始说的,开始有一种散文化的句式。散文化这种东西,我以前是很警惕的,后来慢慢地放松了。华滋华斯认为诗歌与散文没什么区别,当然有些人就特别较这真,比如瓦雷里。但实际上你对这问题的任何看法,全是你当时觉得合适就行,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