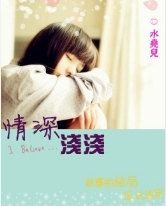深浅-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您所在的位置:登陆网站>深浅>正文回目录
想象我居住的城市(二)
作者: 西 川
上大学时我听过一位美国教授的讲座。教授的名字我忘了,他讲座的题目我也忘了,但还记得他提到过一位西方作家写的有关北京的小说。小说里讲到一个西方人爱上了皇宫里一位满族妇女;这西方人还奇异地探访过北京城地下的另一座北京城。我一直对这两个情节非常着迷,却从未找到过那位教授提及的那本小说,直到最近,我在北京东北郊花家地的一家小书店里翻到一本书。该书作者史景迁(JonathanD.Spence),英国人,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该书书名《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是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集。我因读过他讨论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的著作《天安门》,又见此书讲的是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便将此书购回。到家我才发现,早在八年前我就买过这本书,但一直未读,既然买了两本,看来这书我是非读不可了。于是谢阁兰(Victor Segalen)的名字便通过史景迁教授再次映入我的眼帘。谢阁兰,法国人,1909年至1917年三度来华,寓华时间约7年。1993年三联书店出版过他的诗集《碑》和小说《勒内·莱斯》的中译本:《碑》我读了,可《勒内·莱斯》却被我丢置一旁。这是多么可耻的粗心大意!当我因为史景迁教授对这本小说的复述而从我的书架上重新翻捡出它的时候,我想到巴西作家保罗·戈埃罗在《炼金术士》一书中所讲的故事:西班牙牧羊少年圣地亚哥被自己的梦境牵引,跨海渡洋,千辛万苦,远赴埃及寻宝;结果他发现财宝就在他的家乡,就在他出发的地方。故事绝对精彩,不是吗?或许我千寻万觅《勒内·莱斯)的过程与圣地亚哥的经历并不完全吻合,但我通过想象〃另一个北京〃而认识我居住的北京的努力,至少呼应了《炼金术士》的结论。
在谢阁兰笔下,比利时年轻人勒内·莱斯作为清廷秘密警察的头子,几次挽救过摄政王的命。他还是隆裕皇太后的情人。谢阁兰暗示,这一切有可能只是居住在北京的勒内·莱斯的幻觉。小说写得模模糊糊,奇想不断。谢阁兰竟然奇想到北京城下另有一座北京城:
北京并不像人们可以相信的那样,是一块忠诚与奸诈的角逐在其地皮表面进行的棋盘图形:北京存在着一座地下城,这地下城自有它的城堡、角楼、拐弯抹角之所、毗连邻接之处,也自有它的威胁,它的比水井更可怕的〃水平走向的井〃。……这些东西在地图上找不到。……这真是一座地下充满空穴的深邃的城市!
谢阁兰的叙事并非出神人化,但他的奇想启迪了卡尔维诺,或许他还是熟悉迷宫与噩梦的博尔赫斯的先驱。而最奇妙的是,他的奇想后来竟被林彪变成了现实(林彪不可能听说过谢阁兰的《勒内·莱斯》。难道林彪是另一个天生的谢阁兰?)。在他摔死于温都尔罕之前,他通过大搞战备而将人们派人地下,建成了一座由地道和地下掩体构成的地下的北京。那时我还是小孩儿,一听见警报响起便满怀着对苏联修正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仇恨奔向防空洞。在地道或地下掩体中,我想象苏修或美帝的导弹、原子弹在我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炸开了花。当我怀着想象的仇恨长大成人,那些地下设施的一部分变成了地下商场;当我结束了我被偏头疼折磨的青春期,那些地下设施的另一部分变成了秘密妓院。因此,北京的确存在着另一个北京,是老舍那类人所不曾见过的,就像这世界上存在着老舍不曾见过的生活、不曾读过的诗篇。日常生活的北京还不是全部的北京。你需要想象北京,北京会满足你的想象;即使它暂时没有你所想象的东西,它也会应着你的想象长出你所想象的东西。我们都从想象中来。
多年以前一位小说家曾向我提及,中国古典文学对他来说仅仅是一个他者、一处风景,当他使用中国古典文学时,他是把它当成了类似异国情调的东西。这异国情调并不能激发他的创造力,而是赋予他足够的空间感,也就是说,本来属于时间的东西被他空间化了。不要以为口出斯言者是一位西方小说家,他恰恰是一位熟读中国古典文学的中国人。倘若我暂且抛开文化道德立场来回味一下这〃小说家言〃,那么我不得不倾向于承认这是一个行家里手的高见,尽管他也许会在台面上否认自己持有上述看法。我并不想说我认同这位小说家的〃异国情调说〃,因为文化道德立场在我是无法彻底抛弃掉的,因为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存在一些与道、与天命有关的非文学的东西,这与我眼前的北京所包涵的东西极其相似。但我同样渴望以…个〃他者〃来破坏掉我习见的北京,这〃他者〃就是我对北京的想象。它不仅应带给我空间感、也应带给我历史感:一座幽灵与活人混居的城市比一座被行尸走肉占满的城市更抒情;一座与其地下城市相对称的城市才适于精神驻足。让我走得再远一点儿:或许除了北京和北京之下的北京,还有…座北京之上的北京。
您所在的位置:登陆网站>深浅>正文回目录
想象我居住的城市(三)
作者: 西 川
三
即使我们只谈论地面上的北京,我要说,它依然是一个想象的产物。史称金主完颜亮攻破北宋首都汴梁之后,悉辇其珠宝于此,故所有宫殿规制,均据汴都仿造(金故都方位与今日的北京并不完全吻合)。这种一座城市模仿另一座城市以便人们想象那被模仿的城市的情况,不仅存在于金宋之际:清代山西平遥以票号发际之后,金融家们并没有同时发展他们资产阶级的审美趣味,而是根据自己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把平遥翻建成了一座地主阶级的小北京。
如果北京的规制模仿的是汴梁,那么汴梁又是模仿的那儿?是金陵?是长安?如此类推,金陵、长安亦必有其模仿的对象。在哪儿?在地上?在地下?还是在天上?卡尔维诺在其《隐形的城市》中涉及过这个问题,但我们还是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寻找答案吧。(渊鉴类涵)卷三三二引{公羊传):〃京师,天子之居也。师者,众也;京者,大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又引《左传):〃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这句话让我想起北京中轴线上的空宅子。)中国人这种对于首都作为一座城市的传统定义实际上也是对于秩序、等级、仪式、体制、习惯、法律的确认,由此而产出的语言、精神生活方式、文化产品风格等必然不同于西方城市文明所产出的东西。因此,说到底,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其规制追本溯源是来自中国人的大脑,来自意识形态;这是一座意识形态之城。它可能适于观看,适于仪仗队走正步,适于皇家车马招摇过市,但却不像那些自然生长的城市适于居住。这不是一座自然的城市。在一个标榜〃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国家,这是一件说怪不怪,说不怪也怪的事情。
(说到北京不是一座自然的城市,我们还可以提及元、明定都北京的原因:要么为了西望大漠、南镇九州,要么为了更有效地抗击蒙古人南袭,并进一步控制东北。是中国的政治、军事版图决定了北京作为首都的资格。此外,从地理上说,北京远离水源。据走南闯北的诗人、数学家蔡天新讲,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的首都没有自然河流穿过人工开凿的另说:一个就是中国的北京,另一个是墨西哥的墨西哥城。由于地理位置,北京还常被来自阿尔泰山脉、途经内蒙古额济纳的冷空气所携来的沙尘暴搅得天昏地暗。但这类具体的历史、政治、地理问题我们可以留在其它文章中讨论。)
既然北京来自中国人的大脑,来自意识形态,既然北京不是
一座自然生长出来的城市,那么它就是一座人工之城,就像使用人工语言的和合本《圣经》,就像绢花、绢人、象牙球、白玉苦瓜、磨漆屏风、掐丝珐琅耳挖勺。在这一点上它似乎呼应了拜占廷帝国对于工艺美术的热爱。而欧洲的罗可可艺术风格从中国人的艺术品味中获得启迪就不足为奇了。北京的人工色彩最醒目地见诸其街道的规划。当年马可·波罗记录下的元大都虽然并不完全等同于今天的北京,但其形貌实在与今天的北京大同小异:
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由街道远望彼门也……全城中划地为方形,划线整齐,建筑官舍……
全城地面规模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宣样一座城市显然有违管子的教导:〃凡立国都……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无论是马可·波罗还是谢阁兰,都不了解北京之所以是北京的意识形态根由。他们都被这不同于西方城市的富于工艺之美的人工之城迷住了,他们甚至还在这人工之城的基础上各自捏造出另一座北京。他们都没能解开他们头脑中有关北京的谜团,而他们的功劳恰恰在于
他们的失败之处,也就是说,他们扩大了有关北京的谜团。但我指出这一点不是要否定他们谬误百出的观察、想象和猜测:在今天这样一个土洋结合的时代,他们的工作或许可以成为我们展开想象的出发点。
初到北京的人很容易注意到北京这横平竖直的、气派非凡的、宽阔舒朗的皇家大道、并且很容易在这街道风格与北京人的性格、北京人的道德观念、北京人的文化产品之间建立起类比关系。他们往往不自觉地成为专制之美的拥护者,并且能够感受到创造历史的冲动。成都诗人万夏初到北京时,面对这皇家大道曾经从〃气〃的角度发出过〃三国演义〃式的感慨:北京是天气散,四川是地气聚,而江浙是水气浮。大将皆出在蜀地,可统一中国的还是由魏而晋的北方。他进而评述京蜀两地诗人:由于北京的气升天而散,故北京诗人虎豹行单;而四川的气落地而聚,故四川诗人鸡鸭行群。
我想是北京的皇家大道对万夏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冲撞,才使他发出这大块切割的英雄豪杰式的感慨。其实北京自有它的迷魂阵。我本人就曾在一个夜晚,在西四那一带乱七八糟的小胡同里迷路到天亮。不过,讲究规划的皇家大道确是北京不容撼动的重要特色之一。即使千百幢高楼从四合院平房的废墟上拔地而起,然不得不遵循皇家大道的历史走向。
您所在的位置:登陆网站>深浅>正文回目录
想象我居住的城市(四)
作者: 西 川
四
说到新近涌现的高楼大厦,我就不由得要表达一下我对那个具有副科级品味的北京前市委书记、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贪官污吏陈希同的厌烦。他曾经要求北京每一座新建的高楼上都要加一个大屋顶,以体现现代化北京的古都风貌。这大概也算是个奇思妙想。于是北京就建成了一大批二三十层高的平房。这些高层平房,我操,有的像《封神演义》中的摘星楼,有的像《三国演义》中的铜雀台。幸亏这地主后来被锁进了班房,新建的高楼才不必非顶个大屋顶不可。不过,我对陈希同的厌烦现在已经消去了一半。这倒不是因为他如今正在班房里练哑铃,而我又记起了与人为善、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原则。数日前,我很偶然地在创刊于1884年的《点石斋画报》中读到一幅画,画题《第一高楼),画的是美国28层高的摩天大厦和大厦使用的〃起落机器〃(电梯)。中国人居然在19世纪末就知道了摩天大厦和电梯!但由于作者没见过这两样东西,故尔凭借道听途说,外加自己的想象,把电梯画成了从楼顶屋檐下垂、挂在大厦外面的大吊篮;更妙的是那座摩天大厦,完全符合八十年后陈希同的要求:28层高楼(画面上只画出16层)加一个大屋顶这不是高层平房是什么?作者为了显示这平房之高,还用墨线勾出云带横贯楼身,整个一幅改良文人画!我由此推断陈希同有鬼魂附体,而且那鬼魂来自19世纪末。
你看,我想象我居住的城市,一半是出于主动,一半是出于被迫。除了市中心那栖居着幽灵的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空屋以及那有着历史走向的皇家大道,一个旧北京基本上已经被一个新北京所替代。我并不怀念那个旧北京,因为我从未见过那个旧北京;而那些钢筋水泥的新骨董,根本无法唤起我回到旧北京的感觉。我只是在回味〃北京〃这个专有名词时,会幽幽然获得一种历史的纵深感,我因此而领会想象的乐趣,我因此思索我的天命所在。北京,一个词汇,除了它的方位所指没有大的改变,它的政治所指、经济所指、文化所指,乃至道德所指均已大不同于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