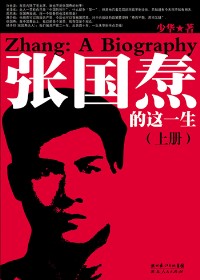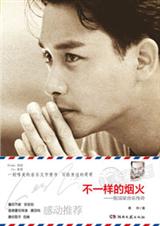张国焘传-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位姓熊的人开的茶楼,此人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同情工人运动。
紧急会议开始了。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张国焘主张立即下令复工。他说: “应当退却时,就应迅速地退却。现在这种和平式的罢工,不能对抗吴佩孚的武力压迫;大家只要细想一下,在江岸分会内,军阀们用诡计屠杀工人的经过,就可预料还会遭受到一些什么样的屠杀和镇压。为减少牺牲,保存实力以图再举起见,现在只有忍痛复工。”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72页。
但大多数与会者反对这个主张,认为应该继续罢工,直到胜利。尤其是项英,对张国焘大为不满,指责他领导不当,说: 罢工既然不能抵抗武力压迫,那又为何发动罢工?如今在武力压迫之下,又何能屈服?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争论仍然在继续。眼看已到了夜半时分,张国焘心里暗暗着急,看来用讨论的方式通过复工已是不可能了。于是,他要求停止讨论,声明以中共中央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全权代表的名义下令立即复工。他说: “这次力争工会组织自由的罢工是正确与必要的,但也犯了对情况估计不清的错误。我们没有完全估计到吴佩孚的残暴本质和他所受中外反动势力的影响之大,因而事先没有详细研究对付武力压迫的办法。现在各工会都应采取迅速而有效的步骤,通告所有罢工工人,一律复工。一切后果由我负责。至于反对意见,可以保留,将来再向上级控告我。”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72—273页。
在这种情况下,众人只能表示服从了。接着,大家的讨论转到怎样执行复工令的问题上。经过大家讨论,由张国焘亲拟了一个复工命令,这个复工令后来由湖北工团联合会作为紧急通知下发。命令说: “我们的敌人,既用这样大的压力对付我们,我们全体工友为保全元气以图报复起见,只好暂时忍痛上工……须知各人此时惟有忍痛在厂工作,才有报仇之日,才有打倒敌人之日。杀吾工界领袖林祥谦等之仇誓死必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誓死必争。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誓死必打倒。惟其如此,所以我们要忍痛复工,才有以后的种种办法。”《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1期。
会后,大家分头去通知工人。
第二天,当上班的时间到时,工人们怀着沉痛的心情,走进工厂,遵令复工。此时,驻扎在江岸车站和工会内的军队正大批出动,准备捉拿工人。当他们得知工人已领命复工后,才罢了手。
“二七”惨案之后,吴佩孚发出密令,通缉张国焘、林育南、包惠僧、项英、许白昊、杨德甫和李伯刚等,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二七”惨案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最悲惨的一页。今天,当我们重温这段历史时,仍不免有一种痛心疾首的感觉。
京汉铁路大罢工毫无疑问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一点已为大家所公认。但作为一次失败的罢工,更有着许多教训值得总结。
张国焘作为罢工的主要领导人,在罢工遭到镇压之后,能够力排众议,当机立断,下令复工,并于危急关头安排人员通知京汉路各分会,尽量将工人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这一决定是正确的。当然,这次大罢工的失败,张国焘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张国焘一直负责工运工作,由于他的推动和其他从事工人运动的同志们辛苦工作,自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全国共建立100多个工会,罢工187次,参加罢工人数30万以上。在这些罢工中,除了少数取得全部或部分胜利外,大多数都被军阀或帝国主义势力所镇压。这除了客观上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外,主观上则是由于罢工领导人,尤其是居于全国工运领导地位的张国焘等存在着盲目乐观和急躁情绪。他们不是详细周到地考虑发动罢工的时机、条件和罢工所能取得的实际效果,而是抱着急于求成的心理,希望通过工人一次又一次的罢工,使反动势力害怕和妥协,为工人阶级争得幸福和自由。事实上,每一次罢工的失败,都会在工人中产生或多或少的动摇,都会使党经受或大或小的挫折,其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张国焘虽然身为全国工运的领导者,但他毕竟是一个刚刚涉足政坛的20多岁的青年,马克思主义水平还很有限,认识水平和实际斗争经验还很差,所以在指导工运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犯错误。
“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开始走向低潮。
为了使共产国际了解中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并给予及时指示,张国焘受马林的派遣,于2月20日启程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和赤色职工国际负责人罗佐夫斯基汇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经过及中国工人运动的情况。
对于马林派张国焘去莫斯科一事,当时在海参崴的维经斯基颇有微词。他在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的报告中说: “……张国焘不知为什么被派往莫斯科去报告罢工情况。在他往返莫斯科的这两个月里,他本来最好应该呆在汉口和北京,组织工会的剩余力量。向莫斯科报告罢工的情况本来可以用书面形式,或者甚至可以从海参崴发电报,这要比张去莫斯科花费少得多,而且不会使党和工会的一位领导人在这样重要的时刻离开工作岗位。”《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页。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看,维经斯基的批评也是有道理的。
张国焘在莫斯科期间,同共产国际领导人有过具体的接触,并就有关中国的问题同他们交换过意见。当时,共产国际上上下下正在根据马林的建议,讨论国共合作应当采取的组织形式问题。对于张国焘来说,莫斯科之行的最大收获就是了解到共产国际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态度。他认为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东方部的拉狄克和萨法罗夫是左派,布哈林是中派,马林是右派。这种分歧无疑加重了张国焘后来反对马林关于党内合作主张的心理砝码。
十三 西湖论争
远东会议之后,共产国际加强了同国民党方面的联系。特别是1922年8月越飞阿道夫?越飞(1883—1927),原名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19世纪末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08年与托洛茨基在维也纳编辑《真理报》。1912年在基辅被捕,放逐西伯利亚。1917年二月革命后释放,与托洛茨基一起编辑《前进报》。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胜利后,在苏维埃政府从事外交工作。1922年至1923年,以苏俄全权代表身份来华。1927年11月自杀。来华之后,与孙中山的联系更加紧密起来。1923年1月,越飞和孙中山经过具体接触和会谈后,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这标志着苏俄与孙中山正式建立了合作关系。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尽快促成国共合作了。
关于国共合作问题,早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于中共一大后访问孙中山时,就曾提及。当时孙中山讲,可以允许在国民党内宣传共产主义。也就是说,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建立国共联合战线。马林对此甚为赞成,于是极力主张以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方式来实现国共合作。关于这一点,他是这样解释的:
我只是以我自己在爪哇伊斯兰教联盟运动中取得的经验作为依据。伊斯兰教联盟是爪哇最早的群众组织。它建于1911年,具有经济、社会和宗教混合一体的性质。它的斗争锋芒直指欧洲糖厂主对爪哇人的剥削。这个群众组织的左翼(集中在三宝垅)接受印地社会民主同盟的宣传,这个同盟是我帮助组织并使之沿着阶级斗争路线开展宣传。这种宣传在伊斯兰教联盟内部得到了强烈的支持,特别在1914—1918年的战争年代里更是如此。结果,在1918年代表大会的宣言中接受了同“罪恶的资本主义”作斗争的思想。和伊斯兰教联盟左翼的联系创造了在我们自己人领导下组织工会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是铁路工会。纯粹民族主义分子反对我们社会主义宣传的日益增长的影响,他们效法正在发展中的工联主义,建立他们自己的工会。伊斯兰教联盟这一松懈组织形式,使我们社会民主同盟的印尼人、爪哇人、马来亚人的影响迅速增长。其影响之大,甚至在军队里也建立了联合会,而这种情况还是在战时呢! 伊罗生: 《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54—255页。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马林经过与国民党领导人的接触和在中国南方的实地考察,认为把爪哇经验运用到中国是完全可以的,对此他很有信心。1922年初从中国南方返回上海后,他就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实行“党内合作”的建议。
中国共产党人对马林的建议是无法接受的。1922年4月6日,陈独秀致信维经斯基,对马林的党内合作建议提出六点反对理由:
(一) 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 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 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 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 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
(六) 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1—32页。
马林在自己的提议碰壁之后,便返回莫斯科去寻求共产国际的支持。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由于接受了共产国际二大和远东会议的有关精神,中国共产党人也开始将国共合作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大会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明确指出: “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在中国的无产阶级现状之下,我们认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而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具体步骤是: “(a)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b)运动倾向共产主义的议员在国会联络真正民主派的议员结合民主主义左派联盟。(c)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工会农民团体商人团体职教员联合会学生会妇女参政同盟团体律师公会新闻记者团体等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5—66页。这实际上是一种党外合作方式。
1922年7月初,马林回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领导人汇报了他在中国的工作和所了解到的情况。他在7月11日写给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说: “我建议我们的同志,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因为通过国民党同南方的工人和士兵取得联系要容易得多。同时,共产主义小组必须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同志们必须共同商定在国民党内应该遵循的策略。国民党的领导人告诉过我,他们愿意在国民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我们的同志拒绝这个主意。这些共产主义小组若不在组织上同国民党结合,那他们的宣传前景暗淡。”马林: 《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39页。
马林这一份关于中国国内情况的详细报告,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高度重视。共产国际执委会经过讨论,决定采纳马林的建议,并要求中共中央把驻地迁往广州。
维经斯基向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于1922年7月18日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命令。这个命令由马林带到中国。当时为了保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