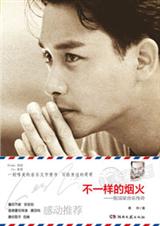戴高乐传-第5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认为,俄国将在美国之前参战,但俄美两家都是彼此参战的。您读过《我的奋斗》吗?希特勒想到了乌克兰。他抵制不了那种想要解决俄罗斯命运的欲望,这将是希特勒失败的开始。。。。。假如希特勒要来伦敦,那他早就在伦敦了。现在,只是在空中进行英国战役,所以我希望法国飞行员参加空战。总之,战争是一个可怕的而正在被解决的问题。还要将整个法兰西引向好的方面。”
6月27日,戴高乐的另一个战前朋友加斯东·帕尔维斯基直接听到了自由法兰西精神的呼唤。当时,帕尔维斯基在突尼斯服役。几周后,他抵达伦敦。苏弗莱上尉同第101飞机驾驶学校的五名同学得以来到英国。这时,抵达英国的有现役军官让·西蒙中尉,从海外法兰西学校毕业的皮埃尔·梅斯梅尔少尉,他们在马赛上了“卡波·奥尔莫号货轮”,并在船长的同谋下,在直布罗陀海峡改变了货轮的航向……6月29日,勒内·穆肖特也抵达直布罗陀,他将指挥自由法兰西空军的阿尔萨斯大队。但空军上尉德旺德弗尔却永远也到不了直布罗陀,因为他被西班牙的防空部队击落。
在抵达伦敦圣斯蒂芬大厦之后,皮埃尔·德尼采取了罗藏的化名。德尼具有大学历史教师的学衔,但他曾在国家公司的金融部门和一家银行里工作,现在则负责自由法兰西总部的财政。德尼讲述说,在他抵达英国前只有14个先令的经费。这14个先令花完了,他就不得不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了10个先令,来付发两封电报的费用。这种极端的贫困只有靠赠款来加以缓解,如一位1914年战争时期在外国军团打过仗的叙利亚老兵捐了一个钻石。只是在英国国库提供了两笔首批贷款之后,才结束了这种极端的贫困。根据丘吉尔的命令,英国国库在7月1日至8月27日期间,将2万英镑拨进了以“戴高乐将军”名义在英国银行开设的帐户。
7月24日,自由法兰西总部再次搬家,但这次是搬进了位于卡尔顿花园大街4号的美丽大厦。在未来的四年里,美丽大厦将是悬挂法兰西国旗的“总部”,其月租为850英镑。这里位于英国政府机关和俱乐部的街区中央,总部拥有七层楼和70个办公室。从此,自由法兰西有了自己的“首都”。拥有一定知名度和份量的首批法国人士到这里来,同戴高乐举行会晤。他们中间,只有唯一的一位前部长:皮埃尔·科特曾在人民阵线第一届政府里担任过空军部长。尽管科特为了最终使法兰西拥有一架轰炸机进行了努力,但右翼报纸开展了激烈的反科特的宣传运动,使整个军界不幸地迷失了方向。戴高乐被迫将科特挤走,他曾对科特承认,如果不挤走科特,那自由法兰西的首批飞机就会离自己而去。唉,除了前部长戴高乐给科特发过一封私信以外,这种对科特的不公正后来将永远没有得到完全的弥补。除了科特以外,唯一投奔自由法兰西的议员是默尔特-莫泽尔省的众议员皮埃尔-奥利维埃·拉比,他属于一个非常接近社会党的、小议会党团的成员,曾任挪威远征军团的中尉。只是到翌年1941年,才有另一位议员抵达英国,他是保尔·安迪埃,一名土地党党员。此外,还有一位很有争议的科学家和一个实验室小组的主任安德烈·拉巴而特;法国行政法院的审查官皮埃尔·迪西埃;美国电力物资公司驻欧洲办事处主任勒内·普列文,他没有跟随法英购买军用物资使团前老板让·莫内去美国;外交官和达拉第的办公室主任莫里斯·德让;芒代尔的前办公室主任安德烈·迪特朗,;伊夫·莫尔旺,化名为让·马兰,后来成为英国BBC广播公司中最著名的新闻记者之一。在大学教授或研究员中间,有来自布加勒斯特的雅克·拉赛涅,来自开罗的乔治·戈尔斯,来自墨西哥的雅克·苏斯戴尔,来自驻阿富汗考古代表团的约瑟夫·哈干,来自赫尔辛基的大使馆秘书弗朗索瓦·库莱。与此同时,有来自巴西的大小说家乔治·贝尔纳诺,这位作家已在《月光下的大公墓》一书中,抨击过资产阶级在西班牙战争时期对专制政权过分阿谀奉承,现在则通过电报宣布他对自由法兰西的支持。
然而,对戴高乐来说,此时的基本的问题是要建立一支军事力量。有时,人们还称之为“法兰西军团”。(36)成立伊始,看来它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大多数路经英国的、从敦刻尔克撤退或从挪威远征脱险的后备军,不管他们对停战或战争发展问题有什么看法,都想要同自己失散的和受到威胁的家庭团聚。总的来说,英国当局对于戴高乐能够派到营地的几位军官——他们在那里宿营——没有提供任何援助。在英国军队最高层,人们对这些以某种方式逃离部队、但现在却号召别人投奔自己的人本能地表示怀疑。人们也担心,万一突然发生入侵,这数以几千计的法国人会持什么态度。人们有时还准备相信,维希政府越过投降的界线,最终加入德国阵营。法兰西帝国的参谋长迪尔将军并不掩饰这种看法。因为存在着那么多的障碍、不理解和怀疑,所以只能是使那些试图投奔自由法兰西的人感到灰心丧气。自由法兰西的招募工作只能在挪威远征军中搞得最好。尽管贝杜阿尔将军是戴高乐的私交,但他却不愿意学戴高乐的榜样,而是相信其义务是率领其人马带到北非去。因此,在外国军团第13联队里,只有900人参加了自由法兰西军队,这些人的头头是人们所谓“蒙克拉尔”的马格兰-维纳雷中校和科尼格上尉。此外,只有来自阿尔卑斯山第六轻步兵营37人其中有6名军官。但不久后,在伦敦奥林匹克大厦这个志愿者的集合地,还迎来了不同军阶和籍贯的越狱者,他们往往是在经历异乎寻常的奇遇之后抵达英国,在热烈的气氛中受到无比热情的欢迎。未来的海军上将弗洛伊克描述过这种气氛:“每当分队进入教堂的巨大甬道时,它们都受到那些已经在场的人的致敬和欢呼,在乌拉声中还响起了嘹亮的《马赛曲》。夜里,这样的欢迎场面重复了20次,30次,直到我们累死了,跌倒在草地上,直接跌倒在地上时为止……”
法国关闭其全部边界,不让人们对新的归顺自由法兰西浪潮抱有希望。7月1日建立了“法兰西军团第一旅”,增加了568名来自法国本土或英国的青年入伍者,并在7月8日吸收了1994人,其中有101名军官。五周后,第一旅已经拥有2721人,其中123名军官。小分队开始在近东地区组建起来。在近东地区,德拉尔米拉上校即将带走好几个团,但他遭到了逮捕,后来不得不逃到巴勒斯坦;但是,殖民军的步兵、由某些军官指挥的摩洛哥骑兵、以及来自西班牙共和军的外籍军团士兵却投奔了自由法兰西,与此同时,还有驻守塞浦路斯的340人和一名上尉。这样,能在7月30日建立一个步兵营,其中包括16名军官,以及560名士官和士兵。一些以西非为基地的现役军人小组转入毗邻的英国殖民地国家,其中有洛朗-尚罗塞上尉的炮兵连。总之,在8月底,自由法兰西军队的兵力升至4500人,其中15%是外国军团士兵、摩洛哥的骑兵、黑人土著步兵,15%是来自法国本土的志愿者。最大的困难是给这些部队配备干部,以致戴高乐在1940年11月建立自由法兰西的士官生学校。这所军校先后设立在马尔维恩和位于武斯特夏尔的里布福特庄园。在1941年至1944年期间,培养了255名准尉,其中48名战死沙场。
海军的招募工作则更加困难,特别是在米尔斯克比尔事件冲击之后更是如此。(37)当时,大多数后备役军人想要返回法兰西,照顾他们的家庭。尽管这样,1940年7月15日有882人登记入伍,其中有30名军官。同时有700名水兵向英国人的压力让步,或者答应英国人的再三请求,转入英国皇家海军。在11月中旬前再有400人归顺,加强了自由法兰西海军。此外还加上172名来自亚历山大舰队的水兵,该舰队根据舰队司令、海军上将戈德弗瓦同英国人的一项协议在原地停泊不动。1940年底,自由法兰西海军的人数达到3300人,商船人数达到2100人。在此情况下,是无法为86艘战舰,150艘拖网渔船、拖轮和鱼雷快艇,以及135艘悬挂自由法兰西旗帜的货轮配备武装和法国船员的。只有三艘战舰及其船长和船组人员归顺了自由法兰西,它们是辅助巡逻艇“奥迪斯总统号”,卡巴尼埃船长的潜水艇“红宝石号”,以及后来在同年秋天被凿沉的、德罗戈船长的潜水艇“纳瓦尔号”。不管人数是那样减少,海军上将阿德米拉尔·泽里埃——戴高乐任命他为自由法兰西海军司令——卓有成效和满腔热情地领导、组织和发展了这支海军。米泽里埃具有迷人的人格魅力;他在海军中经历的动荡不定的生涯——当年,他手持武器,粉碎了1917年在黑海举行的船员暴动;当他镇压了一些被怀疑是走私和暗中投机倒把的行径时,他同军队最高层出现了纷争;凡此种种都使达尔朗让米泽里埃退休。但这并不阻碍米泽里埃表现出巨大的才干。戴高乐对此表示关切,暗中肯定他“在事关荣誉方面没有犯过任何错误”。这样,米泽里埃在10月使2艘潜水艇、4艘护卫舰和4艘驱逐舰,在年底前使2艘反鱼雷艇、3艘鱼雷艇和3艘巡逻艇先后重新驶向大海。在空军高级军官抵达英国之前,米泽里埃也受戴高乐委托,负责空军,但他手里只掌握很少的兵力。在6月15日和30日之间,有近200名飞行员——他们大多是飞行学员——投奔了英国。戴高乐恳求他们不要直接加入英国皇家空军,并对他们解释道:“到凯旋之日,200名身穿法国制服的飞行员比2000名身穿英国制服的飞行员更加有用。”7月22日,有3名自由法兰西的飞行员第一次参加对鲁尔地区的空袭。8月1日,德马尔米埃司令能够用20架飞机,建立了“第一战斗大队”,阿斯迪埃·德维拉特司令则组建了第一支法国轰炸小队。最后,在9月,自由法兰西的10名战斗机飞行员参加了英国战役。在如此弱小的自由法兰西军队里,树立了一种抗战的思想状态,并坚持到最后。对此,让-路易-克雷米厄-布里亚克一开始就在自由法兰西的军队中,他援引过贝玑的话:“革命精神”就是“想要使军队前进,并且使之高于其利益”,并把这种精神的涌现看作是“自由法兰西精神”。现任上尉、未来的将军于歇在他为步兵训练布列塔尼新兵的营地里,在个人日记中写道:“我们人数不多,我们都是志愿者,我们都是一致同意的。没有拉人的重型卡车,但大家都愿意走。”关于海军,反鱼雷艇“凯旋号”的第一任艇长、未来的海军上将维泽尔证实说:“这些人因其主动性而表现突出,在敌人轰炸朴次茅斯的枪林弹雨下表现得了不起……在晚上8时至第二天早晨6时的轰炸中,他们和衣而睡。他们在工作中发扬昂扬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振兴法兰西的思想。”
“这种移山倒海般的热情,”让-路易-克雷米厄-布里亚克还写道,“是青春的热情。自由法兰西的志愿兵的平均年龄,在陆军中是25岁,在外国军团中是27岁,在飞行员里中是23岁。”此外,他们都有其同的热情。他们对戴高乐所谓的“可耻的停战”公开表示共同的愤怒。他们对贝当没有半点宽容。没有任何力量能缓解他们对主张向敌人屈从和投降的人的极大愤慨,也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们放弃自己的不妥协立场。相反地,一切都使他们憎恨同敌人实行和解,几乎同样地憎恨妥协。他们象绝大多数法国人一样,完全一致地和不愁理解地摒弃战前的政权,而且在他们中间,自然有各种各样的法国人的观点,有的憎恨过去的人民阵线,有的自然是共和派,但他们都梦想建立一个更加纯洁和更加坚强的共和国。戴高乐使大家都感到满意,就象后来他使大多数法国人满意一样,因为恰恰是戴高乐同任何党派都没有关系,不曾受到过法国政治生活中任何事件的影响。
其实,“自由法兰西精神”是不能同对戴高乐的某种喜爱分开的。(38)有些人有时对戴高乐与他人保持距离、表面上显得冷漠和粗暴的做法表示反感,但他们非常明确地承认,这就是人们司空见惯的、那些当之无愧的领袖的性格特点,而法兰西在危难中,无疑需要这种领袖,甚于任何其他人。后来,戴高乐的崇高风格,他对敌人和维希政府进行无情斗争的号召,他那对敌人不妥协的名声,凡此种种还使自由法兰西人相信戴高乐正是他们必需的人,并且增强他们对戴高乐的尊敬和敬佩之情,有时则增强他们对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