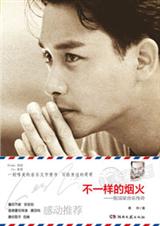戴高乐传-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全一致。但波兰工农群众并不因此响应俄国革命的召唤,而是以受到外来侵略威胁的爱国者的身份进行战斗。在苏联方面,斯大林则与托洛斯基相反,已经预见到这种反抗。在前线的另一方面,戴高乐查证到这点,因而强化了自己的历史观。
然而,对戴高乐来说,这也是一种崭新的战争经验。这里,与那种漫长而可怕的、在香槟和凡尔登经历的堑壕战经验毫无关系。戴高乐在波兰见证了与香槟和凡尔登经验完全相反的经验。从表面上看,军队在迂回,在转移,在前进或在后退,处于一种不完全准确的、但几乎盲目的和巨大的运动的混乱之中。戴高乐叙述了毕苏斯基的胜利,证实了运动战在波兰战争中的重要意义。他写道:“敌人以为波兰人完全绝望了,所以对他们袭击自己的左翼完全感到意外。因此,敌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进行认真抵抗,到处溃不成军,或者整团整团地投降。啊!我们在那里打了一个漂亮的战役!”
理所当然,地形的性质在这里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波兰军队兵力比较有限,战线拉得很长,重武器、特别是炮兵装备也差。但是,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运动战在这场战争中,重新具有首要的和完全决定性的意义——这与人们在法国战线上看到的、至少在1915年至1918年夏天看到的情况不同。戴高乐立即作出了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在拥有现代战斗手段的情况下,运动战可以在别处找到这种首要性,其条件是要有这样的战斗工具。恰好,这种战斗工具存在着,就象他在呈军队参谋部的离任报告中所写的那样:“坦克……应当集中使用,而不是分散使用。”戴高乐在1921年就把这个观点写在白纸黑字上,此后过了15年,他又把这个观点变成了自己全心全意为之献身的事业。
而今,和平重返了欧洲。戴高乐返回了巴黎。在波兰的最后一位上司尼塞尔将军,给他写了一段异乎寻常的评语,并加一句:“戴高乐上尉想要回国结婚。”于是,开始了一个为期10年的阶段,这个10年,至少从表面上看,也许是唯一的、与一个法国军官生涯最传统的过程相象的阶段。对法国军队来说,就象永远对世界各国军队来说,战后的时期是一个反省和休养生息的时代,贫困化和怀疑的时代。这是一种为无穷尽的烈士纪念碑举行揭幕典礼的时代。在数年中,在法国各省,每周都有一位部长,或者至少有一位议员,在佩戴奖章的勇士的簇拥下,为一座石像或铜像揭幕。这些雕像以寓意深刻的法兰西或者象征性的胜利为题,使那些牺牲的“法国兵”永垂不朽;在教堂的墙上或在公共广场的纪念牌上,写上了这些烈士的英名……这也是法国社会遭到通货膨胀吞噬的时代。①英镑从1919年兑换的25个法郎,增加到1923年的85个法郎。货币流通在1914年为50亿多一点,到1925年增至500亿,零售物价指数则从100点增至463点。中产阶级——它吸收了大多数军队干部——多半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受害者。出于谨慎,中产阶级将其储蓄变为国家证券、外国公债和固定资本债券。可是,所有这些证券的指数都从1914年的100点降到1925年的28点。
实际上,法国社会在颂扬战争胜利与对无序的现在和烦人的将来感到惶惶不安之间,在它扎根于过去与加速改变社会风气和思想状态之间摇摆不定。法国人从欧洲和世界地图上,看到了阿尔萨斯-洛林的回归,法国士兵在莱茵河畔的驻扎,一些新的友好国家在欧洲大陆东部的出现,以及一些殖民地的扩大。但是,由于美国国会拒绝批准,美英两国在凡尔赛条约中向法国所作的的边界保证,而未能幸存下来。那些以法国的朋友或盟国著称的年轻国家,则因其社会和政治危机、财政困境和货币动乱而格外引人注目。不久后,摩洛哥发生了里夫战争,叙利亚发生了德鲁兹山区人民的起义,这些事件开始预示着法兰西帝国的不稳定。
实际上,战争并未深刻地动摇法国的社会结构。小企业有些退步,但它有利于中等企业,而不利于大企业发展。那些不到10个雇员的企业还占企业总数的98%。城市手工业者始终有130万名。农村人口外流相当缓慢,并未引起对平均经营土地面积进行任何重大的再分配。虽然1918年的储户在1925年被迫失去其储蓄的实际价值的60%,但胜利公债却轻而易举地找到了700万名认购者。著名的3厘公债在1920年1月值67,20法郎,五年后还值55,50法郎。此后,普安卡雷在翌年稳定法郎和物价,恢复了那种从1914年以来遭到损害和损失的社会“信任”。1924年,41万家庭有了自己的银行存折……
然而,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战争时期,主要是工厂,还有商业和办公室曾经大量使用过妇女劳动——突然加速了夫妻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演变。整个社会受到了妇女劳动的影响,至少是通过引述和神话来受其影响的。例如,女作家维克多·玛格丽特的小说《任性的姑娘》的成功,特别是科莱特的小说的成功,时装的更新——头发剪短、不穿胸衣的连衣裙上衣、短裙子——便是妇女劳动的见证。超现实主义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一个经久不衰的重要地位,开始对人们的观点施加一种人们尚未能估量的影响。“黑人舞会”进入巴黎剧场,传统音乐让位于爵士音乐……扎根于过去与令人目眩的新时代构成了社会的两极。社会在这两个极中间摇摆不定,这在世界各国无疑都是这样。但在法国社会,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时而对商业复兴、许多人发财、重新恢复稳定和出现生活欢乐感到放心,时而感到社会不稳定、在悄悄地发生动摇,前途未卜,受到布尔什维克革命这种“东方曙光”的诱惑——有人认为它是模式,有人认为它是威胁,但大多数人却感到不理解……
“当代的特点,”戴高乐在《剑刃》一书的前言中写道,“是不确定。现在有那么多的违反惯例、预见和学说,有那么多的考验、损失和失望,有那么多的光辉、冲击和意外,它们动摇了现有的秩序。”
但是,对戴高乐所属的军队来说,这特别是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他在此书最精彩的一个段落中表达了这种观点。
“武器刚刚改变了世界,它们不是让人首先受其之苦,而是在为自己徒劳的热情哭泣。军队在经历重大战争努力之后感到忧伤,无疑,这种忧伤状态只是没有任何传统的东西。在和平时期军队进行的虚拟活动与军队的潜在力量两者之间的对比中,有某种令人失望的东西,但那些当事者感受不到,没有痛楚。‘有那么多的军队没有使用,’毕苏斯基说,‘有那么多的目的和那么多的徒劳!’更有甚者,在战役结束后的岁月里,有一种同样的痛苦浸透了士兵的灵魂。若是突然松弛下来,看来活力就会破裂,而且有时还会发出一种深沉而深刻的怨声——沃弗纳格和维涅曾经用这种怨声哄骗过我们。”
在战后的这些岁月里,法国军队的组织机构感到了这种反弹。⑦起先,军队的反应是极其缓慢的,而且有一种维持原状的考虑,而这种情况同战后重建的经济要求毫无关系。必须给政府和议会时间来最后决定实行重大的裁军。1921年的法律规定,从翌年起将服兵役的期限从三年减为一年半,并且明确规定,在1925年底向众议院递交一份关于将服兵役的期限缩短为一年的报告——这是在1921年就决定了的。为了补偿缩短兵役期限的后果,1921年的法律还规定招募8万职业兵、30万海外士兵和3万民事职员。但与此同时,由于相信战后服役不再有前途,许多军官离开了部队。虽然军队人数起先维持在一个肯定过高的水平,但它逐年地降下来。其中,干部人数原定是23万名军官和士官,后来先后降到15万和10万6千人。和平时期用于训练机动部队和守护边界的师,先后从45个降到32个和20个。步兵团从1914年的173个,降到1924年的65个和1929年的56个;骑兵团先后从79个降到48个和25个;野战炮团先后从62个降到60个和28个;重炮团先后从13个降到30个和24个;相反地,土著步兵团从9个增加到28个。与此同时,由于必须在从摩洛哥到叙利亚一线应对动乱,新建了5个非洲骑兵团,并最终组建了10个坦克团。这就是法国军事机器所走的下坡路。诚然,战后国家重建的沉重代价和欧洲和平的巩固证明这种走下坡路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在马其诺防线的庇护下,这种做法导致法国军事机器在30时代初的严重削弱。为着理解戴高乐是什么形势下参加战斗,致力于法国拥有一个装甲兵团——新的军事强国的工具,就必须记住这段历史。
戴高乐返回巴黎后,就结了婚。⑧戴高乐在兄长克扎维埃结婚之后,表明了成婚的意愿。戴高乐家族同旺德鲁家族共同努力,安排了他同未来的妻子、年方20岁的伊冯娜首次见面。旺德鲁家族祖籍爱尔兰,定居法国北方的加莱已有200年历史,其中有些人当了船东,有时也出任加莱市议会议员和市商会成员。伊冯娜的父亲是一家饼干厂的老板,当时远遐闻名。伊冯娜的母亲则独树一帜,是法国第六名获得汽车驾照的妇女,战时还当过加莱军队医院的护士长,因而获得战争十字奖章。旺德鲁家族比戴高乐家族——戴高乐家族完全不是殷实人家——富裕得多,在他们的财产中,主要是在阿登山区拥有一座城堡——“七泉”城堡。在1940年以前,戴高乐经常到这座城堡去度假,直到战争的灾难迫使旺德鲁家族卖掉这份家产时为止。在“金秋沙龙”进行相亲之后,便安排了一次下午品尝点心。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历来都是必定要提及此次品尝点心,因为根据这个多半是真的、而且不管怎样具有象征意义的传说,当时戴高乐打翻了茶杯,茶杯掉到了伊冯娜的连衣裙上。然后,是发出参加圣西尔军校舞会的邀请,使戴高乐同伊冯娜聚在一起。伊冯娜还感到有些困惑。根据她兄弟雅克非常详尽的叙述,伊冯娜对于自己同戴高乐的高矮之差提出了疑问:戴高乐比她高出40厘米以上……因为戴高乐必须在11月20日返回波兰,所以两家的做法变得有点更加急迫。还是根据雅克的证词,伊冯娜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将来要么嫁他,要么谁也不嫁。”因此,两家在11月11日订了婚约。随后,1921年4月6日,在加莱举行了婚礼,先是在市政府,然后翌日在加莱圣母院。根据当时非常流行的习惯,戴高乐同伊冯娜在意大利进行了蜜月旅行。
传统的婚姻。传统的礼仪。戴高乐的私生活显得平静而幸福。其标志是1922年12月28日,诞生了一个名叫菲利普的男婴,男助产士、勒维-索拉尔大夫使得男婴身体健康。戴高乐一家有了一个合适的住所,它始终位于塞纳河左岸,在荣军院(拿破仑墓)和法国军事学校附近,经过格勒诺布尔大街,便是“德塞街心公园14号”。戴高乐先后获得了两次表彰——一次是因其在韦斯迪尔河战役指挥有方而受到军队嘉奖,另一次是被授予波兰的军功勋章。此后,是一次很有趣的分配工作,戴高乐被任命为圣西尔军校的历史副教授,负责教从资产阶级大革命到1918年停战这一时期的法国历史。
1922年5月2日,戴高乐在其军事生涯中,跨越了一个为一切有价值和有雄心的军事学院军官所必要的阶段。他考取了高等军事学院。在参加第6龙骑兵团、一个飞行大队和第503坦克团正规学习班之后,戴高乐在暑假结束后进入了高等军事学院。那份使戴高乐考取新学校的评语毫无例外地写了赞美之词,证如圣西尔军校副校长所写的那样:“该军官具有高素质,他本人知道这点。知识广博而扎实,能力很强,具有很快领会问题和出色介绍问题的才干。讲课很受欢迎,得到学生的高度评价,被誉为演说家,所以对学生具有很大的影响。他准备报考高等军事学院,将来肯定会得到录取和获得成功。”事实上,在129名学生中,戴高乐只是以第33名的成绩被录取和以第52名的成绩毕业。因为此时,是那些塑造其历史人物,预言其前途和书写其“传奇”的阶段之一。高等军事学院当时由德布内将军领导,德布内也尽可能准确地代表贝当的观点,可以说是贝当的发言人。德布内的副手是比诺将军和迪费厄将军,后来他们俩都坚决反对戴高乐在使用坦克问题上表达的观点。据甘默林将军在《回忆录》里提供的证词,迪费厄以秘密支持那些从1936年起在军队内部组建的极右翼网络而著称。沙维诺将军担任防御工事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