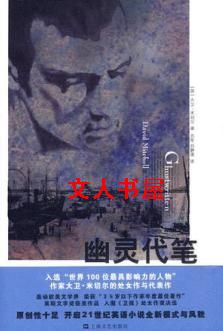云图-第5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什么请求啊,卡文迪什先生?”他是个一点都没有喜剧色彩的牧师。鲁尼牧师是个
职业牧师,和曾经与我在赫里福德较量过的一个逃税的威尔士图画设计师简直一模一样,但
是那是题外话了。
“我想请您帮我寄一张圣诞卡,牧师。”
“就这事儿啊?你请诺克斯护士帮忙的话,她肯定帮你办了吧?”
看来那个母夜叉也把他买通了。
“诺克斯护士和我在与外界通信方面的意见不是很一致。”
“圣诞节为我们在彼此间架起沟通的桥梁提供了个绝佳的机会。”
“圣诞节是个绝佳的机会,让打盹儿的狗继续打盹儿,牧师。但是我真的很想让我嫂子
知道在我们的主生日时我挂念着她。诺克斯护士可能已经跟你提起过我亲爱的哥哥去世的事
了吧?”
“无比悲痛。”他的确清楚圣彼得的事,“我很难过。”
我从夹克的口袋里抽出卡片。“我写的是寄给‘照料者’,不过是为了确保她能明白我的
圣诞问候。她头脑——”我轻轻地敲敲脑袋,“不太正常,说这个我很难过。放这儿,让我
把它放进你的法袍的兜里……”他扭动着身子,但是我逼他就范了。“我真是太幸运了,牧
师,有我能信得过的朋友。谢谢您,衷心地谢谢您。”
简单,有效,神不知鬼不觉,蒂莫西·卡文迪什,你这个狡猾的老狐狸。新年到来之前,
奥罗拉之家醒来就会发现我已经像佐罗一样脱身了。
厄休拉引诱我到她的衣橱里:“你一天也没变老,蒂莫,这个弯弯曲曲的家伙也跟以前
一样!”她淡黄褐色的毛蹭着我的纳尼亚世界里那么长的街灯柱和卫生球……但是接下来,
跟以前一样,我醒了,身上肿胀的附件和冗长的附录一样受欢迎、大有裨益。六点整。供热
系统布置得像是约翰·凯吉(注:美国作曲家、作家与摄影家,亦为前卫派音乐家。)风格
的作品,很前卫。脚指头关节处的冻疮火辣辣地疼。我想着过去的圣诞节,数目要比还没过
的圣诞节多得多。
我还得忍受多少个早晨?
“勇敢点,TC(注:蒂莫西·卡文迪什,下同。)。一列疾驰的邮政列车正在把你的信
带往南方的伦敦老家。它一旦受到撞击就会释放出集束炸弹般的影响,惊动警察、社会福利
工作人员和经由海逸市场老地址转交的莱瑟姆夫人。很快你就能从这里出去了。”我想象中
描绘着为了庆祝我重获自由收到的那些迟到的圣诞节礼物。雪茄、上等威士忌、打一分钟九
毛钱的电话、跟玛菲特小姐(注:原为一首儿歌里的人物,指年轻姑娘。)调情。为什么到
此为止?带着《男人帮》和“队长伟哥”到泰国重新再战?
我看到壁炉架上挂着一只变形的毛袜。我关灯的时候它并没挂在那儿。谁会偷偷进来却
不把我弄醒?厄尼宣布圣诞节期间休战?还能是谁?好人老厄尼!我穿着法兰绒睡裤高兴地
浑身发抖,把袜子拿下来,带着它回到床上。它很轻。我把它从里朝外翻过来,碎纸片像雪
片一样飞出来。我的笔迹,我的字,我的词!
我的信!
我的救赎也被撕碎了。我捶胸顿足,撕扯着头发,咬碎了钢牙,捶打着床垫,把手腕都
弄伤了。该死的鲁尼牧师该下地狱。诺克斯护士,那条偏执的母狗!她在我睡着的时候,像
死神一样盯着我!去他妈的圣诞快乐,卡文迪什先生!
我屈服了。十五世纪晚期的动词,古法语叫sucer,拉丁语叫succumbere,但它是
一项人类生活状况中的基本需要,对我特别如此。我屈服于愚蠢的照管服务。我屈从于礼物
上的小卡片:“新朋友祝卡文迪什先生——未来度过更多奥罗拉之家的圣诞火礼拜式(注:
圣诞期间一种给儿童慈善组织捐款的礼拜式。)!”我屈从于我的礼物:印着世界奇景的一页
有两个月的日历(里面没有写死期)。我屈从于橡胶一样的火鸡肉、人造的填料和苦味球芽
甘蓝,屈从于放不响的鞭炮(一定不能引发心脏病,那对生意可不好)、侏儒戴的纸王冠、
大话连篇、无伤大雅的笑话(酒吧服务生:“要点什么?”骷髅:“请来一杯啤酒和一个拖把。”)。
我屈从于特别为了圣诞节加了点暴力成分的肥皂剧特别节目,还有奎尼的地府之言。小便回
来的路上,我碰到诺克斯护士,又屈从于她充满胜利感的“节日快乐,卡文迪什先生”。
BBC二台的一个历史节目那天下午正在播放1919年伊普尔(注:比利时西南边陲小镇,
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之一。)的一些老镜头。曾经繁荣的城镇变为人间地狱,这样的
嘲讽是我自己灵魂的真实写照。
我年轻的时候只看到过三四次快乐岛,然后它们就消失在雾霭、沮丧、冷锋、霉运和逆
潮中……我误以为那就是成年的含义,以为他们是我生命航程中一个不变的特征,我疏忽了,
没有记下它们的经度、纬度和入口。愚蠢至极的年轻人。为了得到一幅描绘永远持续的难以
言表之物,永恒不变的地图,现在的我有什么东西不愿放弃?这就像是要获得一幅云图。
我挨到了节礼日(注:圣诞节次日,人们之间按风俗互赠匣装节礼。),因为我太难过了,
连上吊都干不了。我撒谎。我等到了节礼日是因为我懦弱得连上吊的勇气都没有,午饭是一
份火鸡肉汤(加脆滨豆),只有在寻找迪尔德丽(那个不男不女的机器人)忘了放在哪儿的
手机时才让气氛活跃了一点儿。还魂的僵尸们享受着猜想的乐趣:它可能在什么地方(沙发
下面),它很可能不在什么地方(圣诞树上),还有它不可能在什么地方(伯金夫人床上的便
盆里)。而我自己正在像一条懊悔的小狗,叩响锅炉房的门。
厄尼站在铺着洗衣机零件的报纸上:“看是哪个稀客来了。”
“节礼日快乐,卡文迪什先生——”维朗尼卡笑容可掬,戴着一顶罗曼诺夫(1613至
1917年的俄罗斯统治家族。)式的皮帽。她大腿上支着一本厚厚的诗歌集。“进来,快请进。”
“有一两天了。”我少说了日子,感觉很尴尬。
“我知道!”米克斯先生大声说,“我知道!”
厄尼还是流露出不屑的神情。
“呃……我能进来吗,厄尼?”
他先是扬起下巴,然后又往下降了几度,表示那对他无所谓。他又把锅炉拆了,满是油
腻的胖手握着很小的银色螺钉。他没让我感到安心。“厄尼,”我终于说,“前两天的事很抱
歉。”
“哦。”
“如果你不把我从这儿弄出去……我会疯掉的。”
他把一个我连名字都叫不上的零件拆开:“哦。”
米克斯先生的身子晃来晃去。
“那……你怎么想?”
他在一包肥料上坐了下来:“哦,别这么窝囊。”
我想法兰克福书展结束后我还从来没笑过。我的脸都疼了。
维朗尼卡正了正那顶风情万种的帽子:“跟他说说我们的收费,厄尼斯特。”
“什么都行,什么都行。”我从来没这么认真过,“你们收多少钱?”
厄尼让我一直等着他把最后一把螺丝刀也放进他的工具袋:“我和维朗尼卡决定继续到
新的地界去历险,”他冲着大门的方向点点头,“到北方去。我有个老朋友会照顾我们。呃,
你跟我们一起走。”
我不知道那样做结果如何,但是那又怎么样?“好,好的。我愿意。”
“那就说定了。行动在两天后开始。”
“这么快?你已经有计划了?”
苏格兰人鼻子里哼了一声,拧开热水瓶盖,往盖子里倒了一杯味道很重的红茶:“哦,
可以这么说吧。”
厄尼的计划是一个高风险的多米诺骨牌连锁效应。“每个逃跑策略,”他上起课来,“一
定要比你的看守要更加聪明。”计划是高明,但是不要说鲁莽,如果任何一张骨牌没有引起
下一张的倒下,随即而来的暴露就会招致可怕的后果,特别是厄尼关于强制下药的毛骨悚然
的说法是真的话,那更可怕。搁以前,我很难想象自己能同意这个计划。对朋友愿意再次跟
我讲话的感激,和逃出奥罗拉之家(活着)的急切之情战胜了我天生的审慎,我只能这么说
了。
选中12月28日是因为厄尼听迪尔德丽说贾德夫人会在赫尔跟她的外甥女们一起看哑
剧。“情报基础。”厄尼敲敲鼻子(注:表示保密的动作。)。我倒是宁愿威瑟斯或是悍妇诺克
斯不在场,但是威瑟斯八月才会离开这儿到罗宾汉海湾探望他的妈妈,而且厄尼觉得贾德夫
人是我们的看守中头脑最冷静的人,所以也是最危险的。
行动日。我在行尸走肉们十点钟被赶上床睡觉前半个小时到厄尼的房间报到。“如果你
觉得你应付不过来,现在是退出的最后机会。”狡猾的苏格兰人对我说。
“我这辈子还从没有在任何事情上退缩过。”我回答道,坏牙里吐出的是谎言。厄尼把
通风机卸下来,从里面一个隐蔽的地方拿出迪尔德丽的手机。“你的嗓音最优雅,”他在分配
任务的时候跟我说过,“要活命就在电话里胡说一通。”我按下了约翰斯·霍切奇斯的电话号
码,号码是几个月前厄尼从霍切奇斯夫人的电话号码本上搞到的。
接电话的声音还睡意蒙眬:“什么事儿?”
“啊,好了,霍切奇斯先生吗?”
“是我。你是?”
读者,你会为我感到骄傲的。“康伟医生,奥罗拉之家的。我是来接替阿普伍德医生的。”
“上帝,我妈妈出什么事了吗?”
“恐怕是,霍切奇斯先生。你一定要坚强些。我认为她可能挺不过明天早上。”
“哦!哦?”
【文】一个女人的背景音在追问:“是谁?约翰斯?”
【人】“上帝啊!真的吗?”
【书】“是真的。”
【屋】“但是,怎么……她怎么了?”
“严重的胸膜炎。”
“胸膜炎?”
可能我这个角色中的同情心稍稍强于我的专业水平。“希利患的胸膜炎在你妈妈这个年
龄的女性中间也不是没有,霍切奇斯先生。这样好吧,你一来我会进行再次诊断。你妈妈现
在想见你。我已经给她注射了二十毫克的,呃,50号吗啡丁,所以她现在一点也不痛苦。
有件怪事,她老是在说些首饰的事儿。一遍又一遍,没完没了地说:‘我一定要告诉约翰斯,
我一定要告诉约翰斯……’你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吗?”
关键时刻。
他上钩了!“我的上帝。你肯定吗?她记不记得放在哪儿了?”
女人的背景音说:“说什么?什么?”
“她好像因为这些珠宝还留在家里感到非常难过。”
“当然,当然,但是它们在哪儿,医生?她说把它们藏在哪儿了?”
“好了,我得回到她房间了,霍切奇斯先生。我会在奥罗拉之家的接待室见到你的……
什么时候?”
“问问她哪儿——不,告诉她——告诉妈妈——您瞧,呃——”
“呃——康伟!我叫康伟。”
“康伟医生,您能把您的电话放在我母亲嘴边吗?”
“我是医生,不是什么电话俱乐部的人。还是你自己来吧。她就能亲口告诉你了。”
“告诉她——在我们到那儿之前坚持住,看在上帝的分上。告诉她——皮普金斯非常爱
她。我会在……半个小时后到。”
第一步结束。厄尼拉上袋子的拉链:“干得好。带着电话,万一他打回来。”
第二张骨牌是让我站在米克斯先生的房间里站岗,透过门缝望风。鉴于非常糟糕的健康
状况,我们忠诚的锅炉房吉祥物没有算在伟大的逃离计划之内,但是他的房间在我的对面,
而且他还能明白“嘘”是什么意思。十点一刻,厄尼到接待室向诺克斯护士宣布了我死亡的
消息。这张骨牌可能会倒向我们不希望的方向。(我们讨论了很多关于说谁死谁去送信的问
题:要说维朗尼卡死了的话需要厄尼演戏才能避免引起悍妇的疑心,他可没那个本事;要说
由维朗尼卡报告厄尼死了的可能也被排除了,因为她又容易陷入一场情节剧无法自拔;厄尼
和维朗尼卡的房间都挨着还有感觉的行尸走肉的房间,他们可能会从中捣乱。但我的房间在
老旧派那边,而且旁边只住着米克斯先生)主要的不确定因素是诺克斯护士对我的个人厌恶。
她会不会冲过来看看她倒下的敌人,用帽针插进我的脖子确认我是真的死了,或者先大举庆
祝一番?
脚步声。在敲我的门。诺克斯护士,闻着诱饵。第三张骨牌在摇晃,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