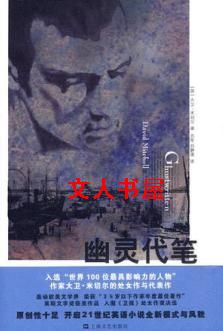云图-第3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抵得上二十个甫叔,元…027抵得上二十个敏植,怎么衡量都是如此。因为一个上等人的疏
忽,我在泰莫山唯一的朋友死了,而甫叔居然认为这次谋杀很好笑。但是愤怒锻炼意志,那
天我迈出了第一步,走向“宣言”,走向这个牢房以及几个小时以后的灯塔。
暑假发生了什么事?
照理甫叔应该把我存放在一个临时宿舍,可是他急着要去北海道打克隆糜鹿,他把这事
忘记了,要么就是认为哪个下层的寄生虫会替他做。
因此,某个夏日的早上,我醒了,发现整幢楼都空无一人。忙忙碌碌的走廊现在悄无声
息,没有铃声,没有广播;连空调都关了。从屋顶上看去,市区跟往常一样烟雾蒸腾,车水
马龙,成群的飞机穿过天空,留下一条条水蒸气的痕迹,但是校园却没了学生。福特场仅有
一半的车。烈日下,工人们在重新铺设椭圆形广场的地面。我查了索尼上的日历,才知道今
天是假期的第一天。我插好实验室的门,躲进了里间。
那么你在五个星期里从未走出过甫叔的实验室?一次都没有?
一次都没有。要知道,我害怕离开我的索尼。每个周末,有个保安来检查实验室。有时
候我能听见文吉秀在隔壁的实验室说话。除此之外,一片寂静。晚上我把百叶窗拉下,关掉
天窗。我有足够的速扑度过整个假期。
可那是整整五十天孤独的囚禁啊!
五十天美好的时光,档案员。我的头脑在我们的文化中纵横穿梭,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
十二部经典:隆尖的《七种方言》、主席的《内索国的形成》、尹将军的《战争史》等。你知
道这些书目。一部未删节的《评论》的索引指引我阅读战前思想家的著作。当然,很多下载
都被图书馆拒绝了,可我下到了两本从晚期英语翻译过来的《乐观主义者》、奥威尔和赫胥
黎;还有华盛顿的《关于民主的讽刺》。
等到甫叔第二个学期回来的时候,你依然是写论文用的标本?
对。我的第一个秋天到来了。我偷偷地收集飘到屋顶上的红叶。秋天过去了,我的叶子
都退了色。夜晚变得冰冷,连白天也会结冰。下午,甫叔多半在加热的炕上打盹,看着三维
影像。他夏天的投资赔了很多钱,他父亲拒绝支付他的债务,他的脾气变得暴躁。我唯一能
抵御他暴怒的措施是不被注意。
下雪了吗?
啊,对了,下雪。去年的第一场雪来得很晚,十二月才下。凌晨醒来时,我感觉到了。
装饰窗户的新年精灵裹上了雪花,美轮美奂,档案员,美轮美奂啊!院子里,无人理睬的雕
像四周,树丛被积雪压弯了,雕像因此显得格外雄伟。我能看到雪花飘落到我曾经的牢房,
我喜欢这里。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雪花像是受伤的紫丁香,那么纯洁,那么宁静。
有时候你像个唯美主义者,星美。
也许那些被剥夺了得到美的权利的人才更懂得美。
这个时候,梅菲博士该走进故事了吧?
是的,六重节前夜的那个晚上也在下雪。大概在二十点左右,甫叔、敏植和方冲了进来,
因为吸了毒,脸红红的,耐克上沾着冰。我在里间,差点来不及藏起我的索尼。记得我正在
读柏拉图的《理想国》。甫叔戴了一顶学位帽,敏植抱着一篮子薄荷味的兰花,篮子跟他一
样大。他一边把花儿往我身上撒,一边说:“花瓣献给勺美、松美、星美,随便什么名字……”
方洗劫了甫叔存放烧酒的橱柜。他一边朝后扔了三瓶酒,一边发牢骚说那些牌子的酒都
是狗尿。敏植抓住了两瓶,第三瓶在地上摔得粉碎,引发了一阵又一阵的笑声。“清扫干净,
灰姑娘!”甫叔朝我拍拍手,然后安慰方说,六重节一年只有一次,他会开一瓶最好的酒。
等我扫起所有的玻璃碴,敏植已经找到了一部三维色情迪斯尼。他们一边看,一边像专
家一样争论优缺点以及是否逼真,嘴里还喝着烧酒。那个晚上,他们醉得肆无忌惮,尤其是
方。我躲到了里间,听到文吉秀在实验室门口叫那些酒鬼们安静一点。我偷看着他们。敏植
嘲笑吉秀的眼镜,问为什么他家没钱给他治疗近视。甫叔让吉秀爬到他的身上。整个文明世
界都在庆祝六重节,他却想要安静。等到方终于不笑了,他说要让他父亲对文的家族进行税
务检查。文吉秀在门口气得七窍冒烟,终于还是被三个上等人扔的李子和嘲笑赶跑了。
方似乎是三个人的核心。
的确。他能挖掘出别人性格中的裂纹线,现在在十二都市中的一个当律师。毫无疑问,
他相当成功。那个晚上,他不停地激怒甫叔。他晃着烧酒瓶,指着柯达上的死雪豹问甫叔,
专门给旅游者准备的猎物在基因改造后变得有多呆笨。这伤到了甫叔的自尊。他反驳说,他
只猎杀那些改造过基因、变得更凶猛的动物。在加德满都山谷,他和他的弟弟跟踪了那头雪
豹几个小时,它被逼得无路可走,扑向他的弟弟。甫叔一箭射死了它。雪豹在半空中被射中
眼窝。听到这里,方和敏植装出一副无比敬佩的样子。过了一会儿,他们哈哈大笑,瘫倒在
地。敏植捶着地板说:“你真能胡扯,金。”方靠近柯达,看了一会儿说,拼接得很差。
甫叔用笔在一个人造瓜上画了一张脸,郑重地在眉毛上写了“方”字,然后把瓜在靠门
的一摞杂志上放好。他从写字台上取了弩,走到窗户的远端,瞄准。
方反对:“不,不,不不不。”他说如果射偏了,瓜不会撕开射手的喉咙,没有一发必中
的压力。他招手让我站在门旁。
我知道他的想法,可是方打断了我的恳求,警告说如果我违抗他,他就让敏植掌管我的
速扑。敏植的笑容消失了。方的指甲掐住了我的胳膊,把我带了过去。他把学位帽戴在我头
上,然后把瓜放在帽子上。“那么,甫叔,”他取笑说,“你现在还觉得你是神射手吗?”
甫叔跟方的关系是建立在敌对和厌恶之上的。他抬起弩,我恳求他停下,甫叔命令我不
许动。
那支箭的钢尖闪着光。死在这种男孩的激将之下,不仅无聊而且愚蠢,可是克隆人连自
己怎么死都无权决定。砰的一声,刹那间,弩箭射进瓜肉。甜瓜滚下帽子。敏植热烈鼓掌,
希望能缓解局面。我一下子轻松了。
然而,方轻蔑地说:“射中这么大一只瓜,你用不着激光瞄准仪吧。再说,你瞧,”他捡
起了瓜的残余部分,“你只不过打到了一点。得用杧果才配得上你的水平。”
甫叔把他的弩递给方,激他自己做到那样的水平:在十五步外射中杧果。
“行。”方接过弩。我绝望地反对,可是甫叔叫我闭嘴,他瞄了一眼那只杧果。方数了
十五步,装好了箭。敏植警告说,死一个实验标本,要填的报告多得要死。他们没有理他。
方瞄了很长时间。他的手微微发抖。突然,杧果炸开了,汁水四溅。可我估计我的煎熬还没
结束。果然,方吹了吹弩:“瓜,三十步;杧果,十五步。我加码到李子,十步。”他说李子
还比雪豹的眼睛大,但又说,如果甫叔承认他确实在胡扯,像敏植说的那样拒绝挑战,他们
就暂告一个段落,十分钟内不再评论。甫叔把李子在我的头上放稳,表情严峻,然后命令我
静止不动。他数了十步,转身,装上箭,开始瞄准。我估计我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会在十五
秒后死掉。吉秀又来砸门了。走开,我心里说,现在不能分心……
甫叔摇着弩的曲柄,下巴抽搐着。咣咣的砸门声越来越响,离我的头只有几厘米。方咒
骂着吉秀的生殖器和母亲。甫叔抓着弩的指节开始发白。
我的头啪的一声被撞开了:耳朵传来剧痛。我意识到身后的门被踹开了,紧接着看到那
些折磨我的人的脸上一副末日来临的表情。最后才看到,门口站着一个年纪大些的男人,胡
子上沾了雪,上气不接下气,开始大发雷霆,
梅菲董事?
是他,但我还是全面介绍一下他吧:统一部教授,梅里坚船民解决方案的设计师,内索
国杰出勋章的获得者,评论李白和杜甫的专著作者——“主体”董事阿洛逸·梅菲。不过,
我那时没注意他。血从我的脖子和脊背往下流。轻轻碰一下耳朵,整个左半身就疼得像被电
击一样。我移开手指,看到上面沾满了血,鲜红发亮。
甫叔颤声说:“董事,我们——”方和敏植没有帮腔。董事用一块干净的丝质手帕捂住
我的耳朵,让我坚持住。他从衣服里侧的口袋掏出掌上索尼。“张先生?”他朝着索尼说,
“拿急救箱来。请快一点。”现在我才认出他,是那个打盹的乘客。八个月前,便是他陪我
离开宗庙广场。
接下来,我的救命恩人盯着三个研究生。他们不敢跟他对视。“嗯,我们开始了一个很
不吉利的蛇年。”他向敏植和方保证,将由纪律委员会通知,对他们处以高额罚款,然后解
散了他们。两人鞠了一躬,赶紧走了。敏植的斗篷落在了炕上,但是他没回来。甫叔看起来
难过之极,梅菲董事让他煎熬了一会儿,问道:“你还打算用那东西射我吗?”
金甫叔扔了弩,好像很烫手一样。董事看了一圈乱糟糟的实验室,闻了闻烧酒瓶口。三
维淫乱场面吸引了他。甫叔在遥控器上摸索了一会,弄掉了,又捡了起来,按了停止,对准
方向,又按了停止。终于,梅菲董事开口了。现在,他准备好了,要听甫叔的解释,为什么
会用系里的实验克隆人练习十字弩。
是啊,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甫叔找了各种理由:因为是六重节前夜,他喝得酩酊大醉;他本末倒置,忽视了焦虑症
状;交友不慎,过度热心于惩戒他的标本;都是方的错。后来连他自己都意识到最好还是闭
嘴,等着斧子落下。
张先生带着药箱来了,给我的耳朵喷了药,敷了药膏,贴了一块胶布,还和蔼地说了些
话。除了元…027从未有人跟我这样说过话。甫叔问我的耳朵能否痊愈。梅菲董事硬邦邦地
说,那不关他的事,他的博士生涯已经终止了。看到了自己的前途滑向落魄,这个曾经的研
究生顿时变得茫然,脸色发白。
张先生握着我的手告诉我,我的耳垂撕裂了,但是承诺医务员第二天早上就回来将它换
掉。我非常害怕甫叔的报复,全然顾不上担心我的耳朵,幸好张先生说我们马上就跟梅菲董
事一起离开,去我的新住处。
这对你来说肯定是个好消息。
是的,只是我没了索尼。我怎么可能带上呢?想不出什么可行的办法。我只好点头,希
望能在六重节假期里取回来。那个旋梯需要我全神贯注,下楼比上楼更危险。在大堂里,张
先生拿给我一件带帽子的斗篷和一双保暖耐克。董事称赞张先生选了斑马纹的设计。张先生
回答说,斑马皮是当季最时尚的街头款式。
董事及时救了你,他有没有说为什么?
到目前为止,没有。他说我将被转到校园西侧的统一系,还道歉不该让“那三只喝醉的
绦虫”拿我的生命当儿戏。由于天气糟糕,他们没能更早地介入。我忘记说了哪些恭顺谦卑
的话作为回答。
校园的回廊上到处是庆祝六重节前夜的人群,充满了节日气氛。张先生教我拖着步子在
粒状冰上走,以便增加摩擦力。雪花落在我的睫毛和鼻孔上。梅菲教授走近的时候,雪仗停
战了,参战人员纷纷鞠躬。帽子提供的莫名感觉非常美妙。穿过回廊,我听到了音乐。不是
广告或者流行歌曲,而是原汁原味、四处回响的音乐。“是唱诗班。”梅菲董事告诉我,“公
司政权的人类不总是冷漠、小气,或者恶毒。感谢主席,他们有时也很高尚。”我们听了一
分钟。我抬起头,觉得自己好像要飞上云霄。
守卫统一系的两位执法者向我们敬了礼,接过了我们打湿的斗篷。跟心理基因组系大楼
的朴素相反,这幢楼房的内部非常华丽。铺了地毯的走廊两旁装饰着隆尖时期的镜子,锡勒
国王的骨灰盒以及统一系名人的三维影像。电梯里有个吊灯,从里面传出声音,朗诵着公司
政权的守则,梅菲董事让它闭嘴。让我吃惊的是,它真的闭嘴了。跟上次一样,电梯加减速
的时候,张先生都扶着我。
我们出了电梯,来到一个宽敞的下沉式公寓,公寓像是一个上层阶级生活方式的广告片。
一丛三维火焰在中央的火炉里跳动,周围是飘在空中的磁悬浮家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