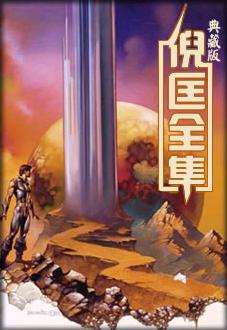木炭-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普索利爵士胀红了睑:“这就是我一生期待著的时刻!”
我又道:“林先生,我们已经知道,你在木炭之中,你曾要求我们放你出来--”
我才讲到这里,记录笔又急速地颤动起来,极快地记录下了四组波形。这四组波形,不必陈长青加以解释,我都可以看得明白,那还是“放我出来”!
我约略向各人解释了一下,又道:“林先生,请问怎样才能放你出来?”
我们都屏住了气息,在等候他的回答,可是记录笔却一直静止著。
我有点著急,说道:“林先生,请问你是不是可以利用英文字母的发音,来表示你要说的话?我们现在要明白你的意思,需要通过很复杂的手续,那太困难了!”
在我这样说了之后,记录笔又动了起来,陈长青摇头道:“不!”
我向白素望了一眼,我要集中精神和林子渊的灵魂讲话,所以我的意思是,将解释的事,交给白素去做。白素立时会意,向普索利他们解释著。
我又道:“那样,太困难了!你所要说的每一个字,我们都要花不少时间来研究,可能一年之内,也弄不懂几句话!”
记录笔又静止了很久,在场的所有人互望著,神情极焦急,过了大约一分钟,才看到记录笔又动了起来,出现了四组波音,但不是“放我出来”,四组音波,看来差不多,然后又静了下来。
所有的人,一起向陈长青望去,这时候,陈长青的地位极高,除了他,再也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
陈长青全神贯注地看著那四组波形,口唇颤动著,冒著汗。我们都在期待著他发出声音,可是过了好久,只见他额头的汗珠愈来愈多,就是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来。我忍不住道:“怎么啦?”
陈长青抬起头来:“这四个音,是没有意义的!”
我十分恼怒,几乎想骂他,但总算忍住了,没有骂出口来,只道:“你说出来听听!”
陈长青道:“第一个音节,和小喇叭的音波形状差不多,短促,那是,那应该是‘播’的一声。”
陈长青一面说,白素一面翻译著。陈长青又道:“第二个也差不多,不过促音不如第一个之甚,要是发起音来,也是‘播’的一声。第三组,音波波形较圆,和第一二组也大致相同,是声音较低沉的一个‘播’字--”
我忍不住道:“播播播,全是播!”
陈长青胀红了脸,说道:“第四组多少有点不同,但是,但是……”
我道:“还是‘播’!”
陈长青怒道:“波形是这样,我有甚么办法?”
我道:“波形有不同,可是你却分辨不出来!”
陈长青的脸胀得更红,说道:“我当然分辨不出细微的差别--”
我也不知道何以自己如此之急躁:“所以,只好播播播播,不知道播些甚么!”
陈长青握紧了拳头,几乎要打我,白素陡地叫道:“等一等!”
我们全向白素望去,白素先吸了一口气,然后才道:“会不会是‘波、坡、莫--’”
她才讲到这里,我和陈长青两人,都“啊”地一声,叫了起来,神情欢愉莫名。
普索利他们,只看到我们争吵,当然不明白何以忽然之间,我们如此高兴,我忙道:“各位,林先生指示了我们一个通讯的办法,他的意思,是用一种注音符号,根据这些注音符号,可以拼出中国话来!”我讲到这里,转过头去:“是不是,林先生?”
记录笔立时振动,出现了一个“是”字的波形。
所有的人一听得我这样解释,都欢呼起来。
【第十四章】
接下来的日子之中,我们这一群人,几乎废寝忘食,在和林子渊交谈。虽然国语注音,是一种好的交谈办法,但是我们首先要弄清四十个注音字母的波形,而且每一个字的注音字母,数字不同,林子渊平时所操的可能不是标准国语,有很多情形,要推敲决定,最后还要问他是,或不,才能决定。所以,花费的时间相当多。
在开始的时候,一天,只能交谈十来句话,而且是极简单的话。到后来,渐渐纯熟了,可以交谈的,就多了起来,比较复杂的语句,也可以表达出来。
前后,我们一共花了将近五个月的时间,在这五个月之中,我们都住在陈长青家的地板上,不理发、不剃须,每个人都成了野人。
有时候,当我们睡著的时候,记录笔会自行振动,写下波形。在这五个月之中,记录纸用了一卷又一卷,不知道用了多少卷。
当然,在这五个月之中,我们也知道了林子渊当年,前赴炭帮,前赴猫爪坳之后,发生的一切事。
我将林子渊的经过,整理了一遍,记述出来。这是有历史以来,一个灵魂对活著的人的最长的倾诉。其中有很多话,当林子渊在“说”的时候,由我发问来作引导,所以我在记述之际,保留了问答的形式,使各位看起来,更加容易明白。
由于“灵”是一种极其玄妙的存在,这种存在之玄,有很多情形,人类的语言文字,无法表达,也是在人类语言所能领悟的能力之外。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灵”可以听到人的语言,但“灵”无形无质,根本没有耳朵,如何听?但是“灵”又的确可以听得到,所以,在语言的表达上,明知“听”字绝不适合,但也只好用这个字,因为并没有另一个字,可以表示根本没有听觉器官的听!
这只不过是例子之一,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总之我在叙述之际,尽量使人看得懂就是。
首先,是我的问题:“林先生,你在木炭中?”
“是的,很久了,自从我一进入,就无法离开,放我出来!”
我苦笑:“我们很不明白你的情形,在木炭里面?那是一种甚么样的情形?我们如何才能放你出来?”
“在木炭里,就是在木炭里,像人在空气当中一样,我只是出不来,我要出来!”
“怎样才可以令你出来呢?将木炭打碎?”
“不!不!不要将木炭打碎,打碎了,我会变得在其中的一片碎片之中!”
“你的意思是,即使将之打得最碎最碎,你还是在木炭之中?即使是小到要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微粒,你也可以在其中?”
“是!”
我苦笑:“这对你来说,不是更糟糕了么?”
短暂的沉默:“不见得更坏,对我来说,大、小,完全一样!”
(这一点,我们无法了解,何以“大”、“小”会是一样的呢?)
“那么,请你告诉我,我们应该如何做?”
“我不知道!”
(他自己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做,才能使他离开木炭,这真是怪异莫名。)
我很审慎:“会不会你进入了木炭之后,根本就不能离开了?”
“不!不!一定可以的,玉声公进入了一株树之后,他离开了。”
“他是怎么离开的?”
相当长时间的沉默:“事情要从头说起,我为何到猫爪坳去的,你已经知道?”
“是,但不能确定你是为了宝藏,还是勘破了生命的秘奥,想去寻觅永恒?”(奇*书*网。整*理*提*供)
“两样都有,但后者更令我向往。我离开了家,一点留恋也没有,这一点,当时我自己也很奇怪,但事后,当然不会觉得奇怪。我到了猫爪坳,可是来迟了,玉声公寄住的那株树,已经被砍伐!树虽然被砍伐了,可是树桩还在,根据地图上的符号,我几乎没有费甚么功夫,就找到了那个树桩。当时,我不能肯定玉声公是还在这个树桩之中,还是在被采下来的那段树干之中!”
“这的确不容易断定,结果,你--”
“我在树桩之旁,聚精会神,希望能得到玉声公给我的感应,但是一点收获也没有,于是,我只好到炭帮去,要找被砍下来的树干。”
“是的,你到炭帮去求见四叔的情形我已经知道了,可是在你不显一切,进了炭窑之后--”
“我一定要进窑去,在他们拒绝了我的要求之后,我一定要进炭窑去!”
“林先生,我想先知道一些因由。你明知进入炭窑之中会有极大的危险?”
“是!”
“你明知道你进入炭窑,可能丧失生命?”
“我知道,我知道一进入炭窞,不是‘可能’丧了性命,而是一定会丧失生命!”
“那么,是甚么使得你下定决心,要去作这样的行动?是不是玉声公终于给了你一些甚么启示?”
“没有,在我进入炭窑之前,一直没有得到玉声公的任何启示。你问我为甚么要这样,我想,是由于我已经认识了生命。”
“对不起,我不明白,你说你认识了生命,是不是一个人,当他认识了生命之后,他必须抛弃生命呢?”
“抛弃肉体。”
“我还是不明白,对一般人而言,抛弃肉体,就是抛弃生命。我再重复我的问题:当一个人认识了生命之后,是不是必须抛弃肉体?或者说,当一个人认识了生命之后,是不是必须自己寻觅死亡之路?”
(在我问了这个问题之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收不到任何讯息,几乎使我们以为已经从此不再有机会收到任何音讯了。但是,音讯终于又传了过来,显然,这个问题,对于一个灵魂来说,也十分难以解答。)
“不是这样,我想每个人的情形不同,不一定是每个人在抛弃了肉体,即死亡之后,都能够有机会使生命进入第二步。这其中的情形,我还不了解,因为我一直在木炭之中,还没有机会知道其它类似的情形,究竟是怎样的。但是对我来说,我在进入炭窑之前,我已经对我当时的生命形式,毫无留恋,而且我可以肯定,会进入另一种形式。”
“你何以这样肯定?”
“你也看过玉声公的记载罢,当然是他的记载给我的启示所致。”
“你为甚么对当时的‘生命形式’一点也不留恋了呢?人人都是以这种形式生存的!”
“太短暂、太痛苦了!先生,如果我不是当时使自己的生命进入另一形式,我现在还能和你交谈吗?”
“那也不见得,我才见过尊夫人,她就相当健康。”
“是么,请问,还有多少年呢?”
(我答不上来。照林子渊的说法,“生命的第一形式”能有多少年?一百年,该是一个极限了吧!)
“请你说一说你当时进入炭窑之后的情形。关于生命的形式,暂时不讨论下去了。因为我不明白,我们所有人,都不容易明白。”
“是的,的确不容易明白,能够明白的人太少了,正因为如此,所以大家才沉迷,在短暂的光阴之中,做很多到头来一场空的事,而且为了这些事,用尽许多手段,费尽了许多心机,真是可怜!”
“请你说你进了炭窑之后的情形!”
“我一跳进了炭窑,身子跌在炭窑中心,那一部分没有木料堆著,离窑顶相当高,我一跌下来,身子一落地,双腿就是一阵剧痛,我知道可能是摔断了腿骨,同时,我的身子向旁一侧,撞在一旁堆叠好的木料之上,那一堆木料,倒了下来。压在我的身上--”
“请你等一等,照祁三和边五的说法,你一进入炭窑,四叔已下令生火,而边五立即跳进来救你,这其间,至多不过半分钟的时间!”
“我想可能还没有半分钟,但是对于奇妙的思想感应来说,有半秒钟也就足够了,我刚才说到哪里?是的,一堆木料,被我撞得倒了下来,压在我的身上,使我感到极度的痛楚。也就在这一刹那间,我听到了,我说听到了,实际上是不是听到的,我也不能肯定……”
“我只是肯定,突然有人在对我说:‘你来了!终于有我的子孙,看到了我的记载来了!’我忙大叫:‘玉声公!’这其间的过程极短,但是我感到玉声公对我说了许多话。”
“是一些甚么话?”
“他告诉我,我的决定是对的,他也告诉我,人的魂魄,可以进入任何物体之中,像他,就是在一株树中,许多年,他现在才可以离去,他告诉我,要离开进入的物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他又不知道如果不先进入一件物体之中,会有甚么样的结果,可能魂魄就此消散,不再存在,所以他不赞成我冒险。”
“当时,你看到他?”
“甚么也没有看到,当时,炭窑之中,已经火舌乱窜,浓烟密布,我只觉全身炙痛,一生之中,从来也未曾感到过这样的痛楚。然而,那种痛楚,相当短暂,我当时可能是紧紧抱住了一段木头,突然之间,所有的痛苦一起消失,我仍然看到火,看到烟,听到烈火的轰轰声,看到火头包围住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在迅速蜷曲,变黑,终于消失。然后,我所看到的是火,连续不断的火。我在火中间,可是一点也不觉得任何痛楚,我知道自己的魂魄已成功地脱离了躯体,所以我当时,大笑起来。”
“那很值得高兴的,再后来呢?”
“再后来,火熄了,我只看到许多火,我自己在一个空间中,突不出这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