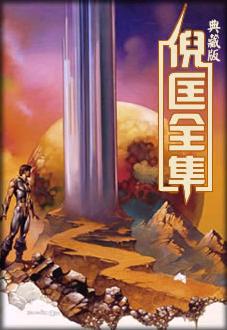梦里废墟-第6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得必有所表示才行。于是也托病辞了印刷厂的差事,乖巧的也请了个长假,回家去钓他的鱼,逗他的鸟。胡自牧又重新的夺回了印刷厂,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报社。
莫桐对这一切的变化,是非常的敏感。首先就是庄老和莫子琪对他异乎寻常的亲切起来,老爱没事找事冲着他说两句,或笑上两下。殊不知莫桐反而因此更加的焦躁起来,他心里一万个希望他们,还是象以前那样对他,不冷不热,不闻不问,自己也落得个清净。可是他这一心愿,是无法传达给莫子琪与庄老他们的。即使传达了,他们这些名利场中的老手也不会理解,反而会徒费心机的猜测来,猜测去,额外增添出事端来。莫桐为他们这点,感到可哀。他不由为此在心底问自己:‘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作人究竟该怎么样做?他想从父亲身上寻求答案,但这个答案,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他又想从母亲那里寻求答案,可这答案却叫他无奈,他想想还是往自己身上寻求答案,可是他寻求来寻求去却发现一个可悲的事实,这就是他身上的答案,是一片空白无头又无绪。
这使他陷入深深的困惑中,于是他决定闭门不出,深思这些对他至关重要的人生困惑。然而一天两天过去了,莫桐埋首于中外哲学巨著中,他没有从那些浩瀚的论述里,得到一点启发,反而愈陷愈陷昏迷。这日,他捧本培根的《人生论》坐在葡萄藤架下研读。忽的,手中的书被人凭空夺了去,他一看是昭儿。他与她之间已生好些日子的闲气,彼此都甚少言语。他不明白为什么要夺他的书。
“昭儿把书还我。”
昭儿说:“你有病,偏又坐在这么冷的石凳子上看书,不怕再把身子给折腾坏了。”莫桐说:“平日你总劝我多读书,多看书。说是有益身心,今儿怎么反倒不是了。”昭儿语塞,她把书还了莫桐,幽幽地说:“你要懂得爱护自己。”莫桐听了就说:“你既然会说这样的话,那又为什么前些日子里硬是用冷冰冰的话来伤我呢,又为什么要象个陌生人一样的远离我呢。”
昭儿心里酸苦,她一句也答不上。她黯然一叹说:“你不知道我的心事,你若是知道了,我的心事,你就不会这样说我了。”莫桐看着她走开,喃喃说:“心,又是心。我这人即不懂得这人的心,那人的心,还看这个劳什子的破书干嘛。”他愤愤将那书往石桌上一摔,大步走出家门。一直走,一直走出葫芦巷,过了枫桥,到了大街上。大街上熙攘人流,你来我往。莫桐茫然的走在人群中,他此时心里有万千个烦念纠结在心头,只有不住的走,才能让他暂时忘却这烦念。不知不觉中,莫桐以走出城外到了西郊。
他想到了前面的废墟,便一步也不停留的走上山去,曲折的黄泥道,一转又一转,阁楼就显现在眼前。这里是何等的熟悉啊!只是门前的一把铁锁住了里面,也锁住他在这里的快乐时光。莫桐抚摩着那铁锁,将脸紧贴在门上,耳边仿佛传来伊震风崔卫回祝牟慈的笑声,纯雯和宣慧的打闹声。可惜只是幻觉,莫桐告诉自己里面是空空如也,一个人也没有。他失望的离开阁楼,走进废墟。高高黄土墙、衰黄的狗尾草在墙头摇曳,只有这些无声的朋友不会舍弃他,莫桐站在黄墙下望着墙头的天空,一直望到天的边际处。
突然角落中响起一个声音:“天上又没有东西,有什么好看的。”莫桐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他举目望去只见前方的一个土堆边,躺着一个人,正懒洋洋地晒着冬日。他一细看竟是他们以前见过的那个神秘老头古恨水,方才他神智昏昏的走进废墟来,竟没有瞧见他。当下就应他:“你看不到东西,不代表我也看不到东西。”
古恨水嘿一声笑说:“有趣、有趣、你这话只可在我面前说,若是在别人面前说,则又当是一番傻话了。”莫桐听了不禁动了怒,他本来心伤至深,才来到这废墟里。想不到就是在这里,也还有人奚落他。他说:“我说了这话,便成了傻话。那你横躺在这里,不也是傻人一个吗。”
古恨水仰天大笑,莫桐连声问:“你笑什么?你笑什么?”古恨水边笑边说:“我这样的一个人,无论躺在那里,别人也不会嗔怪。可是只要你把刚才那句话,放在任何人面前说,别人都要当你是个大傻子。”莫桐静心一想,心里更是黯然。这个怪老头说得一点也不假,自己是不敢在别人面前,说出自己真实的切身感受。因为这些感受都是那么的莫以名状,无法让体会了解。他想到这,不由又哀叹自己竟然连一个疯老头都不如。不如他活得潇潇洒洒,自由自在。
他灰心地说:“你讲得不错,不错。”古恨水翻身坐起说:“你既然认为我说得不错,何不过来坐坐。”莫桐心念一动,就走过去盘膝坐下。古恨水说:“小伙子何必那么郁闷,在这废墟里,只有天地、神灵、你、我,何不放下心胸,当一回解脱之人。”莫桐说:“敢问老人家一回有多久呢?一回之后又该如何?”
古恨水问:“你敢是为这而烦恼。”
莫桐不答反问:“人的一生究竟有多少个这样的一回呢?”
古恨水被他问住了,他皱着眉头反复的念,一回……一回……。最后说:“佛说人生似轮回,一回,一回是无终止的。可道又说虚无,虚无是一回也没有,大千世界俱归于一团飘渺不定的气体中。孔子又曰,未知生,焉知死。是说活得都不明不白,还问什么死后解脱之事。”
莫桐说:“做人可真难,连成神成圣的人,都对人生歧解不一。更何况是平常人,就更难解答了。”古恨水说:“年轻人你何必执作于这个天大的难解呢。”莫桐说:“我思故我在,我若不思,则我不在。”古恨水说:“那你这不是在难为自己吗,人的一生会有很多迈不过去坎,既然知道迈不过去,就干脆不去迈。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争。浑浑噩噩,藏拙蹈晦,也不妨是人生一大享受。”
莫桐说:“老人家你就是这样活着的吗?这样认为人就是这样活着的吗?”
古恨水说:“齐万物,一死生,泯是非得失,曳尾于涂中。”
他说完问:“孩子你知道这个意思吗?”
莫桐点点头又摇摇头,古恨水瞧得奇怪说:“既然点头,又为什么要摇头呢。”莫桐说:“老人家你蔑视生死,甚至将生死视为一体,处在陋巷里鼓盘而歌,无视人言苟议。可是在我看来,却更象是画地为牢,将心作囚。”
古恨水一脸肃穆地说:“我苦苦的在这废墟里,求索几十年,求的就是这样的解脱。我认为我,已经做到物我两忘,代神立言了。”
莫桐听了纵声大笑,笑声回荡在空旷的废墟里。良久,他止住了笑,望着一脸惊鄂的古恨水,长身站起说:“老人家既然生似悬疣,何不一痛溃痈。这不是一了百了,既然物我两忘,为何又要代神立言。”说罢他头也不回的下了山。
一路上,他有种奇特而兴奋的感觉,这感觉就是古恨水原来在他的心目中是神秘的,神秘得近似神圣,仿佛他是个来自未知世界的先知,来引领世人。现在这种罩在他头上的奇幻光圈消失了,消失的原因,就是自己竟比他还要的神秘,还要神圣。回到家里,他找到母亲问:“妈妈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张曼文正在写毛笔字,她停下笔说:“莫桐什么问题?”
莫桐不假思索的说:“什么是人生?人活着是为什么?”
张曼文直直的望着儿子一会儿:“哦!你问这个问题干嘛。”莫桐很着急的说:“妈妈你快回答我这个问题好吗?”他之所以急是因为母亲是他解答这个问题的最后一把钥匙,前一把失效了,让他倍感失望,所以他将所有的希望都放在自己这个孕育了他生命的母亲身上。张曼文思考了下说:“莫桐这是个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如果它有了答案,它就不是个问题了。”
“为什么?为什么?”莫桐拉住母亲的手追问:“怎么会没有答案呢?”
张曼文望着一脸问号的儿子说:“这是从目的论的观点得出的天然结果,什么是目的论?目的论的本身就是人生这个概念,是要宇宙中一切的物质,大到日月星辰,小到蛆虫细菌都是因为人活着才存在,存在就是为了让人实现他美好的理想。人就是固执的把自己放在宇宙的中心,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只有人才把怎样活着比活着的本身更要紧,只有人才顽固的探寻活着的意义。可是人其实却是很渺小,他跟大自然中的一根小草,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一种生命,两种形式的表现。因而生命是愁苦的,它的偶然性大于它的必然性。只是在它该来的时候,它就来。在它该走的时候,自然而然的离开。人的存在是不需要为它编造人为的理由,没有必要给它赋予特别的意义,更不需去费心的证明它的意义。这就注定了人生是无常的,是永远没有答案的。我们能做的只是将这人生的无奈,演化为从容的过程,静静的欣赏它。”
莫桐惘然若失,母亲的话和古恨水的话都不是他所要的答案,他们两人一个让他觉得神的虚幻,一个让他感到人的沉重。他说:“妈妈,我已经有所领悟了,人就应该是顺时而来,适时而去。”
张曼文说:“我们的认知是超越不了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是无法从眼前的世界,看到不可捉摸的未来。”
莫桐心里还有点疙瘩:“妈妈,人活着总是要有点什么的吧!比如你呢?”张曼文抚摩着儿子的头说:“妈妈的一切,就是可用一首诗来概括;一把茅遮屋,若使薄田耕不熟,添个新生黄犊。闲来教儿女,读书不为功名。种竹、浇花、酿酒、世家闭户先生。”
莫桐看着母亲,他发现母亲说这话时,恬淡、宁静的神态就似那石壁画上的飞天女神般庄美,他带着一种信徒的虔诚问:“妈妈,我是不是也可以做世家闭户先生?”张曼文微笑着问:“傻孩子你怎么可以做个世家先生,你怎么会想做个世家先生呢。”
“我觉得这样的人生很美,美得就象蝴蝶穿插在花朵中般。”张曼文用食指轻点下儿子的脑门:“可是傻孩子,你忘了刚才妈妈的话了吗,你想的那种美是种痛苦的美,蝴蝶穿插在花朵丛里翩翩起舞。但只要它抬头,就会发现她原来是飞舞在,苦难这朵乌云阴影下。”
莫桐靠在母亲的怀中,闭上眼睛半是撒娇半是疲倦地说:“不-----妈妈,我已经找到一个法子了,那法子可以让蝴蝶无忧无滤的飞舞在花朵中,它抬头看天是碧蓝、碧蓝的,再也没有什么苦难的乌云,留下可憎的阴影了。”
张曼文琢磨着该怎么回答,儿子这孩子气十足的话。等她想好适当的话时,她却发现儿子已经睡着了,她顺手拿起件毛毯将儿子与自己深深的包裹在一起。嘴里轻哼着一曲《月光光》的儿歌。。。。。。
偎依在母亲怀中睡觉的感觉是甜美,莫桐一觉醒来后,感到整个世界在他的眼中都是澄清的。他写张字条托宣慧带给纯雯,他在字条上约好明日黄昏时在枫桥上等她。冬日的天色灰暗得特别早,到了隔日黄昏时分,桥上已经没有多少人过往了。莫桐守侯在桥中,晚风呼呼的刮过城门的角楼,带动铜铃叮当作响。桥下浦河干枯得露出黯褐色的河床,河水被分割成一小股一小股的细流。河边的杂草倒伏在水边,往日里那散发无尽美感的枫树林,落尽了叶,秃着枝干纠结在一起。
莫桐想起很多往事来,一个个身影浮现在他的眼前;母亲、父亲、纯雯、昭儿……忽然一阵风扬起的沙粒,涩了他的眼睛。所有的身影霎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失神的伸手向眼前捞了捞,什么也没有。桥上的暮色越来越浓,隐约中一个身影走进他的视线,是纯雯,她系着白围巾围巾的一角犹在风中飞舞。
两人站在桥上,互相呆望着对方半天。纯雯才问:“你约我出来有事吗?”
“没有什么事情,只是好久没有见你了,想看看你。”莫桐声音不大,但纯雯听在耳里却如春雷般的响亮。
“想着我”她简直怀疑是自己听错了,她迅将她那明亮的眼睛投向莫桐,只见莫桐一脸平静,含着笑望着自己。她不太相信的又问下:“你想我吗?你会想我吗?”
莫桐说:“是的,很想、很想、实在是无法压抑自己了。”
纯雯的眼里跳跃着许许多多的泪花,不是吗?在在无数个日日夜夜中,她是多么的渴望自己能听到这些话。可当她骤然听到时,她又不敢相信是真实,正是这种落差。使她想求证个清楚:“莫桐你如此的坦然,是因为你把所有的绊脚石都搬开了吗?”
莫桐抱以浅浅一笑:“纯雯看开一切太难,不介意一切更难。这社会上有如此多的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