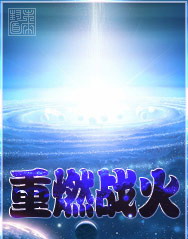车臣战火之谜-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么好吧,由你决定。”公爵给自己斟了一点白兰地,也不祝酒便一饮而尽,然后擦了擦胡子。“你知道有一辆公共汽车爆炸,死了几个人,其中有两个孩子?”
“电视和报纸把我们脑子里都灌满了。这是唯一一次抓住了罪犯的恐怖活动。侦破速度之快是创纪录的,已经开了庭,判了极刑,俄罗斯人都兴高采烈。”
“那么你不高兴吗?”公爵审视地看了他一眼。
“干嘛不呢?”古罗夫不慌不忙地说。“恐怖分子必须逮捕和审判,这次的判决我同意。不过我原则上反对死刑。”
“你的眼神说明你这人对什么都无动于衷。”
“今天令我大动肝火的事太多了,逮捕和枪毙一个恐怖分子没法叫我激动。谁不知道有多少车巨人——女人和男人,还有孩子——死在这场战争中?!”
“你怎么啦,是为这种报复行动辩护吗?”
“决不是!”古罗夫本想把酒杯挪开,却端起来一饮而尽。“罪犯应当抓起来判刑,尤其是杀人犯,行了,公爵,谈正事儿吧。”
“你是个粗人,列夫·伊凡诺维奇。”
“我是直来直去,不谈我不喜欢谈的事。你来找我有事,那就说吧。该你跳你却胆怯了,公爵,只起跑不往前跳。可是你这样的体型不能跑久了,否则跳不成反而会跌交。”
古罗夫对车臣的战争过分敏感。他对总统本来就持怀疑态度,后来总统再次当选,他也投了票,可是同总统许下的诺言相反,车臣的战事愈演愈烈,上校感到无可奈何。偏偏这时候来了这么个脑满肠肥的格鲁吉亚人,高谈阔论,用粗大的手指挖他那尚未封口的创伤。
“你不喜欢我,我可以走。”公爵甚至把身子从桌边挪开了一点,两撇小胡子也垂下来,脸上一副气恼的神情。
“你不能走,公爵!”古罗夫低声说,由于拖长了嗓音,显得有些嘶哑。“既然你上我这儿来,你就是别无办法了。你在电话里说事情很急,不能等到晚上。说吧。”
“铁木尔没罪,可他却被判处枪决。”沙尔瓦从口袋里掏出一方大手帕擦了擦脸。
“铁木尔·扬季耶夫?”古罗夫耸了耸肩。“我不熟悉案情,但这并不重要。原则上我不排除法庭审判可能有误,因此我才反对极刑。这次审判中这一点也无关紧要。判决是有陪审团的法庭作出的,最高法院已经驳回上诉。案卷在特赦委员会那里,特赦机会等于零。总统决不会赦免全国家喻户晓的案件中的车臣恐怖分子。”
“这我明白,”沙尔瓦点了点头,“可这娃娃没罪。”
古罗夫的气已经消了,他用手抹掉脸上的汗,站起身来。
“对不起,我去洗洗脸。”说着他走进浴室。
背后传来玛丽亚高跟鞋的笃笃声。她看了古罗夫一眼,从小柜里默默取出瓦洛科金①,倒了几滴在杯子里,兑了些水。古罗夫喝了药,洗了脸,回到厨房里坐下,问道:
①一种舒张血管的药物。
“你知道是谁爆炸了公共汽车吗?”
“不知道,可那个孩子没罪。”沙尔瓦忧郁地重复了一遍。
“他是你的儿子?这不可能,他是车巨人,不是格鲁吉亚人。我说的是空话,可是你从哪儿知道那小伙子无罪?”
“他爷爷是我的朋友。爷爷也叫铁木尔。他找到我,说这孩子没罪。”
要是换一个场合,古罗夫听见这话准会笑起来。此刻他紧闭嘴唇,转过脸去,只是为了不冷场他才问道:
“为什么你不能等到晚上再谈?请求特赦的案卷在办公厅一搁就是好几年。”
“今天晚上十点辩护律师要乘飞机去外地休假,我原想你需要跟他谈谈。”公爵的背向前弯了下来,一副绝望的神情。
古罗夫开始可怜这个人了,他体格魁梧,头脑聪明,一度叱咤风云,但实际上又很天真。
“我跟辩护律师谈谈吧,不过我相信,他不会告诉我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从理论上说,假如相信已经判决的犯人无罪,那就只有一种办法救他:找出真正的凶手,证明他有罪,然后把材料交给检查机关。”古罗夫推论一番,为的是不至冷场,聊以表示他对这个毫无指望的案件的关切而已。
“是吗?”公爵抬起头来,两眼炯炯发亮。“你找几个朋友干起来吧。花多少钱我们都不在乎。我们试过,想给法官一百万,可人家不让我们靠近法官。这个案子闹得满城风雨,仿佛以前没出过人命案、爆炸案似的。”
“你这话是多余的,”古罗夫摇摇头表示责备。“只要以前杀过人,就可以不分清红皂白,混为一谈吗?头一次抓到一个恐怖分子,人们的心情可以理解。抓到的恐怖分子是车臣人,那更是好上加好,枪毙这个败类。反正是你们杀我们的人,我们也杀你们。”
古罗夫靠在椅背上,点燃一支烟,然后慢悠悠地继续说:
“你一生的经历错综复杂,沙尔瓦,你知道人都不喜欢认错。可这是送上门来的,碰巧是个车臣人,惨无人道的坏蛋,杀害儿童。这就是说,我们问心无愧,我们是对的,车巨人该消灭掉。根据法院判决枪毙的无辜者不止一人,你们那个小伙子没法挽救。”
“跟辩护人谈一谈吧,求你了,列夫·伊凡诺维奇,”沙尔瓦轻声说道,“我跟那人约好了,他等着咱们。”
“你甚至都约好了?那好吧。”古罗夫倒了一大杯矿泉水,喝了一口,沉思起来。
他得跟辩护人谈一谈,可是不论那人告诉他什么,他作为密探都不会按这个案子。古罗夫深信这一点。即使另有重大罪证,画出了真正的恐怖分子的图形,这个案子还是不能办。当然啰,可以像往常一样去休假,去年还剩下两周,加上法定的四十天,时间有的是。带上斯坦尼斯拉夫,还有春季共过事的两个精明能干的退休侦查员。一切都可以办到,没有什么不行的。过一两天或一个月,连上帝都诅咒的亲爱的民警局里就会得知,古罗夫上校正在查找一个制造了恐怖事件的人。可是案卷里已经有了定罪判刑的人犯。这就是说,古罗夫得了“好处”,想救出这个犯人。不用满身泼脏水,只消仔细往他身子抹一点黑,他二十多年的工作和名声、威望就会扫进下水道,冲得一干二净。对于车臣的那场大屠杀,民警局决非所有的人看法都跟他古罗夫上校一样。许多人认为,那些“黑小子”应当好好惩罚一下。俄罗斯人不能吃任何车臣人的苦头,要用坦克把格罗兹尼碾平,让所有“黑皮肤”的家伙再也不敢放肆。行了,咱们对他们热情够了,用不着客气了。
古罗夫认识一些军官,他们就是这样议论的。倘若他们得知他古罗夫,这个洁身自爱的白领阶层、受到宠爱的贵族,竟然卖身投靠这些……其实他既不是什么白领阶层,也并未受到宠爱,倒不如说恰恰相反,是领导容忍他古罗夫,仅此而已。然而这一切都没有意义,就像那车臣人到底炸了还是没炸公共汽车都毫无意义一样,反正“人民”胸有成竹,也就是说,事情就该是那样。
“沙尔瓦,对不起。”古罗夫把矿泉水喝完,本想说不上辩护人那儿去,看见客人眼里凝聚的痛苦和期待的神情,便站起身来说:“我得跟玛丽亚谈谈。”随即走出厨房。
他还没来得及开口,正在扣紧手提箱的玛丽亚就平静地说:
“你去吧,这个人你必须帮他一帮。会有人来接我、帮我的,我安顿好了就给你打电话,三天以后我就到家了。”
“谢谢你。”古罗夫吻了吻玛丽亚的脸颊,把箱子锁好。“告诉你的伙伴们,把桌子上的东西全都带走,只给我留一瓶白兰地和矿泉水。”
“你不用说,古罗夫,我知道带什么、留什么。”玛丽亚使了个调皮的眼色,来到客厅里送男人们出门。
辩护律师是个六十岁左右的知识分子,他接待客人时异常冷淡,甚至带有敌意。问好时点点头,也不伸手跟人握手,只做做手势把他们让进摆满书架的昏暗的书房。房间里一股潮气,散发出纸张和老鼠的气味。主人指了指几张破旧的皮安乐椅,自己在一张堆满公文夹和文件的大桌子边坐下来,把打字机挪到一边,取下没有镜框的眼镜,用一小块绿丝绒擦了起来。
“鄙人博亚里诺夫·伊万·马克西莫维奇,愿为您效劳,”他戴上眼镜。“我尚未有幸认识您,”他对古罗夫略一点头,“而对戈奇什维利先生,我已经相当详细地作了解释,我已尽到了自己的义务,非常遗憾,我无力挽救当事人的性命。我们尊敬的高加索客人以为在我们这个行当里一切都能靠金钱解决,这完全是徒劳的。”
律师讲起话来一口极为优雅的男低音,跟他的外貌形成鲜明对照。他身形瘦削,甚至瘦骨嶙峋,鹰钩鼻,高鼻梁,没有血色的薄嘴唇;看外貌这人说起话来嗓音本该又尖又高、不堪入耳。他那柔和深沉的男低音仿佛属于另外一个人。
古罗夫欠起身来鞠了一躬,彬彬有礼地说:
“请原谅我未作自我介绍。我叫古罗夫·列夫·伊凡诺维奇。”他坐下来,一只腿跷到另一只腿上。“我想说明一下情况。我是沙尔瓦·达维多维奇的老熟人,一辈子都在刑事侦查部门工作,我没有拿朋友的钱,将来也不会拿。我相信您和法庭,我之所以来访是出于对老朋友应有的尊重。我答应他跟您见见面,我们可以像文明人那样随便聊聊。”
“您想必有些问题,那就敬请询问吧。”主人整了整围在青筋突起的颈子上的围巾。“我洗耳恭听。”
“伊万·马克西莫维奇,您本人相信犯人有罪吗?”
“在这个案子中这不是原则问题。”
“对您来说是如此,尊敬的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对我来说则不是。请您务必回答。”
“好吧。我不知道。”律师把他那皮包骨似的手指弄得咯吱作响,又用尖刻的语气补充说:“与其说我相信,倒不如说不信。请注意,这是一种非常直觉的看法,没有具体事实证实。没有具体事实证明的是,那年青人犯了这个罪行。”
“一个有经验的人,他的直觉依据的是一定的事件,而您,伊万·马克西莫维奇,毫无疑问是个很有经验的人。我能不能问一下,您的直觉依据的是什么?是铁木尔·扬季耶夫的所作所为和供词吗?”
“在整个侦讯过程中铁木尔只说了两个词:‘是’和‘不是’,他承认有罪。”
沙尔瓦身躯肥大,坐在安乐椅里显得很挤。他默不作声,脸上淌汗,不时用他的方格大手帕揩汗。
“尊敬的伊万·马克西莫维奇,您的直觉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古罗夫挺喜欢主人,作为密探他不打算管这个案子,但他习惯于遇事刨根问底。
“您没法理解。不过,您是侦查员,也就是密探,我可以回答您的问题。您喜欢一个案子有太多证人吗?而且每个证人提供证词时都满有把握,既不颠三倒四,也不慌乱不安。有一个人看见铁木尔上了公共汽车,注意到小伙子手上有个背囊。铁木尔在后排位子上坐下,把背囊搁在地板上,而同座的人则记住了这小伙子和普普通通的背囊,似乎是背囊压了这人的脚。这个证人下了车,另一个人在他的位子上坐下,那人也记住了铁木尔和放在地板上的背囊。令人不解的是这个证人下一站就要下车,他干嘛要坐下来?下一站铁木尔下了车,站在车门边的一个人对这小伙子记得很清楚,而且斩钉截铁地断言这个‘黑小子’是空着手跳下车的。还有一些其他细节,但我认为我说的已经够清楚了。不,还有一件事。铁木尔跟坐在前面的一个小孩逗着玩,那小家伙后来炸得稀烂。当时小孩的母亲坐在过道另一边前排邻近的坐位上,看见他们玩,她幸免于难,对铁木尔记得一清二楚。她在法庭上说,她当时看着正在跟她儿子玩耍的车臣人,心里还想,我们干嘛对人家态度那么坏呢。这位母亲的证词对陪审员们产生了很大影响。”
“您认为这个案件是伪造出来的?”古罗夫问道。
“我没有根据这样断言,”律师干巴巴地答道。“再说铁木尔也证实公共汽车里的背囊是他带上去的。他只不过把它忘在车上了,因为他差一点错过了要下车的车站,他是在车子开动后跳下去的。”
“这些无懈可击的证人早在爆炸发生之前就在不同的车站下了车,那么刑侦人员是怎么一一找到他们的呢?”古罗夫颇感兴趣地问道。
“这话您问我么?”主人神色疲惫地叹了一口气。
“伊万·马克西莫维奇,为什么铁木尔拒绝讲出供词?”
“我不知道!我一无所知!几个昼夜没睡觉了,神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别再烦我了!”
“沙尔瓦,你带了酒壶吗?”古罗夫问道。
公爵在安乐椅上笨拙地翻动身躯,从口袋里掏出装着白兰地的水壶。
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