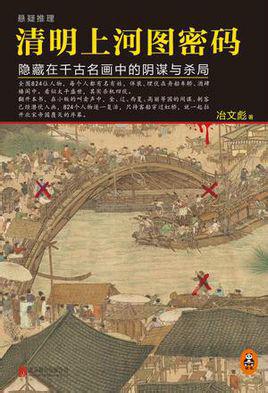清明上河图密码-第3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莫忘了盐,不然明个儿吃白水捞菜!”
“记着了。”彭嘴儿答话时,已经向东边走去了。
听他们叔嫂对答,康游似乎被触动了一下,却想不起来到底是什么。他关好门,回头看屋中昏暗幽冷,实在难以久留,就又打开了厨房门,对着门坐在椅子上,望着夕阳河水发闷。
以往这时候回哥哥家,是最心暖的时候,哥哥在喝茶读书,侄儿在闹,嫂嫂忙着煮饭烧菜,而后嫂嫂轻唤一声:“吃饭啦!”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时不时笑一阵……
对,吃饭的“吃”!
康游猛地想起来,嫂嫂春惜来汴京几年,说话已经大致是汴梁口音,但说到吃饭的“吃”,口音稍有些怪,隐约带着些“嗑”音。刚才彭嘴儿说这个字时,也带着“嗑”音,比嫂嫂的更明显!康游手下有个军士是登州人,说“吃”时,也是这种发声。
嫂嫂是登州人,彭嘴儿难道也是登州人?
康游想了一阵,隐约记起去年彭家兄弟搬到隔壁后,哥哥似乎说起过,他们原籍是登州。
随即,他又想起一件事。有两三次,他去外面井边提水时,碰到彭嘴儿也在打水,彭嘴儿看到他,随口笑着问:“今天是你来替你家嫂嫂打水?”
康游一直不喜彭嘴儿一副油荤样,不太愿意跟他多话,都只是随意应付一下。但现在回想起来,彭嘴儿那句问话似乎另有含义,那笑容里也似乎藏着些失望,难道彭嘴儿每天专门去井边候嫂嫂?
康游心里一震,彭嘴儿刚才凑过来难道是在打探?
嫂嫂藏在船坞内,并没有外人知道。武翘除了第一天送过去后,一直没敢再去,直到前天晚上才去了一趟,只有偷偷跟踪他的人才能得知那个藏身之处。一般人,嫂嫂绝不会带着侄儿跟他半夜逃走,除非是熟人。彭嘴儿自然是熟人,而且一张嘴十分油甜,最能套近蛊惑。
彭嘴儿刚才说去会朋友,不回来吃饭,难道是去见嫂嫂?但嫂嫂一向谨守妇礼,难得和外面男人说话,就连武家兄弟,已经十分熟络,也都尽量回避,她怎么会跟着彭嘴儿逃走?
无论如何,彭嘴儿十分可疑。
康游忙跑出去敲开隔壁武家的门,开门的是武翘,康游急急道:“我估计那贼人是彭嘴儿,我去追他,你赶紧去报知万福主管,带人朝东边追!”
说完,顾不得武翘愣懵在那里,就急忙向东边追去。
追了一阵,见彭嘴儿正大步前行,便放慢脚步,悄悄跟在后面。
彭嘴儿沿着河岸走了一段路,不时回过头张看,康游险些被发觉,因此不敢跟得太近,幸而河岸边隔几步就栽着榆柳,多少还能遮掩。
走了一阵,彭嘴儿似乎想起什么,穿过一条小巷,走到正街上,康游忙跟了过去,远远看见彭嘴儿来到一家馒头熟肉店,买了一大包吃食,又去旁边酒店买了一坛子酒。之后提着酒食又折回到河边,沿着河岸继续向东行去。
这时天渐渐昏黑下来,十几步外景物已经变得昏茫,这下更好跟了。只是四周也越发安静,康游不敢轻心,尽量放轻脚步不发出足音。
走过五丈河船坞,彭嘴儿仍继续向东,沿着河岸大步走着,脚底发出唰唰的声音,暗寂之中格外响。康游便不再往树后躲藏,拉开一段距离,跟着彭嘴儿的足音,轻步追随。
又走了一阵,前面河中隐约亮出一盏灯,是船上的灯笼。
难道彭嘴儿是要去那只船上?嫂嫂和侄儿也在那里?
康游继续小心跟着,渐渐走近了那盏灯笼,船身也渐渐能辨认得出了,那是只小篷船,停在一片小河湾处。船头灯光下似乎站着个人,是个男子。
天已全黑了。彭嘴儿果然走向了那只船,他走到船头边,和船上男子对答了两句,声音压得低,听不清楚,只隐约见船上男人点了点头,随后伸手将彭嘴儿拉上了船,两人一起掀开帘子,钻进了船篷。
康游忙加快脚步,赶到那船的附近,躲在岸边一棵柳树后面,探头去看,船帘里透出一些灯光,但看不见里面的人,只听见彭嘴儿和那男子的说笑声,随后有一个女人声音也跟着笑起来,不是嫂嫂春惜的声音。
三人在说什么,隔得有些远,听不太清楚,只隐约听到彭嘴儿说“饽哥”,康游心里一动,难道是那天取货的卖饼郎?他正在思忖,忽然又听见船里传出一个孩童的声音:“我爹呢?”
是栋儿的声音!
康游再顾不得藏身,急步梭到船边,躲在黑暗里侧耳又听。
又是栋儿的声音:“娘,爹不跟咱们一起去?”
“嗯。”
虽然极小声,但康游心头猛地一颤,是嫂嫂春惜的声音。
康游再忍不住,直起身子,朝船篷里喊道:“嫂嫂!栋儿!”
船篷里忽然静下来,连栋儿的声音都没有了,他的嘴一定是被捂住了。
康游又喊道:“嫂嫂!是我,我来接你和栋儿!”
船篷里仍毫无声息。
康游不耐烦,一步跳上了船头,伸手就去掀船帘,才掀了一角,他猛地想起自己向哥哥盟过的誓:“这辈子绝不再看嫂嫂一眼。”
他忙收回了手,犹豫了片刻,直起身子,转过背,面朝着船尖,放缓了声音,向船篷里道:“嫂嫂,请带栋儿出来吧。”
半晌,身后船篷里才传来嫂嫂春惜的声音,极低极弱,有些颤:“叔叔……请……请稍等……”
“好——”
一个字才吐出一半,他猛觉得后背一阵刺痛,随即感到一把尖刀刺进了自己的后背,疼得全身一阵痉挛。
他曾在边地征战戍守数年,早已无畏于刀兵战阵,回来之后,做了县尉,虽然偶尔也去缉捕盗贼,却哪里及得上边关分毫,觉得这京城如同一大张软床,至于彭嘴儿之流,只如虮虱一般,哪里需要防备。
然而,后背又一阵剧痛,那把尖刀从后背抽了出去。康游费力转过身,见昏昏灯光之下,彭嘴儿手里攥着一把短刀,刀尖还在滴血,他狠龇着牙,脸斜扭抽搐着,嘴唇不住发颤,双眼则闪着惊怕……
康游又望了一眼船篷,船帘遮着,仍不见嫂嫂和栋儿,他知道自己又错了一回,而且错得永无可赎之机。他心里一阵痛楚,随即仰头栽倒,最后低声说了句:“哥哥,对不住……”
第十四章 一个甜饼
命于人无不正,系其顺与不顺而已,行险以侥幸,不顺命者也。——张载
彭嘴儿只有一个念头:杀了康游。
若不杀了康游,他这一世便再没有任何可求可盼之机了。
他的父亲是登州坊巷里的教书先生,一生只进过县学,考了许多年都没能考入州学,又不会别的营生,便在家里招了附近的学童来教。
他父亲一生都盼着他们三兄弟能考个功名,替他出一口怨气。可是他们三兄弟承继了父亲的禀赋,于读书一途丝毫没有天分,嘴上倒是都能说,但只要抓起笔,便顿时没了主张。写不出来,怎么去考?
他们的父亲先还尽力鼓舞,后来变成打骂,再后来,就只剩瞪眼空叹。最后大叫着:“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咯血而亡。
好在他们还从父亲那里听来不少历史典故,大哥跟着一位影戏匠学艺,那师傅口技一绝,但肚里没有多少好故事,他大哥彭影儿学了口技之后,又加上父传的古史逸事,说做俱佳,一手影戏全然超过师傅,得了“彭影儿”的名号。
彭嘴儿原也想跟着大哥学,但他只会说,始终学不来口技,手脚又有些笨,所以只能做个说书人,又不想下死功,因此只学了三分艺,哄些过路客的钱。
他家那条街的街口有个竺家饼店,那饼做得不算多好,但店主有个女儿叫春惜,生得像碧桃花一样。
那时彭嘴儿才二十出头,春火正旺的年纪。有次他偶然去买饼,竺家只是个小商户,雇不起佣人,妻子、女儿全都上阵。那回正巧是春惜独自守店,她穿着件翠衫,笑吟吟站在那里,比碧桃花还明眼。
彭嘴儿常日虽然最惯说油话,那天舌头却忽然肿了一样,本想说“一个甜饼,一个咸饼”,张嘴却说成了“一个甜饼,一个甜饼”。
春惜听了,顿时笑起来,笑声又甜又亮,那鲜媚的样儿,让他恨不得咬一口。
春惜说:“听到啦,一个甜饼,何必说两遍?”文人小说下载
他顿时红了脸,却不肯服输,忙道:“我还没说完,我说的是买一个甜饼,再买一个甜饼,再买一个甜饼,还买一个甜饼……”
春惜笑得更加厉害:“你到底是要几个?”
“你家有多少?我全要!”
“五、十、十五……总共三十七个,你真的全要?”
“等等——我数数钱——糟——只够买十二个的钱。”
“那就买十二个吧,刚好,六六成双。我给你包起来?”
自此以后,每天他只吃饼,而且只吃竺家饼。
吃到后来,一见到饼,肠肚就抽筋。但这算得了什么,春惜一笑,抵得上千万个甜饼。
不过,那时他才开始跟人学说书,一个月只赚得到两三贯钱,春惜的爹娘又常在店里,他们两个莫说闲聊两句,就是笑,也只敢偷偷笑一下。
他好不容易攒了三贯钱,买了些酒礼,请了个媒人去竺家说亲,却被春惜的爹娘笑话了一场,把礼退了回来。
这样一来,他连饼都不敢去买了,经过饼店时,只要春惜爹娘在,他连望都不敢望一眼。偶尔瞅见只有春惜一人在店里时,才敢走进去,两人眼对眼,都难过得说不出话。半天,他才狠下心,说了句:“你等着,我赚了钱一定回来娶你。”春惜含着泪点了点头,但那神情其实不太信他说的话。
他开始发狠学说书,要是学到登州第一说书人的地步,每个月至少能赚十贯钱,那就能娶春惜了。
可是,才狠了十来天,他又去看春惜时,饼店的门关着,旗幌子也不在了。他忙向邻居打问,春惜一家竟迁往了京城,投靠亲戚去了。
一瞬间,他的心空得像荒地一样。
他再也没了气力认真学说书,每天只是胡乱说两场混混肚子,有酒就喝两盅,没酒就蒙头睡觉。父母都已亡故,哥哥和弟弟各自忙自己的,也没人管他。
弟弟彭针儿跟着一位京城来的老太丞学了几年医,京城依照三舍法开设了御医学,那老太丞写了封荐书,让彭针儿去京城考太医生。彭影儿知道后,说也想去京城,那里场面大,挣的钱比登州多十倍不止。彭嘴儿见兄弟都要去汴梁,也动了心。
于是三兄弟一起去了京城。
彭嘴儿原以为到了京城就能找见春惜。可真到了那里,十万百万的人涌来涌去,哪里去找?
他哥哥彭影儿功夫扎实,很快便在京城稳稳立住了脚。弟弟彭针儿进了医学院,看着也前程大好。只有他,那点说书技艺,在登州还能进勾栏瓦舍混几场,到了京城,连最破落的瓦舍都看不上他。他只有在街头茶坊里交点租钱,借张桌凳,哄哄路人。每天除了租钱,只能挣个百十文,甚至连在登州都不如。
京城什么都贵,他们三兄弟合起来赁了屋子,不敢分开住。三弟彭针儿进了太医学外舍后,搬到学斋去住。唯有他,只能勉强混饱肚子,独自出去,只能睡街边。
不过,三弟彭针儿和他一样,做事懒得用心用力,学了几年,仍滞留在外舍。去年蔡京致仕,太医学随着三舍法一起罢了,彭针儿也就失了学。他原就没有学到多少真实医技,又没本钱开药店医铺,只能挑根杆子,挂幅医招,背个药箱,满街走卖。
起初,彭影儿还能容让两个弟弟,后来他挣的钱比两个弟弟多出几倍,脸色便渐渐难看起来。之后又娶了亲,嫂嫂曹氏性子冷吝,若不是看在房屋租钱和饭食钱三兄弟均摊,早就撵走了他们。即便这样,她每天也横眉冷眼,骂三喝四。£我僦暧手機電孞書蛧£
他们两兄弟只能忍着。忍来忍去,也就惯了,不觉得如何了。
这个处境,就算能找到春惜,仍是旧样,还是娶不到。因此,他也就渐渐死了心,忘了那事。每天说些钱回来,比什么都要紧。
两三年后,他渐渐摸熟了京城,发觉凡事只要做到两个字,到哪里都不怕:一是笑,二是赖。
有手不打笑脸汉,无论什么人、什么态度,你只要一直笑,就能软和掉六分阻难;剩下三分,那就得赖,耐心磨缠,就是铁也能磨掉几寸;至于最后一分,那就看命了,得了是福,不得也不算失。
于是,他慢慢变成个乐呵呵的人,就是见条狗,也以乐相待,恶狗见了他都难得咬。
这么乐呵呵过了几年,直到去年春天,他去城东的观音院闲逛,无意中撞见了一个人:春惜。
春惜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已是一个少妇,手里牵着个孩童,身边还跟着个中年男子。不过他仍旧一眼认出了春惜,脸还是那么中看,仍是一朵碧桃花,且多了些风韵。春惜并没有看到他,他躲在人背后,如饥似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