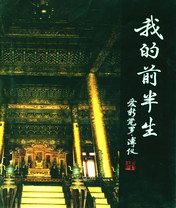老戏的前世今生-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元杂剧在涉及到妓女的爱情时,很自然地将商人与舍人——达官贵人的公子——归为一类,这是失败者一族,他们总是在与书生情敌的争夺中败下阵来。周舍遇到的是名叫安秀宝的书生。这位安秀宝也不是善茬,按照他的自述,“小生姓安名秀宝,洛阳人氏。自幼颇心儒业,学成满腹文章。只是一生不能忘情花酒。”他一见宋引章嫁了周舍,一赌气就要来争。原来他也曾经嫖过宋引章,而且当初宋美人也曾经有意要嫁给他,然而最终却好事未成。戏里没有说为什么没成,但是从戏情上推断,大约总是老鸨不肯让她出嫁吧,现在听说,哦,原来宋美人是可以嫁人的啊,那么,凭什么非要嫁周舍人而不嫁我啊?他的理由是宋美人当年答应过他。不过,妓女从良时选婿,难道还非要论个先来后到吗?好像没听说这行还有这规矩。所以安秀宝的道理是不讲究的,因为道理不讲究,不能光明正大地与周舍去争,才转头来央求与宋美人曾经有过八拜之交的同门姐妹——另一位妓女赵盼儿,她就是《救风尘》的第一女主角。
赵盼儿分明是个好事的主儿,就算她没有因为见着往日依赖着自己的姐妹宋引章嫁了个有权有势的公子哥儿就忿忿然,但心里的不爽起码是有的。刚巧,好好的有个秀才来央求她,装模作样地推托了几句再加几分火上添油后,立马出动要去拆散这桩婚姻。不想宋引章并不听劝,宋美人的回答很实在,要我嫁安秀才?“我嫁了安秀才呵,一对儿好打莲花落。”那意思是说,我可不愿意跟着安秀才过穷日子,文人,文人又怎么样,守着个文人做老公能当饭吃?宋引章的话并不是没道理,就算是安秀才会读点书有点儿学问,毕竟还没有个正经的营生,也看不出有多少出息。用元杂剧《举案齐眉》里的小丫环梅香的话说,“世间多少穷秀才,穷了这一世,不能发迹。”更何况还有宋引章没有说出戏里也故意朦胧了的话——那还是个“一生不能忘情花酒”的文人呢。
这样的心态,很不像大多数戏剧作品里的妓女,因为大多数戏剧作品,妓女好像天生就是用来给文人做托儿的,开头提到的《谢天香》就是典范。此外,她们还经常帮助文人脱困,比如说著名的《玉堂春》,那位有才气也有积蓄的妓女苏三不仅帮助落魄(虽然是由于嫖她而落魄)文人渡过难关,而且还资助他进京赶考终于高中状元,因此她最终是应该做夫人的了;所以,偶尔有妓女嫁给商人或者舍人那她就惨了,《杜十娘》里的女主人公是还没嫁成就绝望投江而死,宋引章倒是嫁成了,一进门就被打了五十杀威棒,然后过的是什么日子啊,不知道是和她以前在娼门里比还是和一般的良家妇女比,总之觉得是生不如死,终于无法忍受,厚着脸皮只好再去求同门姐妹赵盼儿搭救,于是就有了这部精彩的作品。
是的,我经常疑惑不解地读古代戏剧作品,不明白为什么它们那么兴致勃勃地写文人墨客与风尘女子的浪漫情调,而且还经常要拿商人及舍人垫在底下做陪衬。有时你不明白,同样是嫖娼,为什么商人和舍人的嫖娼就很低俗很丑陋,而文人墨客的嫖娼就很风流很雅致。不过,说理没用,艺术本来就不是用来说理的,艺术就是用来为一个时代以及艺术家们自己泄愤的,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那么戏剧作品写文人与妓女的浪漫,应是另有所图。
我想无论是在何时何地,文人墨客的嫖娼与商人舍人一样,无非都是追求婚姻之外的肉体的片刻欢娱,难道其间还真的有多少哲学意蕴不成,非要说文人嫖娼就会衍生出什么有文化深度与情感内涵的戏剧性,那就简直是糊涂到家。但有时我觉得那么多的古代戏剧家,他们把那些本来很普通的、其实并无分别的以文人为主人公的卖淫嫖娼写成文人与妓女可贵的爱情,恐怕并不完全是真糊涂,多是在装糊涂。
有时候这真糊涂与装糊涂是可以分辨的。以妓女为主人公的爱情故事并不是中国戏剧的专利,欧洲经典文学写公子哥儿与妓女之间的深情厚谊,同样是把妓女写得无比高尚的,至少是要强调妓女有高尚的心灵。小仲马的《茶花女》——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主人公阿芒爱妓女玛格丽特爱得死去活来最后还碰一鼻子灰,他有很多机会可以知道他无法拯救这位风尘女子却还不断地自作多情。反过来,作家笔下这妓女的心灵纯洁得超过圣母很多倍,天哪,那不是一般的高尚,读读她的遗书——“除了你的侮辱是你始终爱我的证据外,我似乎觉得你越是折磨我,等到你知道真相的那一天,我在你眼中也就会显得越加崇高。”如果小仲马不是用这样的笔法追求反讽的效果,那我觉得就有点像是真糊涂。至于托尔斯泰的《复活》,恐怕就是装糊涂的代表,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努力想要拯救堕落的风尘女子玛丝洛娃,然而他越是努力却越是清晰地看到,玛丝洛娃从来就不是他在心里所想象的那样的人,所以,聂赫留朵夫只不过是在拯救自己,他根本就救不了玛丝洛娃。因而,当作者也装模作样地写点玛丝洛娃的纯洁高尚的心灵之类文字时,不是在装糊涂又是什么。
在这样的装腔作势装模作样的背后,还有另外的意味,那就是文人要以一个整体的姿态为这个社会代言,坦承这个社会对人类两性间的情感关系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假如这个社会的两性关系,就只剩下或者是夫妻间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的单调乏味,或者是嫖客与妓女间更单调的买卖关系这两种极端的模式,那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要寻找更有情调更有韵致的两性情感并不容易,在一个婚外情被社会普遍排斥与鄙视的社会语境里,仿佛只有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女子,才有更大的书写与想象空间。现在当然不同了,现在以通奸为题材的艺术成为主流,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到《本能》,一波胜过一波。但是从前不是这样的,因此从前的艺术家只能写卖淫嫖娼,而选择以妓女而不是妻室来展开文学与戏剧的想象,这似乎是古今中外艺术家们的一场集体臆症。以我有限的阅读和欣赏,几乎没有对任何以夫妻生活为情爱题材的作品留下过什么印象,或许真的就是没有,唯一记得住的是沈复的《浮生六记》,哦,记错了,那不是文学,是回忆录之类的东西,虽然写得很像用文学青年们偏爱的笔法虚构的小说。
但这样的表达还需要有更多的元素,当你确定你的戏剧要涉及到这类边缘人的情爱关系时,不仅要以风情万种的妓女为女主人公,还需要寻找能够与之相对应能互动的男主人公,于是,文人墨客在这场选择中就得以顺利地胜出。既然要谈爱情而不只是简单的买卖关系,那就需要吟吟诗作作赋;既然不是单纯的生意,那么,妓女们早就习惯的嫖客们“子弟情肠甜如蜜”就不再够用了。你看,周舍虽然是个官宦人家的公子哥,对待宋美人的态度也不算差呀,他“暑月间扇子扇着你睡,冬月间着炭火煨,哪悉他寒色透重衣。吃饭处把匙头挑了筋共皮,出门去提领系整衣袂,戴头面整梳篦。”但是这样的体贴劲以及甜言蜜语,好像还不够有情致哎,好像与家庭生活太接近了吧,而且这与感情之类精神性的交往,总觉得还有些距离,因此非要琴棋书画才够意思。因此,商人与舍人们只好靠边站,还是需要文人们登场才是呀。
文人登场了,宋引章刚刚要跳入妓女从良故事中屡见不鲜的想象中的火坑,安秀才不失时机地出现而且情事受挫,于是像木偶一样成为赵盼儿书写色情从业人员嫖客治理大全时不可或缺的趁手工具。
文人在他们与妓女交往的情爱之路上受挫是反经典的叙述,而反经典正是经典之能成其为经典惯用的欲擒故纵的笔法,果然,故事的高潮由此开始蕴酿启动。如前所述,过不下周家苦日子的宋引章厚着脸皮修书求同门姐妹赵盼儿赶快搭救,她不是说吃不了苦想念当年自由自在的幸福日子了,她说是要请姐姐救命,而是因为她被“朝打暮骂,禁持不过。你来得早,还得见我,来得迟呵,不能勾见我面了!”说她必须厚起脸皮,是因为当时赵盼儿劝阻她时她是说过大话的,她赌咒说自己就算是死,“我也不来央告你”。到了真吃苦时,离死还远着呢,她就忘记或者是假装忘记了,但赵盼儿等的就是这句话。引章妹妹一求,赵盼儿终于证明了自己当时多有远见,觉得倍儿有面子,又加上前面有安秀才的请托,嘴里咕咕囔囔地抱怨了几声就又出马了,自信满满,“我索合再做个机谋。把这云环蝉鬓妆梳就〔还带上些锦绣衣服〕,珊瑚钩,芙蓉扣,扭捏的身子别样妖柔。我着这粉脸儿搭救你女骷髅。割舍得一不做二不休,拼了个由他咒也波咒,不是我说大口,怎出得我这烟月手。”
赵盼儿有什么本事要让周舍休了宋引章呢?说来也简单,用她的话说,“我到那里,三言两句,肯写休书,万事皆休。若是不肯写休书,我将他掐一掐,拈一拈,搂一搂,抱一抱。着那厮通体酥,遍体麻。将他鼻凹儿抹上一块砂糖,着那厮舔又舔不着,吃又吃不着,赚得那厮写了休书,引章将的休书来,淹的撇了。”果然,这位比宋引章更老到的风尘女赵盼儿到了郑州引周舍来酒店一起住下三天不归家,风情万种的手段一招紧似一招地使将出来,她甚至说自己非要嫁给周舍不可,诓道当年劝说宋引章不要嫁给周舍是出于自己对这位公子哥动了心的嫉妒,当然,嫁给周舍的前提,是要他休了宋引章。
周舍并不是个傻人,一出场周舍就声称他“酒肉场中三十载,花星整照二十年”,“自小上花台,做子弟”。要想骗得周舍上当并不那么容易,赵盼儿的手段在这位风月场上的高手面前,显然没有预想的那么见效。他并不肯轻易地写下这份休书,因为他知道休书一旦写下而赵盼儿又反悔,岂不是落得个“尖担两头脱”?于是,赵盼儿不得不使出最后的一招,那就是赌咒发誓,竟然说“你若休了媳妇,我若不嫁你呵,我着堂子里马踏杀,灯草打折膁儿骨。”一时轻信了她誓言的周舍真叫阴沟里翻船,而结果也正如他先前担心的那样。故事的结局,是他们相互牵扯着告到官里,赵盼儿说是自己早就做了保人将宋引章嫁给安秀才为妻,并且叫来安秀才做证见。于是周舍的行为就变成混赖别人媳妇强占有夫之妇的恶棍,况且一时受骗真写下了休书,更没有再霸占着宋引章的道理。郑州太守的司法判决,是周舍受到惩罚,安秀才与宋引章则结成夫妻。
这个故事最终的结局显然是不重要的,没有人关心宋美人和安秀才之间将来的生活究竟会怎样。其实他们将来的生活之离浪漫与幸福很遥远很遥远那是可以想象且可以确知的,按照戏里的描述,这位宋引章不止是在婚姻大事上如此地不聪明,而且还是一个十足的十三点。戏里有关这位宋美人的生活行止所述不多,仅有的两个小段子的描述让人笑破肚皮。一是说周舍娶了宋引章,从汴梁回郑州的路上,只见前面宋引章坐的轿子一直在晃晃悠悠,周舍以为是抬轿的小厮捉弄他的新欢,被他冤枉的小厮告诉他是轿里的人自己作怪。周舍“揭起轿帘一看,则见她精赤条条的在里面打筋斗。”二是说娶到了家里后,周舍让这位新进家门的女眷为自己套床被子,“我到房里,只见被子倒高似床。我便叫那妇人在哪里,则听得这被子里答应道,周舍,我在被子里面哩。我道在被子里面做什么,她道我套绵子,把我翻在里面了。我拿起棍子恰待要打,她道,周舍,打我不打紧,休打了隔壁王婆婆。我道好也,把邻舍都翻到被里面。”就算这两个段子夸张至极,至少赵盼儿是先后两次对周舍说到宋引章是个“针指油面、刺绣铺房、大裁小剪都不晓得一些儿”的和贤惠一点不沾边的女人,更谈不上为他生儿养女,但是赵盼儿没有说像安秀才这样的好男人把宋引章娶回家去有什么不妥。毕竟连周舍这样的浪荡公子,在他将宋引章娶回家时还因为要顾忌左邻右舍的闲话故意离开轿子一段路程,更何况安秀才。而且赵盼儿更分明知道,一般人家哪里能够容忍妓女从良从到自己家里,她不是也感叹道“好人家怎容这娼优”吗?书香门第对婚姻的道德期许总应该更高一点吧,安家怎么就会喜欢宋引章呢?万一娶回家后也要偶尔让她叠个被子之类?因而,她不是心下也觉得娼家姐妹们从良嫁人的前景并不美妙,“只怕吃了良家亏,还想娼家做”吗?“才出娼家门,便作良家妇”,风流快活地赚够了私房钱,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