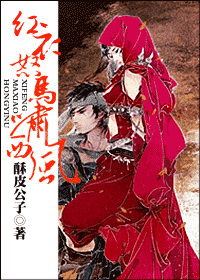怒马香车-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的话声未落,门外一声怪叫,寒风卷处,一个白发蓬飞的老婆子,已冲了进来。
那老婆子满脸都是疤痕,右眼已眇,但一只左目却是神光奕奕,显然是一位内功极具火候的高手。
她一进门,全听酒客,都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惊呼,部份酒客并怯生生地,由后门溜了出去。
那狐袍人却笑道:“这真是巧极了,说到曹操,曹操就到……”
青衫文士目注那老婆子,口中却向狐袍人问道:“阁下说的线索,就是这位老人家?”
狐袍人点点头道:“是的,那是一位疯婆子,咱们最好是当心一点。”
青衫文士蹙眉接道:“看样子,不像是一个神智不清的人呀!”
这当儿,那老婆子忽然向柜台上走了过去,向那掌柜的疾声问道:“嗨!掌柜的,你看到我儿子吗?”
那掌柜的一脸诚惶诚恐,连声苦笑着:“老人家,没有看到啊!”
“那么,你一定看到我孙子?”
“也没有!”
怪老婆突然转身过来,面对着大厅,独目中寒芒连闪,语声也突转凄厉:“你们自己说,谁是我的孙子,谁是我的儿子?”
狐袍人向青衫文士低声说道:“朋友,如果她找向我们,请由我来应付……”
他的话未说完,那怪老婆子已向他们的座位前走来,并厉声喝问道:“你们两个,为什么不说话?”
狐袍人含笑接道:“老人家,你要我说些什么呢?”
怪老婆子道:“告诉我,我的儿子,在哪儿?”
狐袍人笑了笑,道:“哦!老人家的儿子刚刚走……”
“向哪儿走的?”
“出大门,向左拐。”
“谢谢你……”
怪老婆子进来的时候像一阵风,走的时候却比风更快,话声未落,人影已消失于大门之外。
怪老婆子一走,那些还没走的酒客们,才如释重负似地,一齐长吁出声。
青衫文士也长叹一声之后,才向狐袍人注目问道:“朋友,为何要骗一个疯子?”
狐袍人苦笑了一下道:“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只有这一个办法才能将她引走。”
“否则呢?”
“否则,给她缠上,非死必伤,那是有冤没处申的。”
“当她找不到她的儿子时,不会再回来找你的麻烦?”
“那不可能,她一出门,就忘记了,即使还记得再回来找我,我也不会在这儿呀!”
略为停了一下,青衫文士才接着问道:“方才,老兄说的一丝线索,指的就是这个老婆子?”
“是的。”
“在下愿闻其详?”
狐袍人沉思接道:“方才我已经说过,杜老英雄是我的救命恩人,杜家的神秘失踪,是武林中近二十年来的一大疑案,我虽然力量有限,但基于一种感恩图报的心情,总希望能竭尽所能,聊效棉薄。”
青衫文士接道:“所以,这十年来,吾兄一定已在暗中下过不少功夫?”
狐袍人点点头道:“是的,但最初几年,可毫无绩效可言,一直到这位疯老婆子出现之后,才算有了一点线索,可是,由于她神智不清,却又无从着手。”
青衫文士注目问道:“阁下怎能断定,这位疯老婆子与社家的神秘失踪案有关呢?”
狐袍人道:“起初,我不过是下意识地判断她可能与杜家有关,因而特别将她引到杜家的废宅上去……”
“她有什么反应?”
反应很好,看情形,她对杜家庄的一切,似乎还有一点印象,但当我想向她问些什么时,却又疯疯癫癫地,语无伦次了。”
话锋略为一顿,才长叹一声,接道:“所以,我常常想,如果能有一位名医,将她的疯病治好,必然对杜家庄神秘失踪的疑案,大有助益。”
“这构想很有价值,可是,茫茫人海,到哪儿去找一位能够着手成春的名医呢?”
狐袍人苦笑一下,道:“这倒是实情,不瞒老兄说,我已经暗中替她请过好几位名医了。”
“结果都是徒劳无功?”
“唔……”
青衫文士沉思着问道:“阁下,这位疯老婆子,出现洛阳是什么时候的事?”
“大概是两三年以前的事,确实日期,已记不清楚。”
“她,落脚在什么地方?”
“居无定所……”
“不可能吧!看她衣衫整洁,可不像是一个居无定所的人。”
狐袍入微微一笑,说道:“兄台说得有理,但我说她居无定所,也完全景实情,不过,她之所以能衣衫整洁,却是因为有专人照应她的缘故……”
说到这里,忽有所忆地,“哦”了一声道:“对了,说到那位照应她的人,也算是一条有力线索,不过,要想由这条线索上查一个所以然出来,也算是难上加难。”
青衫文士苦笑道:“那位照应她的人,总不致于也是疯子吧?”
“虽然不是疯子,却也好不了多少。”
“此话怎讲?”
狐袍人道:“那是一个又聋又哑的残废人,一问三不知,逼急了,给你一拳,可吃不了兜着走。”
“那残废的武功也很高?”
“不但武功高,人也长得得挺标致的,这两年来,洛阳附近一些不知死活的登徒子,为了想吃天鹅肉而糊里胡涂送掉老命的,可大有人在哩……”
青衫文士“啊”了一声道:“想不到,那还是一个女的。”
“唔……”
“有多大年纪?”
“最多不会超过二十岁,还是一个姑娘家哩!”
“一个又丑又疯的老婆子,配上一个又聋又哑的美姑娘,这可的确是一宗颇富吸引力的新闻。”
“不错,开头一段时间中,的确是很轰动,但时间一久,也像那欲望香车一样,慢慢的也就引不起人家的兴趣了。”
“不过,对我个人而言,这两宗业已褪了色的新闻事件,还觉得很新鲜,也很具有吸引力。”
“两件事情都具有吸引力?”
“不错。”
“总该有个轻重之分吧?”
“那当然是那位疯婆子,更具份量。”
“这,是否是由于方才在下所提供的消息原因呢?”
“可以这么说。”
狐袍人苦笑道:“老兄,徒具兴趣,无济于事,必须有办法使她能恢复神智才行。”
青衫文士接道:“这个,在下倒有一半的把握,可以将那位疯婆子的病治好……”
“啊!想不到阁下还是一位名医,真是失敬得很。”
“阁下过奖了!其实,在下读书学剑,两无成就,对于医理,也不过走由于有兴趣,独自钻研,自信略具心得而已。”
一顿话锋,又蹙眉接道:“不过,如何才能使那位疯老婆子就范,接受治疗,这可是一个难题。”
狐袍人笑道:“不要紧,这问题包在我身上。”
“阁下计将安出?”
“可以由那个残废美姑娘身上着手,我已和她打过两次交道,已经勉强可以以手势交谈了。”
不等对方接腔,又注目问道:“青衫客,阁下是否已找好了歇宿之处?”
青衫人道:“没有啊!在下是刚刚入城,由于投亲不遇,才到这儿来借酒驱寒,顺便打听一下消息。”
“那么,就住在隔壁的悦来客栈好了,悦来栈与这太白酒楼是一个老板,要住店,跟这儿的堂倌招呼一声就行。”
“多谢指点!”
“在下暂时告辞,晚间再见……”
这位青衫文士,也许是由于有着太多的心事,自从他进入酒楼起,除了最初那下意识的目光,匆匆一扫之外,即未再去注意周围的事物。
可是就在距离他三副座头的座位上,却有一双清澈的眸子,不时地在向他愉愉注视着。
那是一位身穿紫色衫裙的妇人,与她同座的却是一位年约弱冠的少年人。
不过,由于这二位是坐在大厅中最偏僻,也是光线最黯淡的一角,因而即使特别注意,也不容易看清他们的庐山真面目。
当然,像青衫文士这么根本不注意别人的人,自然更不知道暗中有人注意他了。
当他向堂倌招呼着,准备要一间清静的上房时,那暗中向他注意着的紫衣妇人和年轻人已悄然离去。
不久,青衫文士也在堂倌的前导下,走向隔壁的悦来客栈。
“爷,这是本店最好的一间上房,小的猜想你一定会满意的。”一进门,店小二就大献殷勤地谄笑着。
“唔,马马虎虎。”青衫文士口中漫应着,游目四顾。
忽然,他目光一亮,走向床头的墙壁前,并“啊”了一声道:“好一手佑军狂草!”
接着,却曼声吟哦起来:
廿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
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
尘满面,鬓如霜……
那是苏轼所作的“江城子”,但却只录了前半阕,而且将第一个字的“十”字改成“廿”字。
这一字之易,似乎恰搔着青衫文士的痒处,使得他特加激赏,曼声吟哦间,那本来充满着忧郁的双目中已涌现出蒙蒙泪光。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难道说,这位青衫文士,竟然是一位别有怀抱的伤心人吗?
店小二尚未发觉青衫文士的反常神态,只是轻轻一“咦”道:“这是谁写上去的?”
青衫文士问道:“小二哥,以前你没有发现?”
店小二道:“是的,早晨打扫房间时,我都不曾发现。”
“昨夜住在这儿的是什么人?”
“那是一位年约六旬的老人家,一早就走了。”
“隔壁还住有客人吗?”青衫文士抬手向左右隔壁一指。
“右边房间现在还有空着,左边是堆放杂物的储藏室,不住客人的。”店小二苦笑了一下,接道:“小的将它擦拭掉。”
“不!”青衫文士连忙接道:“人家写在这儿作纪念的,你就让它留下吧!”
店小二退出之后,青衫文士关上房门,目注那半阕古词,怔怔地出起神来。
半晌,他才低声喃喃自语道:“奇怪?墨迹犹新,显然没超过半个时辰,那是什么人题的呢?……为什么要将“十”牢易改为“廿”字?……难道说是为我而改的?也是为我而题的?并且事先知道我要住在这一个房间,……那是什么人呢?”
接着,又自我解嘲地苦笑道:“别疑神疑鬼的了,这显然是一种巧合,否则,至少这笔迹我应该有点印象才对。”
尽管他自我宽慰著作了一番合理的解释,但他还是不甘心地,在房间内作了一次细密搜查,一直到他认为别无可疑之处后,才和衣躺了下去。
人是躺下了,但脑子却并未休息,不过,他的脑子在想些什么,就只有他自己明白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室内已经一片漆黑,店小二提着灯,唉门而入,后面还跟着那位狐袍人。
狐袍人一见面就歉笑道:“青衫老兄,很抱歉,打搅你的清梦了。”
青衫文士笑道:“事实上,我根本没有睡着!”
接着,又注目问道:“老兄,怎么样?”
狐袍人道:“人已经找着了,外面雪很大,我已经准备了马车,老兄是否须要先吃点东西?”
“不用了,回头再吃吧……”
说着,提起他那只旧书箱,相偕走了出房去。
不错,雪很大,大街已有尺厚的积雪,鹅掌大的雪花,还在纷纷飞舞着。
约莫顿饭工夫过后,马车戛然而止,狐袍人含笑说道:“到了。”
相偕下车之后,青衫文士发现是在一幢极普通的三合院前,狐袍人当先带路,道:“老兄请跟我来……”
进入右厢房中一间起居室中,一位双十年华的美艳少女,正以冷漠的眼神迎接他们。
她,的确是够美的,不论身裁,面目,肤色,一切的一切,都长得那么恰到好处。可惜表情就是太冷,真算得上是艳如桃李,冷若冰霜。
狐袍人接连向她打了几个手势,青衫文士也约略地看得出来,那些手势都是在替他介绍着,表示也是前来替疯老婆子冶病的。
那冷艳少女向青衫文士深深注视了少顷之后,才点点头,转身走向里面房间的门口。
狐袍人压低语声,说道:“青衫客兄,我特别提醒你一声,因这丫头天生残废,喜怒无常,武功又奇高,你得随时当心她对你有不利的行动。”
这当儿,那通往里间的房门已被冷艳少女打开,一股刺鼻血腥气也随之冲出。
青衫文士与狐袍人同时脸色为之大变,狐袍人并疾声喝道:“兄台当心!”
那冷艳少女仍然是一片冷漠,并向他们打了一个“请进去”的手势。
事实上,房门一开的那一剎那间,青衫文士已看清楚了室内的一切,并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
炕床上,那满脸疤痕的疯老婆子,己身首异地,横尸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