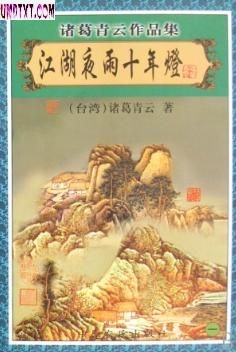��·��-��32��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Ҹ�١�һ�����ļ����������������ʢլȥ�������ϵ������������ļ�Ҳ���Ҷ��������е������ܲ������ļҡ����ļҵ������˼��߶���ͼ��ʳ��Ū��Ǯ�����Ѵ������������ʲô���е�ϲ��ǰͷ�������һͬ��ʢ�����ʡ�����ϲ�������������������д�����������˴���ؼң��ߵĶ�ʱ�ˡ�˫�찳�������˷�˯��������̾�������ȣ�һ����ȫ��֪�����粻Ȼ�ߣ���ͬ���鵽ʢլ��ȥ������һ�ʾ������ؾ��š������ϼ�����˵������������ġ����е���ͬ��ϲ�������ȥʢլ����������Ϣ��һ�Ҷ���Ƶ��š��Դ�������в�ض�Ժ������˯����
�������ϵȵ����������顢��ϲ������˵����ʢլ��û���Ӱ������������Թ����������Ȳ��������ң���β������������ϲ����������ʢլ�����Ϻ尳��˵��������ҡ��������ţ����ý�ȥ�����˶����������ŵý�ȥ��ֻ��������ͣ���������Ů�ˣ�����������ɫ�ӡ������´��������˯�ˣ�����ʢ��үһ����ʢ��ү�յ��˲��ã�˵������ү��������Ϸ��������������ô������ҹ����ȴ������Ѱ���������dz���ʱ�������������ˡ������ǰ��������ţ�����Ҳ��ɫ�ӵ������м䣬�Ǹ����˵����ˡ��Ѿ����ٴ��࣬�ſ����ţ����Dzŵû�����������ײ��һλ��ү��ҹ���Ѱ������������̣�ֻ˵����ҹ������˵����ǽ��̷լ������ү������ү���֣���˵���ϼ���������ү���ͷ���������������ˡ��ٲ��Һ�ҹ�ڽ����ߡ�������Ҳû���ˣ�ֻ˵������ҹ���ˣ�����˯�ա��������Ի���������ϲ����ȥ�˷���ͬ˫���˯ȥ��
������˵�����лص����У����Դ������������Щʱ���ˣ����м�Ϸ�ӵ��£���Ҳ֪��Щ��ô�����Դ������������£������֪����ֻ��һ��Ϸ�����˲ľ���Ů��һ����ÿ����¥�½����̣��иɵ���Ҫ��Ҫ�ߡ���˵��δ�꣬���л��������������Դ��Ҳ�Ͳ�����˵�ˡ����в���һ�ᣬ˯�ڴ��ϣ��ۿ��ŵƣ�һ�����ٲ����ֻ��ҡͷ���Դ���¼����ʵ������������ģ���������Ц�������Կڲ�ա����Դ�����ŷ��ġ���������������Դ��Ҳ�ʹ��Ƿ��˯���������ˡ�
���������е��ײ�֪С�������Ҳ������������������˷��ţ���ɫ�续������ɡ������¥Ժ���ţ������ſ��š�ԭ�ǵ�ϲ����ǰԺ��ҹ��û����˩�������Ľ����ţ���¥�ϴ�ֽ���ţ����������������Dz��������⾰���������ģ���һ��һ���ģ��ߵ�ǰԺ��ֻ�����º�Ӱ���������Σ����Ŵ���һƬ��ɫֱ���˰���������Т�������ֶ���һ��һ�Ŷ����ϵó��ġ����п�������⾰���̲�ס�������ᣬ�������ᣬϸϸ�Ŀ���һ����������ү����ү��Ϊ�δ���̫�磬���ٶ��ꣿ���ү���գ���������ι⾰����ү���ں�������ι⾰������һ�����ˣ�����ʲô��������������������£����������Ŀ�������ɡ������ש�ص��˼��¡�
������˵���ϵ�����ţ��ȶ��Ӳ�������������¥�ţ���ҹ������ֻ������������ϡ������������ש�ػ��졣�ŵİ�¥�Ž��գ��ѱ�÷������������š����й�������Ҳ����˵������
���������п���һ�ᣬ�������Ʋ������ط�ȥ˯������֪��¥���¹�����ڡ�
���������գ���ϲ����˫�������Ժ���������ʵ�����������ҹ������ʲô����������ϲ����������˯���������������ү�����������µļ��ˣ�����˫����DZ�һͷ˯������ֻ�dz�����������������˯ȥ���������˷�������ϼ��е�ϲ����Щֽ������������С���ǵ�������ǰ���ˡ�ף��������úö��գ������ź����ǡ����ȣ���̷����ѽ������֪���˺��д���̨�£���ĸ���꼸���ɣ��뿴������ָ�У�ɽ����Ӧ����Υ��
��������������ֽ��������ҪѰ���ӡ�����������ʱ�����������ղų����������ų���������¥�������Ļ���ҹ����ð�纮�������j��һ����������ˣ��Ѿɲ�֢������Ȼͷ�۶��ģ��������ȣ��������ˡ�
����������û�����ֽе�ϲ����ȥ�ķ�����Ѱȥ�����ϲ��ȥ��������а�֣��ʽ������������ˣ��ϵ��ķ����Ż���������ǰ������һ�����������ڼ�ô����ֻ��һ�������������ʵ����������ǵģ�����ϲ������������ǽ��̷լ���ˣ�������һ�仰���������������������죬���γ����ҵ���Ӱ����������û�ף���û��֪������ȥ�ˡ���ֻ��Ժ������ٸ�������˵����������ȥ��¿�Ĺ���������ȥ�������������������˼�Ц���������Ż�ȥ�ˡ�
������ϲֻ�û������ظ���ĸ������һ���ż����ֽ�˫���ȥ���־�ү��Ѱȥ��ȥ��һ�Σ���¡��Ҳ�����������˹���˵����������������ȥ�ˣ��ҽ���ʢլȥ�ʣ�˫��˵��������ʢլ�ʹ�����������β�ȥ�Ĵ������ȥ��һ���������ϵ������ʵIJŻ���������˵�����Ķ���Ҳ�����������졣��¡�������������ͷ��İա��ض����Ĵ��������˭�����棬�˼�֪������ǽ��̷լ����û�и���������������˵������ס�ˡ������Ĵ���ڼ�ʱ���Ҿ�������ż������Ȳ��ڼң���Ҳ�����¡���������ֶ��˵�Ļ��������Է���Щ����˵���������ֵ���һ·��o�����ȥ����ѰһѰ����¡���������ҵ����Ļ����������ҵ�Ҳ�ؼ�����˫����ʲ�Ҳ�����ſ������������������ջ���һ��˵���ܲ������һ��ˣ������ܵ����ʡ�ֻ˵�Ĵ��Ҳû�ڼң�������ܲ������ˡ��һ�ȥ�գ�����ֻ�ܷ��ġ���¡�����˹����ȥ��
��������Ҳ���߷ֲ��ţ����ķ�������ȥ�ˡ����˵���һ�죬������һ����ƻ裬�������������ɼ���������ȴ���¹�������б�÷˩��¥��˯����˯���ţ�����ֻ�Ǻ����㣺������ˮ���ھ�����߹��ż��º�ȥ��������ͻ��ᣬ�����˹մ�ȥ�������·��ĺã��������Ѱ��ˡ���ֱ�����ʱ����˼ƣ��������˯�š�һ��������������������㡣���ǣ�
������������˸��ģ����д粽˼ǧѰ��
�����������������⣬���ϼ���������
�������˴��գ����ϼ����������е�ϲ����������ȥ¦����������ȥ������ϲ������������ȥ�������ϵ�����һʱ��ͷײ������������ʦ���������ң�Ҳ�Dz��Ҷ��ġ�����ϲ������ȥҲ����ס�������졣�����ϵ�����ֻ��ȥ���ʣ��߲�����Ľţ���Ҫ����������ϲ�ٲ����ϱ����������˰��ջ�����˵������¦ʦү����û�С���ȥ��¦ʦү�����������Ժ�����������
�������ϵ��������ӽ�ѧ����ţ�����ʲô�����й���ô����û����Ϊɶ�أ�����ϲ�������Ҳ�֪����ֻ��ʦү�µ�˵������Ͳ����������֣�����ֻ����һ�䣬��֪��Ϊɶ�������ϵ��������ˡ����û������ô������ϲ�����������и�Ӱ����������û����ֻ����������Ȼ��
���������ս���ʱ�����Ű���������û��û˼���ϵ�¥�������ϼ��ˣ�����䱦һ�㣬˵�������ҵĺ��ӣ���������ȥ�ˣ��ò�Ѱ�����������ŵ�����¦�����ǡ�����ֻ˵���ĸ��֣����ϵ�������ϲ���Ŵӱ�����Ѱ��������������ֵ����������أ���
�������ϵ������������ˣ��������������
��������������һֱ����ǰԺ�������˴��ţ���һ������麺�ӵ��˷������ڷ������������˰�Ǯ�����ˡ����������Ѹ���ǰԺ�������ʵ�����������ʲô�������ŵ�������ˮ���Ŵ��Ҫ���ʮ��Ǯ���ҳ������ˡ����ʹ��С�������ơ������ϵ������Ҳ��š��ۻ�ûһ��Ǯʹ��Ϊ���Ľ����˼��߰�ʮ�����Ҳ������¡������ŵ������ҳ������ˣ�ͬ���Ĵ�硣����ʮ��ͻ������������ϵ������Ҳ�����������������Ҳ������¡���
������ȥ�˷�����һ�������ŵ����������ȥ������ʲô��أ���
�������ϵ�������ز���أ��Ҳ��а���Ǯ����������֪�������ڴ����⿴�ų��ӣ�������Ǯ�����д�ӷ���������Ǯ�ĺں��������������ӥȮ��ר�����ֶIJ��ˣ��Ҵ��Ҫ���ºŶ������������ӡ�����˵��������̷�ģ���ȵ����ļң��Ͳ��ýа��Ƴ�������Ϊʲô��������һ���ϣ������ߣ�������������ȥ�ա������ŷ�������סĸ���������������ȥ�ա�����ɶ�⾰�������˼�Ц���������ϵ������һ��ţ����ɲ���������������ǿ�ڵ������ɵ����ˣ��������һ��ѷ��������������ˣ�Ҳû�˰������ģ������������ˣ�Ӳ��ס�ţ�˵�����ҿ�����˭�Ұ�Ǯ���������������������Ц��һ����ֻ�ܱ���Ǯ�����г�����Ŀ��˵��ʮ�崮����ʮ��������Ӳ�������Ͽ���û�н�ȣ�ֻ�ö㿪���ӻ�ȥ���ϵ�¥��������ү��һ����ޡ�
���������Ŵ����ʮ��Ǯ���ż��Ƴ����ˡ���ס���ţ�ֻ�ڿ���Ժ�����һ������ǻ�һ�أ����������ϵ�¥����˵��������ʵ���ã���ʵ���ã��Ҿ����գ�����ͷ��ǽ��һ�ᣬ���ڵ��£�ֱ��������ϴ�ţ�ס�˿�������ס���ŵ�ͷ���е�����С��������Ǯ��ֵʲô������Ҫ���ң��ҵĹԺ���ѽ���������ң����DZ�÷Ҳ�˲������ϲ��㣬��ȥ���£��ݵĽ������ࡣ
�����������������ף�ҧס���أ�һ�ڲ�Ҳ�����ʡ����Ͽ��˵������ҵĶ�ѽ�����������ҡ���������˭�������Դ�������������أ�����һ�����裬���ŷ��ź�������������һ�ᣬ���ְ���һ�ڣ�˵���������ݼ��ҡ��������ʵ������������ӣ�����������ô�������ŵ��˵�ͷ�����������������Ű���һ������Ϣ���ٵĵ����������ڼ䴲��˯ȥ������Ȼ�Դ������÷���ţ��������������������˯����������ע���ͣ�����Ԥ���ϲ裬��Ҷ�����������ס����ۡ���������Ԥ��ͣ������������ˣ����á�
����������˯�˰�ҹ��ƽ���Ѹ����ƹ�֮�£�����ĸ���۾���������������Լ������ķ��֣������ĵ��������Ķ����㺦���Һú�Ҳ���������ǣ�
�����Թ�����ҹ����������������������
���������춺������������ţɽľ�ֲ�����
��
�ڶ�ʮ���ء���������־���Ĺ��������Ѱ����ٷַ�
��
������˵̷���������һ��ƽ��֮�����������в��ԣ��������������̷��Ҳ���������ң�������Ҳ�����й����徭����Ϊ���ĵ����������֮�ң����������ֲ�Ф֮�£���ͬ��������ĸ�ף����ͼҲƣ�ĸ���ӣ������֮�ӣ���ҹ�������ۣ��ٰ㸧Ħ������������������֮ʱ�������������Ķ��飬�����ˡ��Ļ������ҽ�����ʮ�˾��꣬��˵һ�����²�ʡô�������Ϻ�ʹ��������˫�Ტ��������ףһ���ֳ�סĸ���֣�����һ����������ٲ����ˣ������ϵ��������������ʲô�����������Ż��������Dz����ã���������ȥ��������������ĸ�������������ʹ����裬�����Լ����Լ�һ��ɱ�ˣ�����������㲻��һ�����ˡ������ϵ������Լ����ӣ�ûɶ��˼��˭��ţ������ĸ��˭�Ҷ��Ӳ������ֻ�úõģ����߰�ʮ��Ǯֵʲô����������Ҳ̫���������ҡ�����̷����Խ������һ�仰��Ҳ������
������÷���ˣ������Ը�������������һ����ˮ������һ�����ۣ��������š������ʣ������ж��ʱ���ˣ������ϵ�������ֽ�ǵ����ţ����Ѵ����������ŵ�������Ҫȥ������ȥ�������ϵ��������dz����IJ�����Ⱦ���㡣�����ŵ������Ҳ��¡����������ۼ�һ���ü��ˡ������ʱ�������Ҷ�Ȼû�����¡���Ҫȥ������ȥ�������ϵ������Dz�Ⱦ�ˡ����Ҫȥ������ʱȥ�����Щ�������ٳ����Ѿƶ����д�������г��������Ͳ��ܳ��������������������վƣ��ϲ�����Ҷ�����������ͳ���������˵��һ�����˾��Ǻã�Ҳ���������˼ҵ������������Ҳ�����𡣡����ŵ�����������˵����ʱ�����ա���
������ʱ���Դ�����������ϰ��⻰��˵���Դ���ط����Ѵ��Ҫ�������Ļ��������У��������ڰ���������Ҳ���档���������Ū��ʲô����������û�����⣬����������˵��Ҳ���еġ��������Դ���������㷢������ȥ�����ҵ���¥�£�����˵�������ⲡ��Ⱦ�ˣ����ɽд�����������������Դ�����������㲻�ܶ��ơ������е������Ͼ����ƴ�ǰ��һ�����������������¡����Դ����Ȼ�����ɷ�����������Щ�붫��������ɡ�������ŵ�¥Ժ������˵�����������¥��˵������
�����������������������������

![[250]�ƺ���̷���](http://www.9qudu.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