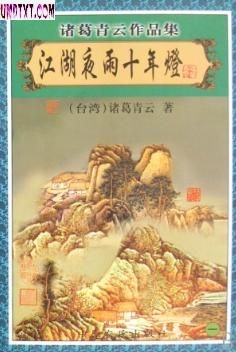读者十年精华-第79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古比雪夫大街飘着雪花,在每一个通往克里姆林宫的路口,我都看见有两名身穿呢大衣、头戴毛皮帽的年轻人,我知道他们是保安人员。15个月前勃列日涅夫逝世时,夜晚的街道上我也看到过相同的景象。如果不是执行任务,谁会有闲情逸致在这样严寒刺骨的夜晚在街上逛荡呢?
我到达南斯拉夫通讯社的时候,斯坦尼克正襟危坐地在听着收音机,我想他一定跟我一样,也感觉到这个城市有某些异常的情况。“很可能是头头。”他说。我们一起分析所有异常的情况,找出各种各样的解释。我说,30分钟之后,广播电台对在西伯利亚建造铁路的青年广播节目就要开始播音,因为那个地方离莫斯科有6个或8个时区。如果这次广播把固定的5分钟幽默滑稽内容撤换,改播古典音乐的话,事情就会更明朗了。斯坦尼克同意我的看法。
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打开收音机,静待对西伯利亚建造铁路的青年的节目开始。当我听到广播开始播放的是古典吉他音乐时,我感到可以给华盛顿的报馆打电传电报了。处理电传的是报馆的外事编辑部副主任利克,我用暗语通过电传告诉他,我想发一则重要新闻,这条新闻同我在1982年11月10日发的新闻同样重要。
利克明白我指的是勃列日涅夫去世的日期。
无线电广播的音乐越来越抑郁了。我开始坐下来写新闻。当然,我的用辞还是留有余地的,尽管我相信我的分析不会有错。我在新闻的开头,报道苏联电视台在晚上8时过后突然把预先安排的节目换成古典音乐,后来无线电广播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联系到安德罗波夫的长期生病,我认为这个国家目前处于紧急情况之中,1982年11月9日,勃列日涅夫逝世的讣告广播之前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形。接着我报道了许多迹象来证实我的推测安德罗波夫在星期四这一天逝世,我发完新闻准备睡觉时已是天将破晓,我的半导体收音机传出了凄惋的音乐。
在我入睡以后,华盛顿却展开了另一个故事。
报馆的编辑副主任接到我通过电传发过去的新闻之后,立即请邮报的编辑、记者们分头同白宫、中央情报局、国务院以及其他一些机构联系,询问这些机关是否通过他们各自的渠道已经获悉这个消息。各机关的回答都说未曾接到这件事的报告。尽管如此,邮报的编辑还是决定把我的新闻登在头版。就在这天夜晚,有几位邮报的编辑、记者出席了国务院举行的一次晚餐会。参加晚餐会的名流有国务卿舒尔茨,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和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一位编辑把邮报第二天一早将要见报的我发的新闻当面向多勃雷宁大使核实,这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笑着说:“得啦!他会死在这些谣言上。”
但是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说他要去核实这个消息。就在晚餐会行将结束的时候,他通知《华盛顿邮报》的一位经理说,我发的消息不确。伊格尔伯格说他曾将这条新闻向驻莫斯科的美国大使核实,那位美国大使开玩笑说:“想必杜德尔喝多了。”鉴于这样的情况,邮报决定把新闻从头版移到第28版,并且把语气也做了一些改动。
上述这些情形我都不知道。当我上午一觉醒来,我们的苏联女佣告诉我,安德罗波夫的讣闻即将宣布,当局已经把这个消息广为传播了。我立即打电话给南通社的斯坦尼克。他告诉我,他的通讯社没有采用他发回去的新闻。他祝贺我捷足先登。
Number:3144
Title:哈木哈木
作者:张伯笠
出处《读者》:总第79期
Provenance:报告文学
Date:1987。1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一
拜拜,北京!拜拜了,我的媳妇、闺女!
坐飞机出国,够刺激吧?现如今有知识的可以出国留学,有好爹好妈的可以出国刷上点金色,有漂亮脸蛋的可以找个高鼻子丈夫……这些我都不沾边,咱也坐上飞机出国了?我是出劳务,说白了就是到外国干活,为国家挣钱。
临上飞机前,我那口子还当着众人亲了我一口,两只眼睛哭得像红灯笼。就好像我再也回不来了。
我在巴格达机场下飞机后,坐了六个小时的汽车,来到了我们参加施工的摩苏尔水坝工地。摩苏尔水坝就在底格里斯河中游的一个天然回弯的地方。
摩苏尔水坝是吉摩德跨国公司承揽的工程,这里有德国人、美国人、日本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泰国人。中国土木工程公司的头头把我和边永宽,姜桂玉、刘尔源分配到美国尤可力跨国公司吉摩德修配厂尤可力底盘车间。头头一本正经地给我们讲了一大套注意事项。无非是要和外国人搞好关系,不要干丧失国格人格的事等等。
还是说我们吧。我们四个人一进修理车间,还真吓了一大跳尤可力自动翻斗车还真够个儿,甭说别的,光车轱辘就二米五高,站在汽车驾驶台的踏板上就可以登上二层楼。看着这庞然大物,我心里还真发毛。这么大的车,甭说修,连见都没见过!
我们车间除了四名美国人外,还有一百多名印度、巴基斯坦和老挝的劳务工人,刚开始,我们本着善良和友爱的愿望,想同各国的工人友好相处,但渐渐地,我发现:这里小瞧我们中国工人。
总工长是个印度人,叫维坚;副总工长是巴基斯坦人。这两个家伙一直不给我们分配修理工作,尽让我们干杂活。尤其是维坚,他干完活,扔了满地棉纱后就抱着肩膀,摸着满脸络腮胡子嚷:“China扫地去!China倒垃圾!”
“China?”英语我一句听不懂,咱哈尔滨当时尽学俄语,哪知道这“查依那”是啥呀!我去问翻译同志,翻译告诉我:China是英语中国!
中国?!我当时只觉得头嗡的一下子,两眼直冒金花。维坚这个王八蛋,他刚才是说中国,扫地去!中国,倒垃圾!我火冒三丈,拳头攥得格格响,我真恨不得一拳把维坚的脑袋敲碎!在国内,我从来没有想到祖国怎么样,这是我活了三十五岁第一次和祖国联系在一起,我卞玉玺这一百多斤值不了几个钱,可是祖国啊,我怎么能在这儿给您丢人现眼!
不过,话说回来,咱们国家不正之风很严重,在出国劳务人员的挑选上不是看技术,而是看有没有后台,这就很难保证出国劳务人员的技术素质。外国人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所以,在摩苏尔水坝,脏活累活都让我们中国人干,技术活和轻巧活都是他们外国人干。咱们出劳务的同志多数不会英语,这就吃了不少亏。一次,一个中国司机开车取料,料厂老板同他比划了半天他也没听明白到哪去装货,料厂老板一气之下,写了一张纸条让他带回来了。这个司机回驻地把纸条交给德国经理,那个德国经理看完后拍着他的肩膀哈哈大笑。原来,那纸条上用英文写着:他是个笨猪,你下次不要让他来领料了!当这个司机知道了纸条上写的内容后,跑到底格里斯河边,痛苦地揪着自己的头发号啕大哭。他喊着:“祖国呀,我给你丢人呐!”要不是哥儿们把他拽回来,这个烈性汉子说不定要干出啥可怕的事。
我这个人怪就怪在这儿,与其生别人气,不如自个长志气,学外语!从那以后,我就让翻译把所有常用的技术用语和日常用语写在卡片上,然后用汉字标上发音。
我和边永宽、姜桂玉、刘尔源四人规定谁也不准拿老婆的信看个没完,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学外语。床头、墙上、到处贴满了英语单词卡片;吃饭、睡觉、上厕所;早起、晚睡、多念、多练;英语、德语、斯里梵里语,天天像念经似的。学习真是个遭罪的事,腮帮子念得又酸又疼,嗓子也练肿了,打针消消炎,再练!还别说,两个月后,我们哥四个就可以用英语对话了。至于德语和斯里梵里语也能辨个差不离。
中国工人是最有潜力和创造力的,但是中国工人往往在缺乏信心的情况下,不能很好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我心里有气,气鼓得足,信心也足。语言关过去了不是目的,我的目的是要在技术上超过外国人!让他们看一看,中国人是不容小看的!
二
在吉摩德跨国公司尤可力修配厂,在这个各国激烈争信誉、争市场、争地盘的世界里,技术保密得像一堵坚固的围墙,这技术关比语言关更难突破。工作时,一到拆装关键部位时,印度人总是先把我们中国工人支走,等我们干杂活回来,他们该装的装了,该卸的卸了。这没啥了不起。关键是尤可力车我们没修过。从这以后,他们外国人拆装关键部位时,我们就躲在一旁边干活边留心瞄着,记在心上。上班前和下班后,我悄悄地到车间测数据,把尤可力汽车的图纸和数据背得滚瓜烂熟。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我们完全掌握了尤可力汽车的构造和性能,同时能熟练地使用英制四分尺和各种表。
有一次,维坚又让我们给他扫地,老边再也忍不住了,老边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地是你干活弄脏的,凭什么让我们扫?”我在一旁抱着膀敲边鼓:“维坚先生,请记住,我们和你一样,是技术工人!”维坚一看我们的架式,怕挨揍,屁滚尿流地找美国经理告状去了。
不一会儿,美国经理吉姆·布朗怒气冲冲地走进车间,他指责我们说:“让你们干活为什么不干?”我用英语回答说:“经理先生,中国工人从来不偷懒,刚才的事责任不在我们。维坚先生分活不均,他从来不让我们修车,却无礼让我们扫垃圾。我们是修理工,并不是贵公司聘来的扫地工!”
吉姆·布朗听后火冒三丈,他瞪圆蓝眼珠对维坚嚷:“是你分配活不均,你如果再这样做我就开除你!”说完扔下维坚,扬长而去。
维坚无奈,但又不甘心,他眼珠转了转,阴阳怪气地对我说:“卞先生,如果你非要修车,那就请把这台车的减速器装上吧!”
我们终于争得了一次修车的机会。按尤可力公司规定,减速器间隙必须在三至十英丝之间,维坚安装时,也只敢调到八英丝。我知道维坚是想让我们丢丢丑,但他想错了!我对老边说:“边师傅,咱们争口气,让老外看看查依那(中国)的技术!我大胆地把间隙调到了四英丝。
车修完了,维坚又来找麻烦。他坚持让我们卸下来给他看看。这小子欺人太甚!我就是不卸。他无奈又把吉姆·布朗经理找来了。
吉姆又象个胖鸭子似地跑来:“你们为什么不听工长的话?我要解雇你们!”
我沉着地说:“吉姆先生,我们把车修好了,完全符合贵公司的技术要求。并不存在什么不听话问题。”
吉姆·布朗怀疑地看了看我们,把工程师门德尔叫来了,然后命令我们把减速器卸下来。
门德尔工程师量完间隙后,高兴地伸出了大拇指说:“OK!OK!再也没有比这更漂亮的技术了!”
吉姆·布朗经理也很高兴,他友好地和我握握手,然后对维坚说:“中国工人有很好的技术,以后他们修车你就不用管了!”
带着胜利的喜悦,我们跑到底格里斯河边。时值盛夏,温度高达五十多摄氏度。荒原的野草、野花全部枯干了,这哪能和我们家乡比哩!哈尔滨,我们的哈尔滨这会儿正是迷人的夏天,真想家呀!在家时,总觉得家乡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可一到了异国他乡,家乡的一切都是那样使人眷恋难忘。
突然,老边快活地喊起来:“快看,那儿有花!”我没好气地说:“石头都烤得快能蹦出小鸡崽了,哪来的花哟!”
老边来犟劲了:“我这么大年龄和你们年轻人开啥玩笑!”我顺老边手指的方向一看,奇了,还真有一簇野花,开得鲜嫩鲜嫩的。我跑过去,扑下身,越看越喜欢,挺拔的枝芽长满了刺,小小的花朵迎着烈日不屈地开放,深深的根扎在滚烫的沙砾里!从此后,我就喜欢上这小花了。每天都要跑到山上采一簇,插在酒瓶子里,放在床头柜上。听一个业余诗人说,这花叫哈木哈木,它生命力极强,不怕狂风,不怕烈日,扎根石缝,不屈不挠!
啊,哈木哈木!我们难道就不能学哈木哈木的精神,在这异国的国土上扎根开花吗!
三
听说我们和维坚发生了几次冲突,中方一位小头头找到我们,他迈着鸭子步,扯着公鸡嗓对我们说:“你们要和外国人搞好关系,否则你们被解雇了,飞机票自己掏腰包买!”我问:“你说该咋搞好关系?”他说:“骂不还口”!我问:“那打呢?”他把眼珠一瞪:“打不还手!”我当时就火了:“放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