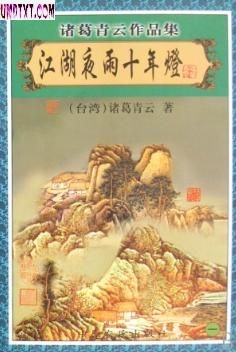读者十年精华-第39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家老幼10人下乡暂避一时。从此,他开始了8年动乱的逃难生活。
他说:“我虽未能真的投笔从戎,但我相信以笔代枪,凭我五寸不烂之笔,努力从事文化宣传,可使民众加深对暴寇之痛恨。”有一天,丰子恺在武昌乡间看见田野中有一棵大树,被人砍伐了大半,只剩下一根主干。这时正值春天,那主干上怒抽枝条,竟也长得枝叶茂盛。其中有的新枝条甚至超过其他大树的顶,仿佛是在为被砍去的“同根枝”争气复仇。他后来提笔把这情景画出来,象征中华民族,并题上自己所作的一首诗:“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
1938年春,丰子恺在汉口得到缘缘堂被毁的消息,这对他来说是巨大的打击。这时候,恰好桂林师范的校长唐现之来信聘请丰子恺去该校任教。丰子恺于是带着全家迁往桂林。后来,他又转往广西宜山江大学任教,并随校迁到贵州遵义。1942年,他搬到重庆郊区的沙坪坝,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沙坪小屋建成后,丰子恺便辞去教职,从此专为卖画写作为生。
抗战胜利次年,丰子恺搭轮船由长江而下,到南京改搭火车。丰子恺踏上阔别十年的上海时,说:“我从京沪火车跨到月台上的时候,第一脚特别踏着重些,好比同它握手。”
他去故乡石门湾凭吊。这个船舶麇集、商贾辐辏的热闹城镇,如今已经面目全非了。胜利还乡的满怀喜悦心情终于渐渐地消失殆尽,他对当时的社会十分不满,深恶痛绝。他引用古人“恶岁诗人无好语”的话,声称自己“现在正是恶岁画家”,但又觉得这种触目惊心的画不宜多画,希望自己的笔“从人生转向自然”。
1949年大陆解放,丰子恺52岁了。此后他专事著译。他在68岁时,完成《护生画集》第五集。69岁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时他住在止海。大字报,逼供信,抄家,关“牛棚”,紧缩住房,下乡劳动,写不尽的检讨交代,批斗,挂牌,游街,克扣工资,丰子恺备受种种精神上的侮辱和肉体上的摧残。
但他横下一条心,把坐“牛棚”看作参禅,把批斗看作演戏。夜晚过黄浦江去游斗,他说是“浦江夜游”;在“牛棚”中被叫去训话,他好像是去上一回厕所,回到“牛棚”照旧与画师门谈笑风生,或偷偷地作诗填词。到上海南郊劳动,冷天睡在铺稻草的泥地上,屋顶隙缝中飘下来的雪积在他枕边,70多岁的老人早上还得亲自到河埠打水洗脸,但他风趣地说:“地当床,天当被,还有一河浜洗脸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回到家里,不管白天发生过天大的事,也只是轻描淡写地叙述一遍,有时甚至避而不谈,只要一斤黄酒入肚,仍是吟诗诵词,谈笑自若。
然而,热爱这位老画家的作品的人,却时刻惴惴不安地关心着他的行踪、境况。当老画家奉命爬上竹梯去贴批判自己的“大批判专栏”时,围观的路人中有不少人暗自替这位老人担心。丰子恺虽然被批成“反革命黑画家”,实际上群众心底里对他更加增添了仰慕之情。
1974年“四人帮”借批大儒为名,炮制所谓“黑画展”,丰子恺自然也不能幸免。《满山红叶女郎樵》这幅画原是画中国近代文学家苏曼殊的诗句,但画中有三片红叶落下,这不成了影射三面红旗落地吗?
做子女的为了关心父亲的安全,一次次地劝他以后留意些。丰子恺却还是我行我素。他给儿子新枚的信中写道:“……我的画都是毒草……然而世间有一种人视毒草为香花,世袭珍藏。对此种人,我还是乐意画给他们珍藏。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画亦如此。”
1974年夏天,丰子恺右手手指开始麻木,次年8月右手臂也逐渐不能动弹,这对辛勤笔耕了半个世纪以上的丰子恺来说,简直是极大的灾难。9月15日,一代艺术家丰子恺安详地阖上双眼,享年77岁。他没见到“四人帮”垮台,就在噩梦中与世长辞了。
不,他没有在梦中逝去。他醒了!1976年10月的鞭炮声把他唤醒了!这位艺术家一生的辛勤播种重新受到滋润和灌溉,在中国各地甚至海外发芽开花。作品就是他的生命,就是他的一切!他与读者同在。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正如他的老友叶圣陶在悼诗中所说:“潇洒风神永忆渠!”
Number:1599
Title:日本留学热中的冷静观
作者:柴生林
出处《读者》:总第90期
Provenance:青年一代
Date:1988。5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语言学校还是“商业学校”
这就是下飞机曾让我眩目过一阵的东京,这就是梦寐以求的留学生活的开始。我们坐在一辆学校巴士上,这辆只可坐8个人的巴士,塞满了15个中国留学生,去分校上课。学校为了招徕学生,办公室设在火车站附近,而教室则设在租金便宜而交通极不便利的地方,和我一起第一天来上课的被挤在两个大汉中间夹缝里的上海姑娘哭了,又不敢放声,只是捂着脸抽泣。嚷嚷着发牢骚的人一下子鸦雀无声了,令人窒息的死一般的沉默,死一般的寂静,死一般的思索。我知道每个人心里都想哭,因为我们经受了多少,放弃了多少,才挤上这辆车的。
有了乘车的体验,看到只有黑板和桌椅的简陋教室已不惊奇了,什么现代化视听设备啦,空调啦等等,“浪漫的奢望”早就烟消云散了。
学校办公室通知下周起巴士停开。同学哗然。我们几位新同学到办公室陈情。还没等我们说完,办公室一位负责人操着一口流利的京腔像电影里的念白一样说:“怎么能说学校欺骗你们呢?学校设有分校是正常的,学校没有必定要接送的义务,你们大陆许多学校不是也有分校吗!?”那本可让同胞感到亲切悦耳的国语让她讲得这样尖厉、刺耳,而那双手交叉胸前的盛气凌人的架势,很有电影里面那位“马列主义老太太”的气度。也许是在东京遇上这种气度吧,我们个个目瞪口呆,最后只能不置一词地悻悻而归。“你们大陆”,她是何许人也?一位老同学告诉我们,她是台湾长大已加入日本籍的北京人。从她谈起,使我对东京语言学校的现状有了真实的了解。
在东京仅有几所语言学校是文部省认可的,其余都是法务省承认的语言学校。由于中国人大量涌来,一些公司纷纷开设语言学校,学校一般由公司老板挂名校长,台湾人把持,近来又雇用几名大陆来的中国人。形成以赢利为主的“商业”语言学校。这样只要有钱就可踏上留学之途。
留学与“留钱”
上课一周才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教室里的课桌椅是20张,班级在编人数30名。我不解地问老师,老师随和地解释:每天只会到三分之二吧。果然如此,教室里不曾坐满过,还有三分之一的人“轮休”。三分之二中不迟到早退的寥寥无几。学生都干什么去了?打工。不加掩饰的说,来日学生中95%以上的人是以留学为名,行“留钱”为实的。来日后,高昂的学费、房租、生活费还有债务,又迫使你不得不拼命打工。所以一位读了半年又退到我们班的同学仍然是五十音图发得“五音不全”。在国内时就听人讲“留日学生素质太差”,分析一下班里同学的文化程度、知识结构,这句判词一点也不为过。80%以上的同学实际文化程度小学(“文革”中的高中生)。看这些三十好几,前半辈子没有在教室正正经经坐过几年的同学在课堂上煎熬的可怜相,心里好不苦涩。坐在这样的教室仿佛使我想到20年前“复课闹革命”的情景,求学的热望顿时减退了。
生活的悲与喜
大林总算有了一间自己的房子,还是我的房东老太动了恻隐之心做保人为大林向街坊一位邻居租的。大林来日一月已在3处搭过铺,搬了3次家,为找房子一个月掉了10公斤肉。近来房租日日见涨,大林的“新居”3贴(约4。5m2)租金1。5万日元,外加水电近2万日元。我真替大林担忧,他现在两个地方打工5小时,收入仅6万日元,肯定要入不敷出,马上要夏天了,这房子连个大澡盆也放不下,外出洗澡每月又得多支出1万日元,真够受的。
今天从一上课开始,广州来的阿龙就一直趴在课桌上。邻座的同乡向老师解释,他来日3个月至今没找到工作,虽说凭这几年在广州的积蓄混过来了,可再雄厚的资金在东京也会很快坐吃山空。在东京的中国男儿“有泪轻弹”已司空见惯。课是不能上下去了,大家议论帮他找工作的办法。一位女同学说她工作的饭店缺一名刷锅的,估计问题不大。
小方苦着脸姗姗地走进教室第一句就说:“单丽娟被护送回北京了。”小方的话很轻却很沉。同学们听到这消息并不吃惊,可脸上个个挂出为同病者送殡的神色。
上周六晚上,单丽娟骑自行车忘了打开车灯被警察拦住,要查她的外国人登记证,她正巧没带,又加上语言不通,就被带到派出所。那晚回家同室的小方就见她眼睛失神、发呆。第二天醒来不见她人影,桌上留着一张字条:“警察今天还要来抓我,我先走了江姐。”单那脆弱的神经在长期的过度紧张又加上一阵剧烈的惊吓后变形了,她疯了,一周后被警方找到时,那件穿出去的旗袍的两边已被撕到大腿跟。
要问留学生最苦最难忍受的是什么,就是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所形成的无形无影却24小时陪伴着你的高压。有些来了二、三年的人都无法摆脱这种心理压力,可只要待在日本一天,就得承受一天。
爱国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
元旦是日本的新年,放假3天。一个朋友的朋友邀请我参加他们几位朋友的聚餐。10平方米的房子来了七、八个人,好不热闹。在日本难得有这样的轻松,难得有这样的休息。绍兴黄酒、上海五香茶叶蛋、北京水饺、广州烤鱿鱼纷纷登场,各显神通。一盒马季的相声磁带、一曲费翔的《故乡的云》听得你先笑后哭。渐渐地大家似乎“醉了”,平日里憋着的那口怨气都发泄出来。“东京的马路高低不平像山路,哪有我们上海的马路平坦,要不我也不会骑车摔了一跤。”小殷拍着受伤的腿说。他早已忘了每次跨过苏州河桥时所产生的厌恶。“东京的羊肠小道和日本人的心胸一样狭窄,哪有我们北京的大街宽阔、畅达。”小顾更是不无自豪地申辩着,他决不再对北京的风沙有半点抱怨。话愈说愈多,愈说愈气。“我们老板是个吝啬鬼……”“好了好了,说到底一句话,日本人是中国人的死敌……”一位看上去挺文静的姑娘突然站起身拿起一把切菜刀模仿着电影里的动作唱道:“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大家笑得前仰后合,酒瓶翻了一地,汤洒了一桌,饭喷了一身,“醉了”真的“醉了”,尽管明天又得向“鬼子”俯首贴耳”说一百遍“哈伊”(是),今天能放肆就放肆个够。
我似乎也被弄得似醉非醉,就这么似醉非醉的回家躺倒,似醉非醉的思索:40年前日本人妄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如今那些未被征服者的后代却争先恐后地涌来“心甘情愿”地接受“心理征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民族的悲哀。无怪乎日本方面对中国留学生数目激增持乐观、积极的态度,一则解决苦力活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二则留学生不能定居日本,回国后必然会带着潜移默化后的“日本化”影子。
自信与自尊
小刘是朋友写信介绍到我这里借宿的。现在每天去一个清扫公司扫大楼,每天回家就对我讲一个日本人干活的“笨伯”故事。对于日本人干活中显出来的“笨”劲,留学生几乎是众口一个词。可说的时候往往忽视了一个事实,我们的许多留学生是以自己大学的文化程度,或者以精明强干的能力与日本最少需要文化知识的洗碗、扫大楼、端盘子工人作比较,这种反差是很明显的,结论也就明显了。
无论从哪方面说中国人也许比日本人多一点聪明。可日本人却“笨鸟”先飞,显巧了,这个问题从民族心理上探讨却有许多可深思的地方。我本想把这番话告诉小刘。再一想他一个大学生每天扫大楼,心情可想而知,回家说说只是求得一种满足自尊心的平衡而已,所以作罢。
小刘与我同住,最大的不满便是缺乏现代化气息。是的,比起有些留学生从“露天商场”“免费采购”的彩电、冰箱、地毯甚至于沙发、衣橱一应俱全来,我的居室可以说家徒四壁了。
某晚我们一起到朋友家看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