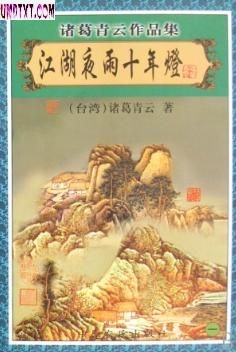读者十年精华-第259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处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
她死了使我可以更多一些时间思索,
更多一些时间工作。
梁漱溟的第二次婚姻与前一次有着显著的不同。
1943年夏季,梁漱溟偶然遇到了比他年轻6岁的桂林教员陈淑芬,梁漱溟深深地爱上了她。他们的爱情成了一件闻名广西全省的事情。桂林的报纸以幽默的口吻大量地报道这段颇具浪漫色彩的恋情。
“究竟谁追求谁?”这个问题成了舆论注意的焦点。记者们为此往来穿梭于陈淑芬和梁漱溟之间。当人们向陈女士祝贺她赢得了梁漱溟的爱情时,她回答说:是他深深地感动了我,“敲开了我心灵的大门”。由此引出了这样的报道:“新双城记?”当时满城都风传梁漱溟正在留胡子,以便能在他的爱人面前显得更像个男子汉。梁漱溟否认了这些谣传,他说:“一个老新郎在婚礼之前总是要刮刮胡子的。”梁漱溟的朋友们也对此事大事渲染,他们打趣说:梁漱溟“为我们这些中年伙伴们赢得了荣耀”。
1944年1月,梁漱溟和陈淑芬在友人家中举行了传统的婚礼。当时在桂林的文艺界和学界名流大都参加了庆祝仪式。李济深将军是宴会的主持人,著名的剧作家田汉还为此写了一首极富幽默感的长诗。
当时的一位名流白鹏飞在宴会上讲了一段很精彩的话:
梁先生原籍桂林,……抗战开始后方归故里。但他在桂林并无家室。既无家室,何言回家。那么最好就是着手建立家庭。敞开的心扉自然容易被人占据。陈女士出阁甚晚,因为她一直要嫁给一位哲学家……于是她就乘虚而入了。
来宾发言结束以后,纷纷要求梁漱溟报告恋爱经过。梁漱溟答应了大家的要求:
现在,我听说谈恋爱要花很多钱,下馆子、看电影、看戏等等。但我却没有花过一分钱。我羞于谈及此事,但的确连出去散步也没有过。我也曾给她写过信,约她在天气好时一起去经山村的河边散步。但那天恰逢阴天小雨。她是否会应约前来呢?我犹豫了一会儿,拿了把伞就出门了。如我所料,在半路上遇见了她。因为还在下雨,我们仍然无法去散步,于是我们终于只是在路边的小亭子里坐了一会儿。
梁漱溟说这样的话,在他的一生中,怕是绝无仅有的了。由此可以想见这次恋情对他的影响。
在婚礼上,梁漱溟还当场唱了一段“黄天霸”。而后对来宾说了声“我去也”,便挽着新娘兴冲冲地走了。梁漱溟的第二次婚姻在相当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十分完满的。
佛还是儒
梁漱溟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但是他的行为却又自始至终表现得超乎寻常的一贯。梁漱溟曾经自称自己是:
1。最讨厌哲学,结果自己也讲了哲学;
2。在学校里根本未读过孔子的书,结果讲了孔家哲学;
3。未读过大学,结果教了大学;
4。生于都市,长于都市,而从事于乡村工作。
尽管梁漱溟一生以承继儒家的道统自任,但当人们把他作为儒学第三期复兴的象征而与熊十力并提时,他却又极认真地将自己与熊十力加以区别:
我与熊先生虽然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以此相交游、共讲习者四十多年,踪迹之密少有其此,然彼此思想实不相同。熊先生应归属儒家,我则佛家也。
在这里,我们无法对他的深层思想背景加以分析,我们只想说,无论梁漱溟如何地倾心于佛家思想,从他一生的行迹看,他最终还是一个“志伊尹之志”的真正的儒者,这从下面两件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1941年圣诞节,日本军队袭入香港。经过九死一生的挣扎,梁漱溟终于逃脱虎口。他乘船逆西江而上进入广西。在安全抵达国统区以后,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
前人云:“为往圣继论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底,万不会有的事。
这一番话,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的人讥评。而梁漱溟却回答他的朋友说:“狂则有之,疯则未也。”
1973年,梁漱溟出席政协的小组会。小组里的同事们不断督促他发言或写文章批判孔子,而这正是梁漱溟坚决拒绝的。连续几天,组员们对他那令人恼火的沉默进行指责,并严令他以某种方式表达。终于,梁漱溟同意公开表态,但他迸出的只有一句话:“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这难道真的如某些学者所认为的,是儒家传统最后一次有意识的公开表现了吗?梁漱溟真的竟是“最后的儒家”?这看来只有等待时间来回答了。
Number : 9677
Title :名人轶事
作者 :赖康宁等
出处《读者》 : 总第 190期
Provenance :大公报
Date :
Nation :
Translator :
婚礼祝词
1942年,作家周而复与王女士在上海结婚,女方是一位护士。周而复请钱钟书先生当证婚人,钱先生欣然答应。他在婚礼上致词:“新郎是从事文学的,文学讲究美,新娘是搞科学的,科学讲究真。真与美的结合,自然就善。”
(方 文摘)
幽默教授
中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教育家钱玄同,30年代起一直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36年,钱玄同在北师大中文系讲传统音韵学,讲到“开口音”与“闭口音”的区别,一同学请他举一个例子,他说——
北京有一位京韵大鼓女艺人,形象俊美,特别是一口洁白而又整齐的牙齿,使人注目。女艺人因一次事故,掉了两颗门牙,应邀赴宴陪酒时,坐在宾客中很不自在,尽量避免开口,万不得已,有人问话才答话。她一概用“闭口音”,避免“开口音”,这样就可以遮丑了,如这样的对话:
“贵姓?”“姓伍。”“多大年纪?”“十五。”“家住哪里?”“保安府。”“干什么工作?”“唱大鼓。”
以上的答话,都是用“闭口音”,可以不露齿。
等到这位女艺人牙齿修配好了,再与人交谈时,她又全部改用“开口音”,于是对答又改成了:“贵姓?”“姓李。”“多大年纪?”“十七。”“家住哪里?”“城西。”“干什么工作?”“唱戏。”
学生听了都大笑。
(赖康宁文,韩小君摘)
肖邦的饭费
1810年3月1日,“钢琴诗人”肖邦诞生在波兰。他年幼时就显露出不凡的才华,在他12岁时,华沙一家报纸曾醒目地以大字刊着:“上帝把莫扎特赐给奥地利人,把肖邦赐给了波兰人。”
19世纪30年代初,肖邦来到了欧洲文化中心巴黎,他的第一场音乐会就征服了这座城市。结果请柬纷至沓来,他成了沙龙的常客。在这些社会的交往中,肖邦总是流露他那种以艺术为尊的艺术家气质。据说在一次宴会后,主人指指钢琴又指指肖邦,意欲让他演奏一曲作为“餐后的节目”来助助兴。肖邦感到他那艺术家之心受了莫大的污辱,大为不快,冷冷地对主人说:“对不起,我吃得很少,”并取出钱往桌上一扔,“给,这是我的饭费。”说完愤然离去。
(殷 月文,段小文摘)
梁启超铭言传弟子
●周续端
当年,著名维新革命家、大学者梁启超重病在身,始而延请西医诊治,效果甚微。
其入室弟子谢国桢看到老师病情日重,遂将自己弟弟的岳父——驰名中华的四大名医之一萧龙友引荐前来给他诊治。
萧龙友登门诊治两次后,遂改为由谢国桢用信详细函告梁的病情,用通信的方式互相联系,然后由萧先生处方对症下药。
服用萧先生开的中药,梁觉神清体爽,颇见功效。但是后来,病情又出现反复,病情反复的主要原因是梁没有停止读书治学的活动。
当谢国桢将梁的实况函告萧龙友后,萧遂复函谢国桢说,梁的病要想治好并不难,但不能光靠药力,俗话说“三分看病七分养”。要想彻底恢复健康,前提是停止劳神费心的工作,读书治学当然是在必禁之列,否则即使是扁鹊再生,华佗降世,也是无能为力的。
萧龙友复函后,满以为学富五车的梁启超能听其劝告,放下书本,配合治疗。没想到,当谢国桢将其意转告梁时,梁不但不采纳大夫的意见,竟回答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仅此一句,当萧龙友从谢国桢处听到后,一时惊得目瞪口呆,连连叹气,深感无可奈何。
时过不久,即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这位信奉应像死在沙场上的战士一样的大学者,在京与世长辞,死在毕生致力的学术研究上。
时隔几十年之后的1982年,谢国桢因胆结石病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
在病床上,他反复发着高烧,有时竟达40度。大小便不能自理,下床走动都十分困难。
然而,只要他病情稍微稳定,便在病房内读书工作起来。
有一天,萧龙友的儿子——北京师范大学的萧璋教授前来探望,见其病床旁桌上放着许多书,遂劝其在治病期间不要读书治学。
谢国桢听后,默然片刻,即正色道:“‘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梁先生这句铭言,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Number : 9678
Title :作为生物的社会
作者 :刘易斯·托玛斯
出处《读者》 : 总第 190期
Provenance :细胞生命的礼赞
Date :
Nation :美国
Translator :李绍明
从适当的高度往下看,大西洋城边青天白日下的海滨木板路上,为举行年会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的医学家们,就像是群居性昆虫的大聚会。同样是那种离子式的振动,碰上一些个急匆匆来回乱窜的个体,这才略停一停,碰碰触角,交换一点点信息。每隔一段时间,那群体都要像抛出钓鳟鱼的钓线一样,准确无误地向恰尔德饭店抛出一个长长的单列纵队。假如木板不是牢牢钉住,那么,看到他们一块儿筑起各式各样的巢穴,就不用感到吃惊了。
用这种话来描绘人类是可以的。在他们最强制性的社会行为中,人类的确很像远远看去的蚁群。不过,如果把话反过来讲,暗示说昆虫群居的活动跟人类事务总有点联系,那在生物学界将是相当糟糕的态度。关于昆虫行为的书籍作者,通常要在序言里苦口婆心提醒人们,昆虫像是来自外星的生物,它们的行为绝对是有异于人的,完全是非人性、非世俗,几乎还是非生物的。它们倒更像一些制作精巧,却魔魔道道的小机器。假如我们想从它们的活动中看出什么显示人类特点的东西,那就是在违反科学。
不过,让一个旁观者不这样看是很难的。蚂蚁的确太像人了,这真够让人为难。它们培植真菌,喂养蚜虫做家畜,把军队投入战争,动用化学喷剂来惊扰和迷惑敌人,捕捉奴隶。织巢蚁属使用童工,抱着幼体像梭子一样往返窜动,纺出线来把树叶缝合在一起,供它们的真菌园使用。它们不停地交换信息。它们什么都干,就差看电视了。
最让我们不安的是,蚂蚁,还有蜜蜂、白蚁和群居性黄蜂,它们似乎都过着两种生活。它们既是一些个体,做着今天的事而看不出是不是还想着明天,同时又是蚁、蚁穴、蜂窠这些扭动着、思考着的庞大动物体中细胞样的成分。我认为,正是由于这一层,我们才最巴不得它们是异己的东西。我们不愿看到,可能有一些集体性的社会,能够像一个个生物一样进行活动。即使有这样的东西,它们也决不可能跟我们相关。
不管怎么说,这些东西还是存在。野地里一只独行的蚂蚁,不能设想它头脑里想着很多。当然,就那么几个神经元,让几根纤维串在一块儿,想来连有什么头脑也谈不上,更不会有什么思想了。它不过是一段长着腿的神经节而已。4只或10只蚂蚁凑到一起,围绕着路上的一只死蛾,看起来就有点意思了。它们这儿触触,那儿推推,慢慢地把这块食物向蚁丘移去。但这似乎还是瞎猫撞着死老鼠的事。只有当你观看聚在蚁丘边的、黑压压盖住地皮的数千蚂蚁的密集群体时,你才看见那整个活物。这时,你看到它思考、筹划、谋算。这是智慧,是某种活的计算机,那些爬来爬去的小东西就是它的心智。
建造蚁丘的时候,有时需要一批一定规格的细枝,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