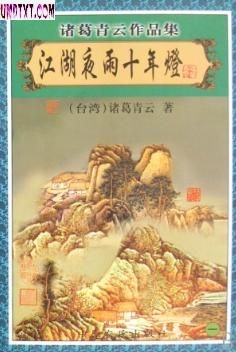读者十年精华-第244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魏明伦:1941年生,川剧编导
自述:我比拿破仑个子矮,与鲁迅、曹禺相当,反复衡量,没有力气玩枪,有条件摸笔,于是便操了文学。
吴祖光:巴山一鬼,
威慑诸神。
晏婴转世,
是魏明伦。
蒋子龙:1941年生,作家
自述:你看,我这张脸是不是有点冷涩、难读、不潇洒、不畅销?
陈国凯:蒋子龙把中国产业工人的豪气雄风带上文坛。他毕竟是性格过于耿直的文人,没有多少机关城府,不懂阴柔之术。
李玉皓:琢磨世人,咀嚼自己,苦痛地体味和揭示着欺诈、蛮横、琐屑、虚伪,被他名之为“饥饿综合症”的人生的悲喜剧。
胡殷红:只要能冲破他那道“严肃”的防线,便可发现,他那张脸挺幽默,挺可亲,也挺男子汉。
Number : 9296
Title :假如我有九条命
作者 :余光中
出处《读者》 : 总第 179期
Provenance :台港文学选刊
Date :1996。3
Nation :中国台湾
Translator :
假如我有九条命,就好了。
一条命,就可以专门应付现实的生活。苦命的丹麦王子说过:既有肉身,就注定要承受与生俱来的千般惊扰。现代人最烦的一件事,莫过于办手续;办手续最烦的一面莫过于填表格。表格愈大愈好填,但要整理和收存,却愈小愈方便。表格是机关发的,当然力求其小,于是申请人得在四根牙签就塞满了的细长格子里,填下自己的地址。许多人的地址都是节外生枝,街外有巷,巷中有弄,门牌还有几号之几,不知怎么填得进去。这时填表人真希望自己是神,能把须弥纳入芥子。或者只要在格中填上两个字:“天堂”。一张表填完,又来一张,上面还有密密麻麻的各条说明,必须皱眉细阅。至少照片、印章,以及各种证件的号码,更是缺一不可。于是半条命已去了,剩下的半条勉强可以用来回信和开会,假如你找得到相关的来信,受得了邻座的烟熏。
一条命,有心留在台北的老宅,陪伴父亲和岳母。父亲年逾90,右眼失明,左眼不清。他原是最外倾好动的人,喜欢与乡亲契阔谈宴,现在却坐困在半昧不明的寂寞的世界里,出不得门,只得追忆冥隔了27年的亡妻,怀念分散在外地的子媳和孙女。岳母也已过了80,5年前断腿至今,步履不再稳便,却能勉力以蹒跚之身,照顾旁边的朦胧之人。她原是我的姨母,家母亡故以来,她便迁来同住,主持失去了主妇之家的琐务,对我的殷殷照拂,情如半母,使我常常感念天无绝人之路,我失去了母亲,神却再补我一个。
一条命,用来做丈夫和爸爸。世界上大概很少全职的丈夫,男人忙于外务,做这件事不过是兼差。女人做妻子,往往却是专职。女人填表,可以自称“主妇”,却从未见过男人自称“主夫”。一个人有好太太,必定是天意,这样的神恩应该细加体会,切勿视为当然。我觉得自己做丈夫比做爸爸要称职一点,原因正是有个好太太。做母亲的既然那么能干而又负责,做父亲的也就乐得“垂拱而治”了。所以我家实行的是总理制,我只是合照上那位俨然的元首。4个女儿天各一方,负责通信、打电话的是母亲,做父亲的总是在忙别的事情,只是心底默默地怀念着她们。
一条命,用来做朋友。中国的“旧男人”做丈夫虽然只是兼职,但做起朋友来却是专任。妻子如果成全丈夫,让他仗义疏财,去做一个漂亮的朋友,“江湖人称小孟尝”,便能赢得贤名。这种有友无妻的作风,“新男人”当然不取。不过新男人也不能遗世独立,不交朋友。要表现得“够朋友”,就得有闲、有钱,才能近悦远来。穷忙的人怎敢放手去交游 ?我不算太穷,却穷于时间,在“够朋友”上面只敢维持低姿态,大半仅是应战。跟身边的朋友打完消耗战,再无余力和远方的朋友隔海越洲,维持庞大的通讯网了。形成近交而不远攻的局面,虽云目光如豆,却也由于鞭长莫及。
一条命,用来读书。世界上的书太多了,古人的书尚未读通三卷两帙,今人的书又汹涌而来,将人淹没。谁要是能把朋友题赠的大著通通读完,在斯文圈里就称得上是圣人了。有人读书,是纵情任性地乱读,只读自己喜欢的书,也能成为名士。有人呢,是苦心孤诣地精读,只读名门正派的书,立志成为通儒。我呢,论狂不敢做名士,论修养不够做通儒,有点不上不下。要是我不写作,就可以规规矩矩地治学;或者不教书,就可以痛痛快快地读书。假如有一条命专供读书,当然就无所谓了。
书要教得好,也要全力以赴,不能随便。老师考学生,毕竟范围有限,题目有形。学生考老师,往往无限又无形。上课之前要备课,下课之后要阅卷,这一切都发挥“人师”之功,在“教”外施“化”。常言“名师出高徒”,未必尽然。老师太有名了,便忙于外务,席不暇暖,怎能即之也温?倒是有一些老师“博学而无所成名”,能经常与学生接触,产生实效。
另一条命应该完全用来写作。台湾作家极少是专业的,大半另有正职。我的正职是教书,幸而所教与所写颇有相通之处,不致于互相排斥。以前在台湾,我日间教英文,夜间写中文,颇能并行不悖。后来在香港,我日间教30年代文学,夜间写 80年代文学,也可以各行其是。不过艺术是需要全神投入的工作,没有一位兼职然而认真的艺术家不把艺术放在主位。鲁本斯任荷兰驻西班牙大使,每天下午在御花园里作画。一位侍臣从园中走过,说道:“哟!外交家有时也画几张画消遣呢。”鲁本斯答道:“错了。艺术家有时为了消遣,也办点外交。”陆游诗云:“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向令天开太守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陆游认为杜甫之才应立功,而不应仅仅立言,看法和鲁本斯正好相反。我赞成鲁本斯的看法,认为立言已足自豪。鲁本斯所以传后,是由于他的艺术,不是他的外交。
一条命,专门用来旅行。我认为没有人不喜欢到处去看看:多看他人,多阅他乡,不但可以认识世界,亦可以认识自己。有人旅行是乘豪华邮轮,谢灵运再世大概也会如此。有人背负行囊,翻山越岭。有人骑自行车环游天下。这些都令我羡慕。我所优为的,却是驾车长征,去看天涯海角。我的太太比我更爱旅行,所以夫妻俩正好互作旅伴,这一点只怕徐霞客也要艳羡。不过徐霞客是大旅行家,大探险家,我们,只是浅游而已。
最后还剩一条命,用来从从容容地过日子,看花开花谢,人往人来,并不特别要追求什么,也不被“截止日期”所追迫。
Number : 9297
Title :给一位小朋友的信
作者 :哈里·贝迪
出处《读者》 : 总第 179期
Provenance :
Date :
Nation :
Translator :朱晓慧译
在我熟悉的人中,有一位特别的朋友:年幼、皎美、聪慧。她名叫卡罗琳,7岁,家住香港,正在一所主要为移民孩子开设的学校里读书。她母亲虽出生在澳大利亚,后来却一直住在香港。她的父亲是瑞士人,在香港拥有一家小小的贸易公司。不久前,我到她家做客。她拿起一本《亚洲周刊》,认出了我在上面的一张照片,于是问我究竟写些什么。我告诉她我主要是写人。“哦,为什么不找点时间写写我呢?!”她问道,带着常有的那种急迫的样子。我告诉她,等她长大成名,会有不少人写她的。“好的。那么现在就以悉尼的哈里伯伯的名义给我写信吧。”对她的要求,我作了承诺。这不就是:
亲爱的卡罗琳:
真高兴给你写信。我有好多好多事要告诉你,可你总是忙。你要读书,上钢琴课、芭蕾课,还有作业呀,参加生日舞会什么的。每周,你要给苏黎世的奶奶和悉尼的伯伯写信,真像香港的大老板那样忙碌!我真同情你,既没养小狗,也没地方骑小车。我想,你妈妈安排了那么多的事要你做,正是要你不闲着吧!虽然你不太喜欢学芭蕾,妈妈却希望这能帮助你成为一个标准的好姑娘。你不知道吗,大多数父母,都期待着自己童年的梦想在他们的孩子们身上实现。当你妈妈年轻时,那时姑娘们的风尚就是习歌学舞。可是,如果你想学些其他知识,别以为你不行或你不需,更不要相信那些学问是专门留给男孩子的!今天的女性中有宇航员、工程师、医生,也有飞行员和政治家。别把自己的选择限在过去那种姑娘的圈子里。
记得有一天我与你爸爸带你去看网球赛吗?你和你的朋友们聚在校门口等,旁边却孤零零地站着一位小姑娘。我想她一定来自斯里兰卡,是少数几个来自其他亚洲国家同学中的一位。干嘛不与她聊聊呢,多了解些她那个美丽国家的事情。我敢肯定你还有华人同学。你知道,香港是他们的家。当你的那些朋友离开以后,他们还留在这儿。别忘了香港也是你的家——不是苏黎世也不是悉尼。即使你今后走了,你也会常常怀念这个地方。试想,有一天你打算去香港观光,干嘛现在不多交些朋友呢?!
我知道你没有机会去交很多当地的朋友。你所留连忘返的俱乐部中没几个亚洲的小朋友。更叫我伤感的是,在你们的教科书中,我看不到有什么地方给你们讲述过中国和亚洲其他一些国家的情况。今天的澳大利亚学生比你的同学们知道的亚洲的事情要多得多!当你长大的时候,澳大利亚说不定会把自己看成是亚洲的一员。也许,你会因为把你叫成亚洲人而得意呢!到那时,你们都是众多国家的儿女,每一个人都会理解我们共同分享的世界,你也会因为乐于帮助每一个人而显得重要。
我永远忘不了一个傍晚的情形。你碰见一个人提着一篮子刚出窝的猫仔。那人说,如果没人买,就只能 将这些小猫儿溺死。你哭得好伤心哟,就因为不准你带一只回家。可令人悲伤的是,世界上比这惨的事多着呢。人太多,空间却太少;太多的恐惧和贪婪,太少的爱意与怜悯。我们装着对别人的困难视而不见;一旦影响到自己还怒发冲冠!记得那天你游泳,一跳进脏海就冲回了岸边。再想想那些可怜的鱼儿,却不得不在水里忍受长年。我们呼吸的空气也变得越来越臭!当然,你今后成为舞蹈家或钢琴家,我们会引为自豪。但别忘了,要做的事还远不止这些。我希望你长大后不仅是一位贤德的淑女,同时是一位深知这个广博世界而又献身为她造福的女士。那样的话,卡罗琳,成千上万的人都会追着写你。
哈里伯伯
Number : 9298
Title :我所看到的美国小学教育
作者 :高钢
出处《读者》 : 总第 179期
Provenance :三月风
Date :1995。12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当我把9岁的儿子带到美国,送他进那所离公寓不远的美国小学的时候,我就像是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交给了一个我并不信任的人去保管,终日忧心忡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学校啊!学生可以在课堂上放声大笑,每天最少让学生玩两个小时,下午不到3点就放学回家,最让我开眼的是根本没有教科书。那个金发碧眼的女老师看了我儿子带去的中国小学4年级的课本后,温文尔雅地说:“我可以告诉你,6年级以前,他的数学不用学了!”面对她充满善意的笑脸,我就像挨了一闷棍。一时间,真怀疑把儿子带到美国来是不是干了一生中最蠢的一件事。
日子一天天过去,看着儿子每天背着空空的书包兴高采烈地去上学,我的心就止不住一片哀伤。在中国,他从1年级开始,书包就满满的、沉沉的,从1年级到4年级,他换了3个书包,一个比一个大,让人感到“知识”的重量在增加。而在美国,他没了负担,这能叫上学吗?一个学期过去了,把儿子叫到面前,问他美国学校给他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他笑着送给我一句美国英语:“自由!”这两个字像砖头一样拍在我的脑门上。
此时,真是一片深情怀念中国的教育。似乎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为什么中国孩子老是能在国际上拿奥林匹克学习竞赛的金牌。
不过,事到如此也只能听天由命。
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儿子的英语长进不少,放学之后也不直接回家了,而是常去图书馆,不时就背回一大书包的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