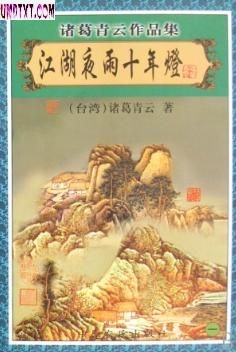读者十年精华-第213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Number : 8184
Title :不怕整容
作者 :
出处《读者》 : 总第 161期
Provenance :北京科技报
Date :1994。8。17
Nation :
Translator :
法国新时代女艺术家奥伦把自己的身体“彻底奉献给艺术”她先后接受过15次整容手术,将自己变成“活生生的大师级作品”。
43岁的奥伦,将自己当作活的雕塑,以皮肉当粘土,使自己的脸庞糅合了古典名画美女的种种美态。在手术刀下,据说她得到了蒙娜丽莎的前额,赫拉德笔下普西沏的“一双秋水”,包提柴里所绘维纳斯女神的鼻子,以及一位佚名法国画家笔下女猎神戴安娜的下巴。
她在接受手术时也与众不同,充满所谓艺术气氛。医生穿的不再是白袍,而是名师设计的黑袍,手术室内挂了不少画,又摆着经过消毒的塑胶水果;局部麻醉的她,一边接受手术,一边高声诵读法国哲学家的作品。
据一位为她整容的医生说,从奥伦的脸部及其身体部分割下来的皮肉,迄今总共有54公斤左右。
Number : 8185
Title :丑人俱乐部
作者 :沈洪
出处《读者》 : 总第 161期
Provenance :中国青年报
Date :1994。6。19
Nation :
Translator :
~15@ 在意大利皮奥比考,有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丑人俱乐部。凡是丑陋的人,无论其国籍、性别和年龄,都可申请加入该俱乐部。
1879年,皮奥比考市政府发现,该市尚有128名大龄姑娘未嫁,原因是长相不佳。为给她们找到伴侣,市政府决定发起“丑人节”。
每年9月,世界各地的丑人就云集皮奥比考。节日的高潮是选举“金色伏尔甘”。伏尔甘是意大利传说中的英雄,因长相丑陋而被逐出家门。后来,伏尔甘成为武士,拯救了意大利这个国家。“金色伏尔甘”候选人的条件不是长得丑,而是要对丑人事业做出贡献。当选者将身穿伏尔甘服,被人们当英雄看待。“丑人俱乐部”的这些活动,使凡是加入俱乐部的丑人,自尊心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恢复。
Number : 8186
Title :白天鹅的记忆
作者 :从维熙
出处《读者》 : 总第 161期
Provenance :
Date :
Nation :
Translator :
来到南方,是不是因为这座城市,有个白天鹅宾馆的缘故?头一夜,我就梦见了我曾见过4只白天鹅。
1964年,我在一个劳改农场改造,第一次见到那天性驯良、美如天使的水禽动物,是在劳改队大队部的葡萄架下。我隔着铁丝网,神往地望着白天鹅那一身洁白的羽翼,心里不禁自问:蓝天才是它们的故乡,江河湖泊才是它们诗的天堂,它们到这儿来干什么?还摆出一副悠然自得、闲庭信步的架势!
飞吧!我的天使!这儿是囚笼,不该是你漫步的地方;露珠闪光,水草萋迷的青青河畔,那儿有你的群落,有你的家族,为什么你要眷恋这个鬼地方呢?
后来,我知道了:原来这两只天鹅是被主人剪去了一圈欲飞的翅膀。它们来自天茫茫野茫茫的东北大草甸子兴凯湖,那儿的劳改农场捕获了它们,场长从兴凯湖调往我们所在的劳改农场时,把这“姊妹俩”也装进囚笼,像携带仆从眷属那般,把它们迁移到这个地盘上来了。
使我忧虑的是,随着生存环境的改变,他们天性中的善良,被岁月的流光啮食掉了,使这天使般的两姊妹,只剩下天鹅的形态与仪表。有一次,我到劳改队办公室去请示什么事情,当我穿过葡萄架时,那“两姊妹”竟然拍打着仅存的短短的翅膀,对我发动了突然袭击。
一只对我嘎嘎狂叫,神态犹如家狗般凶厉。
一只用嘴叼住我褴褛的衣袖,撕扯下我袖口的一缕布条。
我挣扎着,我奔跑着,待我逃出葡萄架,惊魂初定之后,留给我的是满腹的狐疑:
“这还是天鹅吗?”
“这是两条腿的狗?”
“这不是黑狗、灰狗、黄狗。”
“这是被异化了长着翅膀的白狗。”
50年代中期,当我还是个青年作家的时候,我去过东北三江草原。那儿块块沼泽,如同大翡翠中镶嵌着的一块块宝石;它们在那野花盛开的水泊旁,交颈而亲,合翼而眠。那姿态像是无数下凡的安琪儿入梦。在这美丽的群落中,总有一个“哨兵”站岗,它们警惕人类,它们警惕枪口,它们警惕秃鹰,它们警惕野兽。他们从不惊拢邻居,他们以不吞噬同类,它们从不以鸟类王国皇后自居,它们从不趾高气扬,自喻为“羊群中的骆驼”。
据萝北草原的一个猎人告诉我,他从不捕杀白天鹅。他说此种鸟类不仅羽毛如雪,还有代其他鸟类孵化雏鸟的本能。有的“娘”把娃儿生下来后,一扑楞翅膀飞了。白天鹅则扮演“娘”的角色,把其他鸟类家族的后代孵化出来。群居草原和与囚徒为伍的白天鹅,反差如此之大,简直令人吃惊!
仔细想想,似乎从中发现了一点道理。地壳喷出炽热的岩浆可以造山,磨盘眼里流出的粮食可以碾成面粉;美丽的天使安琪儿,在主人驯化豢养以及囚徒们的挑逗凌辱之下,就不能改变它那颗善良的灵魂吗?它最初是出于生存本能的反抗,久而久之就把人类视若顽敌,见了脖子上驮着脑袋的人,就首先对其进行袭击
!大约过了年把光景,一群白天鹅在春日北返,它们在天空中发现了两个同族,在天空徘徊良久之后,终于有两只飞落下来,大概是想来叙叙手足之情,但他们刚刚落地,两只在囚笼旁生动的天鹅,则像凶神一般,与看望它们来的两只天鹅,摆出武斗架式。飞下来的天鹅鸣叫着说着天鹅家族才懂的语言,但这两只“地鹅”,则已完全丧失了天鹅家族的一切属性,将飞来的兄弟姐妹,叼下来一团团白色的绒毛。飞来的两只白天鹅历经惊愕之后,终于起飞了。但这时猎枪响了,这对来探望家族兄弟的美丽天使,双双从天空中坠落下来!
枪声惊醒了我的梦,于是我想起了文学的使命。
善与恶。
生与死。
Number : 8187
Title :红粉知己
作者 :王惠
出处《读者》 : 总第 161期
Provenance :青年月报
Date :
Nation :
Translator :
有一种女性,你和她认识的过程一点不特别。假使是坐下来谈完了该谈的事,没有多聊,便起身告辞,她走了之后,你好像不会若有所失,不会忽发奇想,一切还是原样。随着时间的流淌,你和她仍是那样偶尔接触一下就分开。没有痕迹的,很自然很恬静的一种交往。
自然你不会只认识她一个女性,你的同学、亲戚朋友、单位同事中都有女性,她们当中,或许有一个是你的女朋友,或许有一个成了你宝贝的妻,或许有一个能与你坐下深谈,或许这些你都还没有,你还是寻找的年龄,但自从你毫不经意地认识她之后,虽然没有妨碍什么,可后来你会在某一天,要么很多人,要么独处的时候,便突然想起她,想她时,没有异常的激动,你想约她风面,约她谈谈。这样的谈话,你不一定非要面对面地谈。你拨通电话,你对她的客套似乎比对别的女孩要少得多,而且你也没有跟她开大家都熟悉的那一种玩笑,你在电话里,和她淡淡地聊几句,一点无意烘托什么,渲染什么,聊完,你心里坦荡,有踏实感。
她呢,有时候会找你,这一般是有点事情商量,或是提点看法。你们的谈话声从来高不起来,也不是在异性面前故意深沉和腼腆,就很有点像瑞雪落在水面,本身就是一种天然。
你们的接触似乎没有高潮,倒是比常人的接触还要少一点,但双方心里都有这样一个人,并不在什么非常秘密的位置,亦不是任意一个地方搁置的,确切的地方,大概你也不知道,只晓得,是忽明忽暗,若隐若现,飘飘忽忽的一个存在。有可能好长一段时间,把她忘得干干净净,可是会在一个时辰里,比方说出差,正走在街上,挤在公共汽车里,躺在宾馆中,你莫名其妙把她从记忆的那一个角落打捞起来,却是很鲜明的。你吃惊,如何在他乡异地不想起自己非常亲近和熟悉的朋友!
到了年末岁尾,五彩缤纷的贺年卡小摊前挤满了人,大家都在祝福,你也凑过去买了,可轮到要寄给她时,你停下,你判定这样浩浩荡荡寄贺卡,虽是风俗,亦是时尚,可你不想对她这样做,你把本该寄出去的那一张扣下。你知道她这一年会收到许许多多精致漂亮的贺卡,但少你的一张,并不少了你的祝福,倘若你也寄了,那么,众多的像雪片一样的贺卡会把你的祝福湮没。把祝福留给自己,有空没空就祝福她,现在留下一片空白,比什么都好。
但是有时间和没时间的时候,你还是有见到她的渴望,而且见她之前,一定是你对自己满意、感到最充实的时候。至于穿得时髦一点,大可不必,干净就行。每一次的谈话,幻想成分少,真实成分多。话题时宽时窄,时具体时空泛,但不议论同志,不发牢骚。她坐在那里,表情自然,富有神韵。
很久之后,你不甘心违背你的意志,你曾经想对她说出自己的心思,但看着她端端庄庄的脸庞,洁净方正的气质,你不忍心了。你觉得为了一点私利,而刺破这样仿佛白雾缭绕的清纯境界,实在是一种罪过。所以,你尊重了自己并尊重了对方,也就尊重了你们的交往。你口里呷着绿茶,泪眼汪汪,她问你是不是哭了,你说不是哭,你说你的眼睛到了秋天,风一吹,就自然流泪。
至今,你们依然保持着来往。来也淡淡,去也淡淡,而你一旦和她对坐,犹如面对湖山胜地,林泉溪涧,男人的俗念会减得少一些,再少一些。
这种女性,比不上戴金银首饰、装扮得姹紫嫣红的女性,但文化素质以及女人素质都要是一流的。她并不独身,照样做妻子,你和她认识,便是一种福分
Number : 8188
Title :小狗鲍比
作者 :马中行
出处《读者》 : 总第 161期
Provenance :女性天地
Date :
Nation :
Translator :
纽约,很阔气,很豪华……你可以用各种发烧的词来形容它,都不会过分。
可是,我这个到纽约做客的人,却飘零,孤独。
小弟说,美国比中国先进了一个世纪,你来过过下个世纪的生活。来了个霸王请客,不由分说,把机票寄来了。
我到纽约才发现,小弟住着一个套房,可他为了省钱,把里屋转租给一个阿拉伯人。
无可奈何,他为我找了一个中国女医生家,与她和她的12岁的小儿子阳阳做房客。
我刚走到她门口,开门扑上来的,是一只小不点儿的、全身长着长长的白毛的、小球球似的狗。我生平最怕小动物,见了毛烘烘的猫、狗,我全身的毛孔都会乍起来了,感到皮肤发刺,心发紧。这回找了个养狗的户,还和人家合住。
我大概吓得够呛,女医生连忙“鲍比!”“鲍比!”叫着,把它轰开了。
小弟为了多挣钱要上两个班,只有星期六、星期天带我出去猛玩。平常我就关在家里,女医生出门时总要关照我,有人按铃,你就拿起话筒问他是谁,屏幕上会现出来人的形象,认得了,你再按开门的钮;还要我一定得把通凉台的玻璃门锁上。特别要警惕黑人。
纽约就有这么吓人。
小弟了解除我的寂寞,给我租了好多录相带。
每回,我要看录相,就和鲍比展开了沙发争夺战。它人模狗样,白天总是躺在正对电视机的沙发上睡觉。
我看着它那侧卧着安然入睡的小样儿发愁,用录相带顶着它的脊背叫它挪挪窝。可它只要见我坐在沙发上,就要把它毛烘烘的身体偎向我,睁着一双蓝蓝的洋眼睛。
它那小样儿挺招人怜爱,但我怕那一身的毛。当我轰它走开时,我看到它像小孩受到挫伤,不胜落寞地逃向床底下阴暗的地方。
它大概像我一样,也感到寂寞吧。
一次,我陪女医生出去遛狗,碰上住在隔壁的矮墩墩的日本女人,她操着生硬的英语说,白天我们不在家里,她常常听到鲍比哭。
它也会哭?而且失声地哭?
当它再偎向我时,我试着去抚摸一下它,它马上就来舔我的手,还用它那尖锐的小狗牙,轻轻地咬往我的指头玩,舔我的脸,钻到我的腋下,爬到我的肩上,没完没了。
两个天涯沦落的灵魂,一个人,一个狗。
我们吃饭的时候,也是它最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