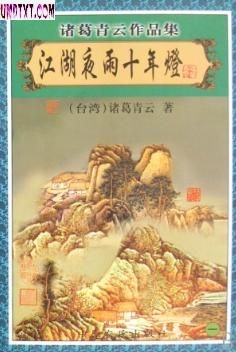读者十年精华-第195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于在罗浮宫入口处加装一个玻璃金字塔式的顶。1988年我去巴黎的时候,巴黎人骂声不绝,有人说:这就像在身穿锦绣袍服的古代王公头上戴了一顶小丑才能戴的透明尖顶帽。有人说:这个贝聿铭,人们把他夸坏了!有人说:这个中国人,他以为扔给我们一顶农夫的破草帽我们也得戴。这次访问巴黎,还是那些人,说法又改变了。有人说:贝聿铭敢于有这种设想,就说明他真是个天才!有人说:很协调!好像是原有的一样。有人说:罗浮宫更醒目了。其实,这是一个我们司空见惯而又从未细想过的审美观念问题。
后来,当我沿着塞纳河散步的时候,有时会觉得有些毗连着的不同时代的房屋很别扭,十七世纪的古拙和十九世纪的精细反差很大,而且每一座桥都风格各异。巴黎圣母院和蓬皮杜文化中心大厦,凯旋门和新落成的拉底第斯大方门遥遥相对,想想觉得很荒谬,看看,觉得还过得去。假设拿破仑突然醒过来,一定会为巴黎的变化大发雷霆。其实他也改变过巴黎,包括罗浮宫。今天的巴黎人到香港和上海旅游,看见一些人手持大哥大在街上大声喊话非常反感,幸运的是他们不是拿破仑,才没有发生战争的危险。但我想,下一代巴黎人会比上一代巴黎人更宽容些……宽容之后也就渐渐习惯了。
????
Number : 7521
Title :情系“蓝草莓”
作者 :玛丽莲·凰里巴斯
出处《读者》 : 总第 144期
Provenance :语文报·七彩月末
Date :1993。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秋水
我和格伦于1961年结婚,1962年丈夫投效空军,我们的两个儿子于1963年和1964年相继出生。1965年,一辆天蓝色的顺风牌双门汽车从底特律一家汽车公司出厂。
1968年,我们在住所附近的旧车场里遇到了它,但它并非格伦所渴望的艳红色敞篷车。车的旧主人含情脉脉地望着这辆车:“你们决不会后悔买它的。”同时递给我们一瓶蓝色的修饰用油漆。
我们给这辆车取名为“蓝草莓”。我做了两个厚厚的垫子给五岁的丹尼和四岁的尼克坐,好让他们能看到车外的景物。
由于格伦调任新职,我们曾先后到过科罗拉多、纽约、亚拉巴马和弗吉尼亚等州,“蓝草莓”一直忠心追随着我们。修饰用的油漆已经用完了,两个儿子的垫子也减去了一半厚度。
后来,我们买了一辆几乎全新的新星型汽车,于是“蓝草莓”一下成了“旧”车。冬天,新星车停在车房里,“蓝草莓”则在路边“打冷战”,身上长出了锈斑。我们替它修补,又花了99。95美元把它重新油漆当然是蓝色,但和原来的蓝色不完全一样。当它的里程表跳到99996。5时,我们全家上车,在街上兜圈子,直到它跳回00000。0。
格伦又被调到加里福尼亚的萨克拉门托。合理的安排当然是把“蓝草莓”卖掉,但运去十几年来它已成为我们家庭的一员,于是我们驾驶两辆汽车横越大陆。在加里福尼亚,“蓝草莓”老态渐露,油漆像晒焦了的皮肤似的剥落,然而,丹尼和尼克领了驾驶执照后还常常驾驶它。
两个儿子先后毕业,搬了出去。格伦也从空军退役进了本地一家公司做事。公司供给他一辆普通的通用汽车公司出产的短尾车。结婚25周年时,他送了我一辆新车没有什么特色的通用公司短尾车。它有空调、桶形座椅和立体声音响系统,但它只能算交通工具,不是我们家庭的一分子,连名字也没有。
“蓝草莓”孤独地停在街边,里程表早在三年前就不再转动了,当时车子已经跑了237391。7公里。车的两侧已经漆上了第三种蓝色的油漆。格伦在报上登了个卖车小广告,要价500美元,我猜格伦并不是真的要卖,因为这价格实在太高了。
但还是有一个人对这辆车感兴趣,他开车跑了很远的路来看“蓝草莓”。他拿出500美元,格伦无可奈何地交出了钥匙。
格伦万分沮丧。我抓住他的手说:“它不过是辆汽车而已。”我虽这么说,但它并非只是辆汽车,并非只是钢、布和一小块补在挡泥板上的纤维玻璃。它是我们儿子小时在后座上坐的厚垫子,是我们穿越众多州县的难忘经历的一部分。它陪伴了我们将近20年。曾有数千个早晨,我挥手目送格伦开着它去 上班。现在,它最后一次从我们家驶出去了。
我不禁泪如泉涌。
????
Number : 7522
Title :丁聪访谈录
作者 :权海帆 杨乐生
出处《读者》 : 总第 144期
Provenance :喜剧世界
Date :1993。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不知道“小丁”的。中国的普通人只要认识几个字,能看书报的,没有没看过“小丁”的漫画的。
“小丁”就是大名鼎鼎的漫画艺术家丁聪先生。
由于已很少从传媒中得知他的消息,我们带着种种复杂的情绪和种种疑惑在北京西三环路侧叩响了丁聪先生的门丁聪先生70岁以后乔迁的新居。
76岁的老人了还称“小丁”
人们常常关心“小丁”这个名称,我们自然也不例外。丁聪讲,说起这个笔名,要上溯到他父亲。他父亲丁悚先生,字幕琴,曾在刘海栗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担任第一任教务长。他有一批当时漫画界和其他艺术界的朋友,如张光宇、叶浅予等,彼此来往频繁,丁聪自然幼小时候便和他们熟识了。丁聪发表的第一个作品是一幅儿童画,当时大约六七岁(这自然是编辑估计的),署名是“画家丁幕琴先生之公子”,旁边还有“公子”的图照。后来他开始画漫画,签名曾用过真名“丁聪”,因繁写的“聪”字笔画太多,写小了印刷出来看不清楚;写得太大,又破坏了整幅作品的艺术效果,张光宇就建议他署名“小丁”,一举数得,一用就是快70年。丁聪严肃地说:中文的“丁”字有“人”的意思,“小丁”即“小人物”。自谦之外,倒确实和他这一辈子的经历相吻合,尽管成名较早,创作也搞了60多年,但始终是个“小人物”。
说完了,丁聪又幽默地补充一句“我连个头也是矮小的,笔名‘小丁’更就自然而然了”。
生命和漫画连在一起
丁聪从小接触漫画,接触漫画家,因而不只是爱上了漫画,也开始画上了。张光宇对丁聪早期创作影响最大。丁聪上中学后,便不停地画漫画,向报刊投稿,发表了不少作品,小有名气了。
丁聪说:“我母亲生了十几胎,我为老大。我们兄弟姊妹成长起来的有六人。我早早地便肩负着抚养弟妹的责任。最小的妹妹比我小18岁。”苦难使人早熟,中学毕业,丁聪便急着想就业画画。19岁,丁聪便一面画画,一面当记者,在社会上奔波。
“8·13”至“7·7”事变之间的几年,丁聪的漫画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可以说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炮火改变了丁聪的思想,决定了他以后的创作生活道路。这种与国家,民族息息相通的深厚感情,像一条红线,从此一直贯穿于丁聪的作品之中,直到今天。
抗战之初,丁聪创作了不少救亡漫画;曾编辑过《战士画刊》,给《救亡漫画》不断投稿。上海沦陷后,丁聪来到香港,协助叶浅予编一部《日寇暴行实录》,和马国亮创编大型画报《大地》,宣传抗日英雄事迹,直到1941年香港沦陷才停刊。在香港的四年中,丁聪除编画报外,还有大量的创作作品。在《星岛晚报》上画过100套连载的漫画《小朱从军记》,在党领导的《华商报》上发表了《而公路依然伸展着》等高质量作品,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旅港剧人协会”,做了大量的舞台设计工作。
香港沦陷后,丁聪和一批文化界人士在广东党组织的协助下辗转来到重庆,继续以画笔从事爱国宣传活动。宋庆龄曾专门请丁聪等人到她家。宋庆龄一见丁聪便说“小丁,香港出来有什么损失?”又说:“我送你个东西。”说完便上楼取来丁聪与她的合影照。以后丁聪多次去过宋家,宋庆龄还总签名赠给丁聪一本英文版的《为新中国奋斗》,该书的封面是丁聪设计的。
这一时期,丁聪创作丰富,社会活动频繁。先后举办过“香港在受难”画展,与廖冰兄等10人举办过“漫画联展”,又搞了《北京人》、《家》、《雾重庆》等剧的舞台美术设计。这个时期创作的彩墨画《花街》,受到徐悲鸿先生的高度评价;创作的24幅《鲁迅阿Q正传木刻插图》获得了极高的赞誉,被认为是经典之作;反映大后方抗战悲惨生活的《现象图》为中外多家杂志报纸转载,蜚声欧亚。
抗战胜利后,丁聪又回到了上海,积极投身于日益高涨的上海民主运动。他创作了大量的思想内容深刻的讽刺漫画,挟击时政,揭露黑暗现实,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忌恨,以致有些作品一出来,便遭到国民党雇佣流氓的撕毁。这期间,丁聪以一个“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帮助共产党做了大量的党组织不宜出面做的工作。
当时年仅30多岁的丁聪被誉为艺术界的奇才。1948年底,周恩来向香港的党组织打电报,开列了一批文化名人的名单,“小丁”名列其中。
40岁的“小丁”当上新郎”
“小丁”好多地方让人羡慕。40岁的丁聪,已担任《人民画报》副总编兼编辑部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青联常委、中国美协理事、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但这时的丁聪还没有老婆,甚至连个“对象”也没有。这可急坏了朋友们。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与丁聪有近20年交情的夏衍当众宣布:“小丁如果今年结婚,一切由我包了,我请客。”
当时的许多朋友都为小丁的终身大事着急,冯亦代当时曾感慨道:“皇帝不急,急煞太监。”
36年后的今天,在我们的相“逼”下,丁聪老人有如下“招供”:
“我40岁前,一直在电影、戏剧、美术界混,按说成家什么的不会有啥问题,但我一直未谈过恋爱。当时,一些女明星常来我家玩。我思想正统,老觉得与文艺界的女性成亲,婚姻不会稳定,不愿与女演员谈恋爱,也不愿意轻易就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后来,抗战中,我先后去香港、重庆,萍踪不定,更无心谈恋爱了,倒觉得一个人生活得自由、便当。抗战胜利后,解放战争期间,我忙于画画,投身实际工作和斗争,也无暇谈恋爱,这事便一拖再拖。解放后,我一度曾担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还兼编辑部主任,什么具体事都得管,十分忙碌,个人的事也顾不上考虑了。1956年我40岁了,才碰到我的爱人。她在外文出版社工作,学俄文的,比我小11岁,与我妹妹是一行。我有一个朋友在外文出版社担任副总编,催促我成家,撮合了我们的婚姻。我们是1956年底结的婚,参加婚礼的来客只有冯二哥(冯亦代)一人。”
“猪比人好!猪不打小报告,猪有猪情味!”
丁聪结婚刚半年,便被打成了“右派”。
结婚一年后爱人生了孩子,丁聪没有享受初为人父的喜悦,只在医院隔着玻璃窗望了望自己的儿子,便被发配北大荒,劳动改造去了。
说起来颇有“讽刺”味。茅盾在题为《谈丁聪的(阿Q正传)故事画》一文中曾说:“‘小丁’给我的第一眼的印象是一位运动员,直到现在,我每逢读到‘小丁’的画,眼前便跳出一个短小精悍、天真快乐的运动员。”
“反右”以后20多年间,丁聪确实是一位资历颇深的“运动员历次政治运动中挨整的“动动员”
丁聪最初被送往北大荒,四年后又去了黄村干校。“文化大革命”中被不清不白地打发到最偏远的地方去养猪。直到1979年春节,丁聪才得到彻底的平反。
“文革”时造反派的头头让丁聪交待黄苗子的反革命罪行。黄苗子夫妇当时被关在监狱。早在30年代,黄苗子就和他熟悉。黄苗子参加革命很早,但30年代的国民党上海公安局长吴铁城做过他的干爸,所以黄苗子现在就“反革命”了。丁聪没办法只好交代“黄苗子这个人不够朋友,精得很,干了那么多的坏事,竟然都不给我说”。结果挨了一顿打。
吴祖光也“反革命”了,又和丁聪一起是所谓“二流党”的骨干分子,自然又得丁聪“揭发”。实在没啥可揭发的,丁聪只好老老实实地说:“吴祖光确实和我是老朋友,我了解他。我俩一起在上海主编过《清明》月刊。他不该在刊物上发表一些进步人士的文章,他也不该不先弄清自己姓啥为老几就给当时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