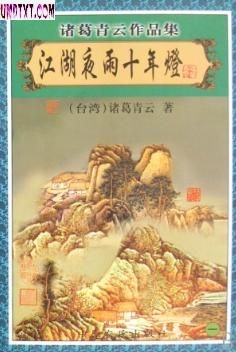读者十年精华-第174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饩褪呛罄吹母鹬薨庸こ獭�
作为三峡工程的实战准备,10年来,葛洲坝工程经历了24次大洪水的考验,大坝的沉陷、位移、渗漏量等均在技术设计允许范围内。它向世人表明,中国的水利水电科学技术是过硬的!
1960年,在全国万名科技工作者的努力下,国务院三峡工程科研领导小组提交了三峡工程的设计报告。报告说:坝址选定三斗坪,正常蓄水水位200米。
中央原定60年代兴建的三峡工程,因国家暂时的经济困难和国际形势变化而放慢了步伐。随之而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备战备荒任务,又使三峡工程被束之高阁。
星移斗转,正当国家又着手三峡工程前期准备工作时,重庆市人民政府对正常蓄水水位提出异议。他们要求将80年代初重新论证后确定的正常蓄水水位150米提高到180米,以使万吨船队能直抵山城。对这条建议,中央予以高度重视,要求专家们就三峡工程正常蓄水水位重新论证。这已是1984年的事了。专家们比较分析150、160、170、180、200米等不同蓄水工程方案的优缺点,综合多方面(水利、水电、航运等等)意见后,认为坝顶高185米、正常蓄水水位175米最合适。
就在1984年间,随着新一轮论证工作的展开,关系到三峡工程是否该上的争论再度白热化了。来自全国政协的多位委员明确表态:三峡工程不能上。海湾战争爆发后,有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发表文章,认为三峡工程上了,如被战争摧毁,后果不堪设想。
四百多名专家、教授经过又一次细致深入的论证后,向中央提交了新的可行性论证报告。报告中对三峡工程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提出了相应对策:如蓄水淹没35万多亩耕地后,土地资源紧张的问题,已开始试点进行开发性移民、合理利用现有环境条件的工作;针对水生珍稀物种生存受影响的问题,将采取人工繁殖的保护措施;还有水库泥沙淤积,采取“蓄清排浑”调度方式;加强对库区地震、崩塌、滑坡的监测预报;抓紧被淹风景名胜点的迁移、重建、复制工作等等。
万一战争爆发,如何防止因大坝被毁而危害中下游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专家们提出的对策是:首先三峡大坝采用重力混凝土方案,能防御常规武器的破坏;其次为防遭核武器破坏后造成下游大面积水灾,采取设足够量的泄洪低孔方案,以利临战时,将水位迅速降低,以减轻可能造成的水灾损失。若水位降到130米时,洪水将不会溢出长江中游的“悬河段”荆江分洪区,灾情较轻。
专家们认为,三峡工程经过几十年反反复复地论证,已相当全面、细致、深入,“方方面面,都已摸过多遍”,不会再有什么疏忽。因此,在新的可行性论证报告上,他们把千言万语凝结成醒目的17个黑字:三峡工程“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建议早决策”。
最后,我以毛泽东的诗词作此文的结束语:
……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
Number:6698
Title:欧洲奇城
作者:李原
出处《读者》:总第130期
Provenance:《自然与人》
Date:1991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加布罗沃幽默城
保加利亚中部的加布罗沃,人口8万,是个纺织工业城。市民机警而富幽默感,城市标志是只没尾巴的猫,城市名言为“世界完好,只因有笑”。市中心的五层“幽默艺术之宫”,收藏几万件幽默与讽刺书、面具、脸谱和雕塑品;看门老头与讲解员全都奇装异服,不停地与观众开玩笑。一年一度的国际幽默与讽刺节,展评各国幽默讽刺作品;是日市民狂欢,着古怪服装,罩各色面具,通宵舞蹈,比赛说笑话。1989年的滑稽游行队伍中,出现一辆满载废物的驴车,赶车人大喊:“我的家产能值多少美元?”另一辆卡车载着短尾巴的巨大布猫,猫身写道:“为节约能源剪短尾巴!”
哈默林传说之城
德国威悉河畔的哈默林,人口6万,歌德时代即被誉为“传说之城”。相传700多年前,哈默林鼠疫猩獗,一位穿花衣的笛手悄然而来,声称能消灭全城老鼠。他将风笛一吹,万千老鼠窜出住宅、阴沟,着魔似地跟着笛声跳进威悉河毙命。鼠害既除,市民却背信弃义,拒付讲定的酬金。笛手遂吹起风笛,130名儿童失魂落魄跟着他走,出城门,不知所往。悲剧广为流传,译成30种文字。哈默林人自此守信立诚,奉花衣笛手为神明,为之立塑像,年年举行笛手节,制作“老鼠糖”、“老鼠糕”、“老鼠尾菜”、“捕鼠人酒”,演出连场的笛手故事剧。节日那天,父母们高喊当年“中了魔”的孩子名字,不停念叨:“快回家来!”哈默林因“传说”致富,每年吸引20多万国际游客。
哥酋洛蛇城
意大利歌酋洛市中心有座纪念碑,矗立先祖圣达美尼科·阿尔培脱驯服巨蟒的雕像,碑身盘着许多活蛇。每年“蛇节”,家家将喂肥的蛇放到大街爬行,以示庆贺;不少人以蛇缠身,招摇过市。哥酋洛先民世代养蛇,靠表演蛇技、擒拿毒蛇、贩卖蛇药为生。今日哥酋洛工商业兴盛,操持蛇业的日渐减少,但养蛇玩蛇之风未变,因而老鼠绝迹。
古马尤滑雪城
阿尔卑斯山脉最高的勃郎峰下,意大利的古马尤城,居民3500人,却有旅馆85家,每年有50万人来此滑雪。主索道1956米,3分15秒就将游客送上高山大本营,然后有26条支索道伸向四面八方的滑雪场。每逢除夕,上万人手持火炬,彻夜滑雪迎接新年。“姑娘身上的酒店”随客登山服务,她们身穿长袍或紧身长裤,袍上有大小口袋几十个,内装一二十千克的酒、饮料、食物,游客一招手,即将布铺展在雪地上,让游客选食,吃多少收多少钱。
Number:6699
Title:父亲的音乐
作者:韦恩·卡林
出处《读者》:总第130期
Provenance:《青年参考》
Date:
Nation:美国
Translator:李颂
我还记得那天父亲费劲地拖着那架沉重的手风琴来到屋前的样子。他把我和母亲叫到起居室,把那个宝箱似的盒子打开。“喏,它在这儿了,”他说,“一旦你学会了,它将陪你一辈子。”
我勉强地笑了一下,丝毫没有父亲那么好的兴致。我一直想要的是一把吉他,或是一架钢琴。当时是1960年,我整天粘在收音机旁听摇滚乐。在我狂热的头脑中,手风琴根本没有位置。我看着闪闪发光的白键和奶油色的风箱,仿佛已听到我的哥们儿们关于手风琴的笑话。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手风琴被锁在走廊的柜橱里,一天晚上,父亲宣布:
一个星期后我将开始上课了。我难以置信地看着母亲,希图得到帮助,但她那坚定的下巴使我明白这次是没指望了。
买手风琴花了300块,手风琴课一节5块,这不像是父亲的性格。他总是很实际,他认为,衣服、燃料、甚至食物都是宝贵的。
我在柜橱里翻出一个吉他大小的盒子,打开来,我看到了一把红得耀眼的小提琴。“是你父亲的。”妈妈说,“他的父母给他买的。我想是农场的活儿太忙了,他从未学着拉过。”我试着想象父亲粗糙的手放在这雅致的乐器上,可就是想不出来那是什么样子。
紧接着,我在蔡利先生的手风琴学校开始上课。第一天,手风琴的带子勒着我的肩膀,我觉得自己处处笨手笨脚。“他学得怎么样?”下课后父亲问道。“这是第一次课,他挺不错。”蔡利先生说。父亲显得热切而充满希望。
我被吩咐每天练琴半小时,而每天我都试图溜开。我的未来应该是在外面广阔的天地里踢球,而不是在屋里学这些很快就忘的曲子。但我的父母毫不放松地把我捉回来练琴。
逐渐地,连我自己也惊讶,我能够将音符连在一起拉出一些简单的曲子了。父亲常在晚饭后要求我拉上一两段,他坐在安乐椅里,我则试着拉《西班牙女郎》和《啤酒桶波尔卡》。
秋季的音乐会迫近了。我将在本地戏院的舞台上独奏。
“我不想独奏。”我说。
“你一定要。”父亲答道。
“为什么?”我嚷起来,“就因为你小时候没拉过小提琴?为什么我就得拉这蠢玩艺儿,而你从未拉过你的?”
父亲刹住了车,指着我:
“因为你能带给人们欢乐,你能触碰他们的心灵。这样的礼物我不会任由你放弃。”他又温和地补充道,“有一天你将会有我从未有过的机会:你将能为你的家庭奏出动听的曲子,你会明白你现在刻苦努力的意义。”
我哑口无言。我很少听到父亲这样动感情地谈论事情。从那时起,我练瑟再不需要父母催促。
音乐会那晚,母亲戴上闪闪发光的耳环,前所未有地精心化了妆。父亲提早下班,穿上了套服并打上了领带,还用发油将头发梳得光滑平整。
在剧院里,当我意识到我是如此希望父母为我自豪时,我紧张极了。轮到我了。我走向那只孤零零的椅子,奏起《今夜你是否寂寞》。我演奏得完美无缺。掌声响彻全场,直到平息后还有几双手在拍着。我头昏脑涨地走下台,庆幸这场酷刑终于结束了。
时间流逝,手风琴在我的生活中渐渐隐去了。在家庭聚会时父亲会要我拉上一曲,但瑟课是停止了。我上大学时,手风琴被放到柜橱后面,挨着父亲的小提琴。
它就静静地待在那里,宛如一个积满灰尘的记忆。直到几年后的一个下午,被我的两个孩子偶然发现了。
当我打开琴盒,他们大笑着,喊着:“拉一个吧,拉一个吧!”很勉强地,我背起手风琴,拉了几首简单的曲子。我惊奇于我的技巧并未生疏。很快地,孩子们围成圈,格格地笑着跳起了舞。甚至我的妻子泰瑞也大笑着拍手应和着节拍。他们无拘无束的快乐令我惊讶。
父亲的话重又在我耳边响起:“有一天你会有我从未有过的机会,那时你会明白。”
父亲一直是对的,抚慰你所爱的人的心灵,是最珍贵的礼物。
Number:6700
Title:母亲不说那个字
作者:阿盛
出处《读者》:总第130期
Provenance:《广州日报》
Date:
Nation:台湾
Translator:
读大学时,老教授说过这么一个故事明末洪承畴曾经如是自道:“君恩似海,臣节如山。”后来降清,成了二臣传中人物,于是有人这般讥他:“君恩似海矣,臣节如山乎?”老教授说,所谓笔如刀,真是。
“嘴唇两片刀”,这句话,当年童稚常听我母亲说起。通常,小孩多话缠烦时,母亲总会训一句“小孩子有耳无嘴!”若是有人好大言,口涂蜜,母亲便会告诫一声“做人啊,重心不重嘴!”
其实,我昔时并不很明白什么叫做重心不重嘴,直到长大成人,有足够的智慧深入思考问题,这才回头想起母亲的言行如一自我开始懂人事起,一直没听过母亲对我们说过“爱”这字。
我母亲从未认识过一个字,她生养七个儿女,除了我在读初中时当过小流氓之外,其余都平平顺顺地被教育成国家栋梁。她付出的心血,纵使未必浩荡如黄河,至少也长流如我乡的急水溪。可是,她顶多只愿意对我们这么说:“阿母当然很疼你们。”
“疼”有两种意义。一种是疼惜,另一种是打疼。我在新营各戏院门口混太保时,三两个星期就打一次群架,由于彼时台湾经济尚未起飞,小太保打架是不用刀枪的。拳来脚往一番,顺便嚷叫几声,如此而已。糟的是,乡下人好管闲事,我打过架回到家,消息总是也差不多同时传到家。母亲处理的方式恒常不变,首先,书包放下,外衣脱掉,接着,到厅里面向墙壁站好,接着,母亲问清楚事情,接着,打,哭出声一定不准吃饭,连锅底饭粑都不准吃,接着,母亲叫大姐来替我擦药草汁,接着,她躲到内房里去哭。
母亲命不好,但是好面子。我虽是家中最常被打疼的小坏人,却也是最被母亲疼惜的大将才,我四岁就会画福禄寿三公像,七岁时写的字就比读高中的六叔还漂亮,唱歌考试作文等等比赛的奖状多得墙壁贴满。母亲对我有厚望,期盼我为她争面子,她打疼我之后,通常隔几天就会对我说:“盛也,枉费阿母疼你啊!”
我也是个会心疼人啊,终于,我立定决心不再“行走江湖”,收拾起那分“称雄武林”的少年野心,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