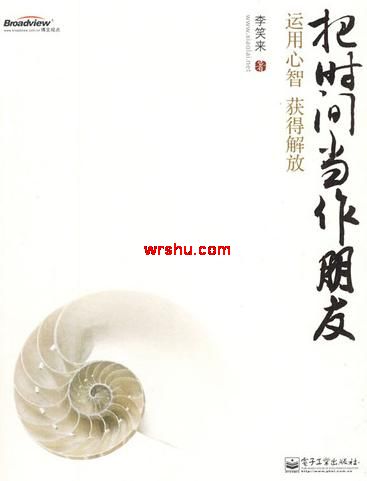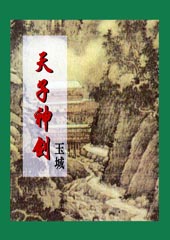知君用心如日月-第1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十七 玉窗红子斗棋时(2)
晋人说,棋为手语,她这一招,如此的蛮,对面弈棋人,一下子便明了她心绪的不稳,掩口一笑,心中并无千万雄兵之戾气,于是淡淡出手,不忍伤她,使棋局两两对峙,谓之双活。
身边侍女珊珊而来,端来了两杯刚刚淘制出来的玫瑰露,时值春末夏初,风清日炎,正好可以消渴。两人端起杯来,看亭树间有双燕剪剪而飞,海棠花瓣不经意间潇潇落下,两人相视,不由会心一笑。
知道赵令畤还是缘于他那个香艳的‘二十八字媒’。 赵令畤本是皇室后裔。元佑中时,结识苏轼,并于其交好。他贤妻早丧,却念念不能忘,尝凄然有悼亡词:
东风依旧,着意隋堤柳。
搓得鹅儿黄欲就,天气清明时候。
去年紫陌青门,今宵雨魄云魂。
断送一生憔悴,能消几个黄昏。
可巧这同城有王氏女,岁已壮年,父母为其择偶,却屡不称其心,心心念念欲寻得有诗心的才子为婿。并作《咏怀》诗:
白藕作花风已秋,不堪残睡更回头。
晚云带雨归飞急,去作西窗一夜愁。
赵令畤见其诗词语工丽,语意深婉,女儿心思似是一只鸟,从白藕池花中扑扑而出,化作清愁,飞至西窗。词中清丽无助的闺怨,正暗和了自己失伴的孤独失意,读罢此诗,心早已随人绕天涯,于是请人为媒,欲与王氏女成其姻缘。那王家姑娘终是苍天不负她,终于等到了自己梦中人,两人相遇,各是惊喜到心里去,遂成眷属,恩爱终老。
刚才还在紫陌青门徘徊,口口声声说为妻断送一生,只为这王氏女的二十八字便已然魂倾。
赵令畤也一定是曾经看见新妻与人斗棋,他人在书房,外面风清日暖,唯听见棋子啪啪而落,他走出来,外面正花风阵阵,妻午睡初醒,正一身慵色,在亭上与人对弈,自有一种随心自适、逸神闲情。
所有的一切,是这样的静美,圆满,如他开篇之句:水满池塘花满枝。满得还似是要溢出来。
十八 掺掺女手,可以缝裳(图)(1)
自己手也纤纤,可是不会缝裳。穿针引线,为亲人缝制,长长的一件衣服,想必得用上数日光阴,日日捧在手里,铺在膝上,一定是有人生的大爱在里面。那衣服也会如软玉一般,温润地有了性情,穿在身上时,那不寻常的感觉,可以入诗的。
我真是喜欢画里的光阴岁月,这样缓缓地,在亭台的芭蕉树下面,缝着一件衣裳。那衣裳清风抚过,有蕉叶的清阴,树下刚才还有一只仙鹤,修长的颈,啄着羽翎,临水照花一样的娴雅淑静。
风透湘帘花满庭的好日子,四个女人,从陈年的箱子底下,搬出来各色宫匹锦缎,铺展开来,裁定、熨贴,为一件衣服,围坐在一起,这样风清日艳,都有了好性情,好心思,人也变得慷慨亲切。“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四个女人心有深爱,愉色婉容,将富贵花开、金玉满堂、山河日月绣了个满衣满衫。
古人制物都寓着个理儿,制冠有冠理,制衣有衣理,衣服上如有这些繁华大气象,人也会清晏沉厚,必定坚起一个信念,堂堂正正地走在岁月里,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男人着上此服,有了王者镇重、安静四方之风仪。那“衣理”束着他,也照在扰扰人行过往处,邪僻之心也不得而入了。家中的女人有此灵慧的内心,男人在外面也会心性平和,眉清目扬,事事占得一个先机先运,福禄寿禧天也赐。
而这女人终是“碧梧栖老凤凰枝”,庭院深处,琴瑟在御,岁月静好,原是福与慧双修而得的。
纤手所制,因为有心思,有对话,有交流,穿着之人也必定在有一刻感怀。或远行或羁旅,愁思怅然时,睹物怜人。“此中虽云乐,不如早还家”的念想是怎样起的呢,必定亦是低眉敛首心有落寞的那一刻,看见了那个用尽气力与心思的《如意云锦图》的衣纹,贵气而贞静,突然让人那么强烈地开始想家,想念堂前一几一桌一瓶一花,都有妻的温婉笑语、眼光如波徘徊流连。万事万物如有让人琢磨让人寻味的,便多了自身份量以外的东西,就格外让人珍惜。衣物也不只是用来暖身,它也有着太多的东西附着。
唯其美,还因为它的“缓”,“缓”便有养,有养便有韵。这个养字是一种蕴含收集,收集心思,想了又想,改了又改,最后得了一个最完美的。因为缓,给了自己重头再来的机会,所以这样翻来覆去地就有了感情,无论衣衫穿在谁的身上,几时看到,都有一种亲情。
此画题跋出自《诗经·魏风》:
掺掺女手,可以缝裳?
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
维是褊心,是以为刺。
以《诗经》里的《魏风》点题,让人想起劳作的和谐之美,无论是身在候门,亦或是落在贫家,图中所绘的场景也是和气而贞静,上下有序的。
《诗经·国风》源于礼乐行起的周,那时人们有了私有的井田,人也大气开豁了,五谷黍麦,花初叶嫩,有了自己的田产,可以随意耕种,人与人之间有了不一样的东西,可以相互欣羡,人也有了个性的扬溢,我猜想有那么一个时期,社会和谐,人们是快乐劳动的。“掺掺女手,可以缝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缝裳也开始有人歌了,闲暇之余,人们有了心情来关注一下别人的生活。“掺掺女手”之中的那个“好人”的不配合,想必也是一时兴起,撒娇使性子,有人便站出来说说她,口气也像是堂上婆婆。我读着不觉是讽诗,只有一家人的平和热闹。
那个男子在山下田陌劳作,亦想念着采萧的人: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真是丰富饶足的生活,采萧采葛采艾,在他眼里成了最美的舞,想那女子在田间山上的风景里,采葛之时也一定眼波顾盼,与那男子目光相接,瞬间就爱到了心里去。他也真是想思得苦,须臾不见,便嚷嚷着如隔三秋,被煎熬的劳动也不能了。
十八 掺掺女手,可以缝裳(2)
那种有点赖有点玩世的无俚头,原来周人就会。
彼时的人们对于财物没有野心,所以这样知足而乐,人的心思亦如春天里的桑树嫩芽,艳阳初露,饱满、润泽、惬意,满是清平的希望。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
简直是最美的田园诗,没有隐忍,没有压抑,稼穑之人像是王公士人一样贵气,有田亩有桑园有家有爱人,什么都有了。我还不知道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踏实和心安的生活,所以可以穿得像士人一样宽敞舒适,与爱人到处游玩,然后执手而还。
劳动成了歌,也入了诗,因为人们心里自在,可以这样一吐心曲。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思我,岂无他人?
你若爱我,就涉溱水而过,来找我,你若不爱,哈!难到这世上就没有别的男人了吗。少女无所顾忌地恼了,指着她爱的人,劈头就甩下两句掷地有声的话去了。男人一定是唯唯着,左右不是。
而汉乐府里劳动的歌,就变得更加华美而有韵致,人们不只是性情的表达,更有一种天地之初的大气与贵气:
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
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
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
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
出去采桑,也穿得那么好,缃绮紫绮为衣,满头乌云也是斜斜地偏在了一旁,双耳戴得坠子也耀亮如明月,那个盛桑叶的笼子更是那么精心有情致,青丝为系,桂枝为钩,香馥馥的倚在她的臂弯里,满满一笼全是好心情。她后对使君说的那番话,那样义正而心思明阔:
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先就自己把自己看得贵重,倒是使君相形之下见得自己的卑微,他一定会知趣而退。出来采桑也是一种游赏,不想碰见无礼之人,自已三言两语说得他回头就走了,不但没扫了兴,更见得社会的清明,人事的丰富。
在田陌深处,恍然听见谁家女人,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近若远,忽断忽续。这样的劳动是为了享受,不是为了贪欲,所以如此明媚,歌者欢悦,听者清旷。
田间坊里,人们心思明水如,缓歌度日,无时无序。一针一线,一锄一耕,都是喜乐光阴。
《拾玉镯》就是这样的天成佳会。孙玉姣在家中挑针纫线的时候,俊哥儿付朋怀着玉镯就来叩门了,正好妈妈去前村听经去了,她开门看见付朋貌似潘安,温温儒雅,也就喜滋滋地大着胆子收了,不巧被邻居刘妈妈看到。后来经刘妈妈撮合,她回赠了付朋一支绣花鞋。这一来一去的婚姻就在这针线女红里安排定,机缘巧合也是如此委婉有深意。
“豳风”本就是今陕西地区的民风民俗,此画为清吴求的“豳风图册”之一,画意中描摹的即是民间的活泼清贵。
十九 昔年曾见(图)(1)
明月白露,光阴往来。
与子之别,思心徘徊。
南朝 江淹 《别赋》
看着眼前云树苍苍,山峦如黛,心中却空无一物,恍惚已记不得与你何时相见何时别离,从春草碧色等到秋露如珠,一年一年我只是等……可是唯见明月耀白露,心中早就是一层淡淡的霜色了,没有了相思,唯见日月来去,光阴回环。
情到深处情转薄,是一把刀深刻在生命里了的痕,这么多年早已不知道什么是痛。唯有月下清辉里,一声轻叹,不提也罢。
唯有在这样的暮色里,想起少年的他,从远处走来,身披一身清淡的灰,像是夜深时悄悄从窗棂里度进来的月光,深婉如水,有一种不经意的喜悦。而那一双温情的眼正语笑晏晏,望住我,我蓦然就呆了,他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他怎么就知道了?可是,他只是这样走过了,什么也没说,原本他或许是想说什么来着,不然为什么他会对着我而来。那一刻我断定他是为我而来的,可是他终是什么也没说,沉吟了一下,他在我的身旁。我几乎就闻到他身上的味道了,听到了他咻咻的鼻息了,可是他终是身子一闪就去了。
那个长衫少年。在上元之夜。
可是去看灯会的路有千条万条啊,可他为什么偏偏就走过这条清越越的街呢。
桃花几度开落,他们之间却无故事。
提亲的人来了又去,可总不是他,那个在薄暮清寒里相见的少年。她在深闺的夜里,望着月亮一遍一遍地想:
为什么乍见他,就像是前世的宿命一样心痛神痴不能逃离。可既然是宿命,为什么却没有那根相牵的线?那天怎不在他眼底下遗一方帕子?上绣着并蒂莲的那方,或是题着‘闲却秋千索,寂寞梨花落’的那方。或是遗下一只翠凤的宝钗,他拾在手里,睹物思人,难保不动攀折之心。钗上蝶双舞,宝钗本成双,另一只还簪在佳人头,他诗书之暇,拈在手里时,或许相信这份姻缘原是前生定,不管千里万里也总还有个寻头。可是那天我什么也没做,他也是。如果光阴可以倒转,我一定在那个淡淡地暮色里,迎上他的眼光,走上前告诉他:‘奴家姓李,名叫青鸾,家就住在这条街的尽头,那个黛瓦粉墙的宅院里,父亲即是告老还乡的李员外……’要一口气说完,说完转身即走,不看他的脸,一切交于天安排。不知这样可不可以把宿命的人儿抓在手。”
世上最痛的是莫过于日日为他情思奄奄,却不知道他是谁。
日子如流水,一年一年过去,待字闺中的她再也不能等了。她嫁到一个本地最大的绸缎商人家,夫家家道殷实,夫君是嫡长子,也读些诗书,管些家事,与她年岁相当。只是模样气度与那个少年相差甚远。她虽富足安逸,却终有失落。多年来不敢想象那个少年郎,自己为人妇为人母,一切像是人家画好了的线,她只沿着这条线走即可,她没有一件事是拗过了命的,所以她谁也不怨,一切顺其自然,她也从不争,只是默然接受,她断定这即是天意。
二十年过去了,她依然似是什么也没经历过,她有时看着堂前穿过的爱子娇女,有刹那的陌生,突然这一切像是跟她没了关系,她只想收拾了自己的金钗翠钿、针线女红回她的娘家去,躲在自己的楼上,继续绣她从门前货郎那里买来的各种花样子,然后再提上几行字,这几行字她已仔细推量了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