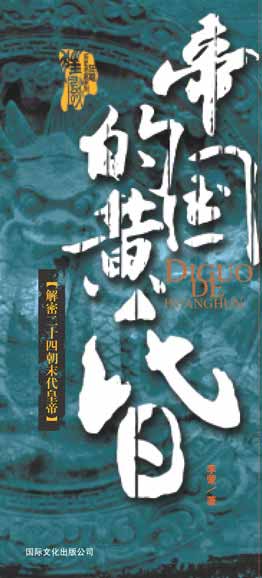厚厚的黄土层 周国春著-第6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不去找他,狐皮沟永远是我的家。”林昊这样说。
七年以后,林昊仍然是一个人过活。学校里沈虹虹在追求他,他还没有动心。他和末末、小南仍然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鸡娃上了大学,又留学美国,已经在攻读博士学位了,这如同在山里放了一颗卫星。根柱在部队里当上了团长,成了家,想接他大和娘进城去享福。寻老六两口子不去,他们不愿意撇下秀秀。茅缸的婆姨生了双胞胎,两个儿子都念书了。那个念娃如今上了川坪中学,住在林昊那里。
1987年的秋天,林昊收到了丁胜从法国巴黎寄来的信。第
二
十
九
章找回失去的爱
是的,丁胜在巴黎,他正在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他给林昊写信的时候,才刚刚来到巴黎三个月。
1986年的暑假,丁胜从就读的齐鲁大学回到了海边。
人的一生将要走过的路,是会为人所言中的。也许爷爷和他的同僚们都是预言家,在他过百天的时候他们就说,他不是将才,是的,他与绿色的军营是没有缘分的。他不会去做买卖发大财,是的,他不仅不是一块经商的料,而且点钞票都令他头疼。大概是穷惯了的缘故,一百元对于他都是一个大数目。莲花妈妈说他长大了,当年爷爷为他留下的一笔钱,现在到了交给他的时候了。但是,他死活不要。他是一个舞文弄墨之辈,这却让人们说着了。他在圆爷爷的梦。爷爷说过,要让他的孙子“披挂博士盔甲”,换一个活法,他现在就是按爷爷所说在活呢。
离开了那个埋葬了他的爱,撕扯他的肝肠到断头的狐皮沟,他来到海边的咪咪村。他像是重新投了一次胎,从混沌、缭乱的自我之中走了出来,如同刚刚离开了母体,睁开眼睛,好奇地看着陌生的世界。这里的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颖,新颖到令他幼稚地瞪大了眼睛。眼前的景清晰似画儿。蔚蓝色的海洋深情地拥吻着远天到不分彼此。岛儿、云儿、船儿、人儿、海鸟儿仿佛有条不紊地出现在同一幅画面上,俨然又是浑然一体的,你为我涂色,我为你调情,它们共同托出了日月、星辰。海天是那样的阔绰,阔绰到没有边际。
从日出,到日落,海天朝气蓬勃,汹涌澎湃,荡涤着一切污泥浊水,洗刷着人的灵魂。挫折、哀怨、忧伤,为博大的海天抹平了。
当月亮船载着星星在海与天之间荡漾的时候,又是那样温馨地在抚慰人,不是吗?渺小的命运溶入那浩瀚的海天,个人,人类,事业,永恒,丁胜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开通。海洋就是人的心,它是不会平静的,这不平静,就像是人的心脏在不停顿地跳跃。然而,只有当人们能够认识到海和天的浑然一体,才能够真正懂得,为什么人的心要比海大。比海大,大到可以忘记自己的渺小,自己的所缺,自己的创伤,自己的痛楚,而重新扬起风帆去远航。因为心比海大令人懂得了振作。虽然儿时爷爷带他来过这里,但是他还不懂得将自己的命运与海天联接,不会有如此驰骋奔放的情怀和畅想。
如今不一样了,他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男子汉了。
咪咪村并不是因猫咪而得名,是因海鸥而得名,它是一个小渔村。这小村是一个小小的半岛,像是一个婴儿从嘴里吐出的舌头,舔着大海的乳汁儿,那么津津有味。这舌头上有溶洞,有海蚀的悬崖陡壁,所以,这里栖息着许多的海鸥。清明节前后,它们像是八方来客,似云团一般飘落于悬崖陡壁之间,做窝,做爱,产卵,繁衍。渔民们从不惊扰它们,让它们与日月同在。它们也亲近人,与渔民一同出海,飞累了,就在渔人的船头上歇息。海鸥叫起来是咪喵咪喵的,像可爱的猫咪,永远为渔民们传送着平和、宁静的祥波。渔人喜爱这些美丽、吉祥的海猫子,不知道从哪朝哪代开始,他们把自己居住的小村庄起名为咪咪村。这里是丁胜的家,因为莲花妈妈在这里,佟辉爷爷和吴奶奶也在这里。在这里,他的魂魄与大海同唱,与海猫子同乐。生活在他的眼前焕然一新了。面对大海,遥望与天衔接的大洋,佟辉爷爷问他:
“黑毛头,还记得黄河入海流吗?”那个已经长大的黑毛头开怀大笑,因为他懂得了黄河入海的壮阔和宏伟,幼时的恶作剧是何等的荒唐!
“不要忘记爷爷,他要你做什么呢?”他的亲人们这样说。
丁胜又一次找到了爱,找到了似乎远去的爱,他要给这爱以还报呢。
197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齐鲁大学历史系。快满三十的人,不能与小他十几岁的人争雄了,所以他没有报考理工科。学文科,岁数大一些还是可以的。他考了他所在地区的第一名,他的亲人们乐了。在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他对着北北的相片,和她说了一夜。
“北北,我终于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去考大学了。”北北微笑着似乎在说:
“我知道了,你想什么,干什么都是不会瞒过我的,对吗?”
年9月25日,教育部决定恢复高考,
“北北,你知道吗?1977
多少人的命运在一夜之间突变,可以求学去了。你为什么不考呢?
也许你那时考走了,我们是不会分开的。”北北还是那样微笑着,好像在说:
“你怎么忘了?你写给我的信中说过的,要我去考,我是怎么说的?”
“我想起来了。你说,等我回到你的身边,我们一起去考大学。”
“你怎么说的?”
“我说,我怕是不行的,我这狗崽子的血统,不会让我心想事成的。”
“所以,我说,我要等着你。”她微笑的唇调皮而固执地翘起,那样子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为什么要苦苦等我?为什么?”
“呆子,不是爱你吗?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我还爱过谁呢?”这声音仿佛就敲击着他的耳畔。
“爱我,为什么不等我?”
“永远在爱你,永远在等你呀。”
“不,你没有等我,你走了,走了。”硕大的泪从他的眼眶里跌出。
“我在广袤的宇宙间等着你,不好吗?我们都是宇宙之子,我们彼此忠诚地等待。真的,爱你,等你,不是吗?现在一切都好了,你终于不用去想你是一只狗崽了,对吗?”她微笑着,像是为亲爱的人高兴。
“你知道嘛,我是多么的想你。我想你,想你。宇宙太大了,我找不到你。”
“我吗?我在那天的尽头,你一定会找到我的,你学成了,干成了,活够了以后,就来找我呀。”北北微笑着注视着她的丁胜。
是的,他还在她的心上,她呢,仍然在他的心上。
“天呀,想你,想你,多么折磨人!多想见一见你,见不到哪怕能梦一梦,可是无论如何呀,也梦不到你,梦不到你,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丁胜亲着北北的相片,仿佛听到他的北北在轻轻地说:
“我不是你的梦,我是你的心呀。我也想你。你会来找我吗?”
“会的,我会去找你的。你和我的爷爷在一起吗?和小娟姐姐在一起吗?”北北仍然微笑着,又像是在说:
“是的,我们在一起,我们都是天上的星,天天都在看着你。
你不会失去我们对你的爱,不会的。去吧,人间的春天在召唤你呀。活着是多么的好啊,你是一个幸福之子,对吗?抬起你男子汉的头,不是有海洋和苍天为你助威吗?你应该是一个强者,不能总是这样想我想得伤心呀。”
丁胜泪眼模糊地吻他的北北,然而,那不是一个活体。最后,他不得不收起了他的北北。他一把擦干了男人的泪。
于是,他像是一个游泳的健将,一个猛子扎进了知识的海洋,除了需要换上口气,好继续向前游,他是不会把头露出海面的。四年的时间,他取得了学士学位,毕业了。他又考取了研究生,专攻外国史。那外国史,他最痴迷法国史。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百姓居然捣毁了封建王朝的巴士底狱,以后,又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巴黎公社。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人又驱逐了法西斯德国的占领军。李北就说过的,她很佩服戴高乐将军。法国投降了,他却打出“争取民族独立”的旗帜。丁胜和那时的千千万万的中华学子是一样的,当然,还有他的那个北北。尽管是在农村,他们仍然读大量的书,对于特别能战斗的民族颇有好感,尤其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抱有极大的兴趣,倾注了浓厚的感情。当然,法国又是一个文学巨匠云集的国家。从上中学开始,他和李北就涉猎了不少外国的名著,从小说中在读法国。雨果的《悲惨世界》、《笑面人》,他们是一起读的。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系列,李北则更加喜欢,尤其是那本《高老头》,她读了不止一遍。在她的日记里,有她写的心得体会,丁胜经常翻看那三本日记。如今,自己对于法国,要比北北是精通了。他成了研究法国历史的专门人才,当然也研究法国文学。那里有《巨人传》的作者弗朗索瓦·拉伯雷,他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人文主义作家;那里有法国杰出的古典主义戏剧家莫里哀,丁胜喜欢读他的《吝啬鬼》,他笔下的阿巴公六亲不认,儿女不顾,恋人不要,只爱钱(这也是一种爱,爱到失去了人间的真情);那里有以哲理小说《老实人》著名的伏尔泰;那里有《红与黑》的作者司汤达;那里有《基督山伯爵》的作者,法国资产阶级浪漫派作家亚历山大·大仲马;那里有《茶花女》的作者小仲马。那里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作家简直是太多了:雨果、梅里美、莫泊桑、巴尔扎克、福楼拜、都德、左拉、罗曼·罗兰、凡尔纳、巴比塞丁胜陶醉着,可以忘掉一切。然而,他也有苏醒的时候,会记起恍如隔世的那个黄土窝,那里有像信天游一样美好的秀秀,还有那个他不曾见过的儿子。他寄给林昊一笔钱,这是爷爷留给他的那笔钱的一部分,从莲花妈妈那里取出这笔钱的时候,他说要资助一个山里的朋友。他在信上对林昊说:
“这钱用于念娃以及他妈妈的生活。用你的办法贴补他们,要告诉他们这钱是我给的,暂时就说是你的钱。总有一天,我会去找他们的。因为,我还没有学成,还没有与他们团聚的资格,没有心思完成感情的转折,去面对他们母子。也许你会认为我太怪僻了,太不尽人情了,但是,不知为什么,我此时的神经仍然是僵持的,除了李北,我谁也不会去想的。但是,我毕竟是一个儿子的父亲,这是事实,我不想赖,赖是赖不掉的。我不会去逃避抚养儿子的义务,这是我一个做父亲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我不曾见过他。秀秀仍然一个人守着儿子。我欠秀秀的债,不是说还就能还清的。我想,毕竟李北已经去了,等我学业有成的那一天,我会认真考虑我的生活,会把他们接到我的身边。”林昊理解他,他知道,人的感情就是这样专一,专一到常人不可理解,这没有办法。然而,一个男人,不该是这样吗?对事业,对女人,因为都是可以爱到痴傻的程度的,所以这专一是难得的,难得到可以令人起敬的。
林昊应承了他所拜托的事,这对他是一种宽慰。秀秀和念娃,他会照顾的,至于丁胜的钱,他存了起来,等到丁胜来寻这母子俩的时候,他会把一切说清楚的,会的。于是,他把这事情做得很完美。
他毕竟和寻老六一家人有着特殊的亲情,这亲情虽非同手足,却足以使他们彼此间牵肠挂肚。
就这样,时间到了1986年。放暑假了,丁胜在咪咪村与人间的亲人们在一起,与自然界的海鸥们在一起,在恬静和深沉中,在躁动和浪漫中,敞开了胸襟,尽情感受着大海和蓝天厚重、辽阔、温暖的情怀。他从书海里游到了岸上,在家里歇息。
这一天,母子俩坐在院子里,院门开着,有一条路通向大海边,那路啊,像是伸到了海底。海边有嬉戏的一群小顽童,一丝不挂,他们从海里走出来,又回到了海里。他们爱海,离不开海。远处几只渔船,和云儿一起像是在天上荡。海猫子忽而天上,忽而海里,忽而船头,在飞?在钻?在蹿?莲花妈妈问他:
“你为什么不成家?”她并不知道丁胜有了儿子。丁胜和她对答,但是只有前一句话是对妈妈说的,后面的话,自己在对自己说呢。
“还不到时候。是的,渔船还不到返回的时候。”
“要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你的儿子念完书。是的,渔船有归时。”
妈妈想着孙子,你爷爷奶奶们想着重孙子。
“会有的。”人类的繁衍,是不会断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