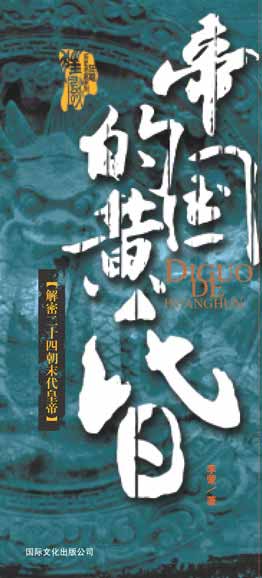厚厚的黄土层 周国春著-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是答应了?好吧,这件好事做成了。”待老首长喘过气儿来,按照自己的理解,说出了这么一堆话。他一想,算了,就这么着吧。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部队进城了,在北平的一间平房里,他和姚慧敏,着军装,夹在笑闹的人群中,由老首长兼媒人证婚。老首长当时是这样说的:
“李炳彪在革命的征程上,选择了姚慧敏。他们是战友,现在又成了夫妻,这不只是他们的需要,也是革命的需要,我们祝他们幸福。”众人的掌声在笑声和叫好声中响起。他不能说是在叫苦,因为他和慧敏虽不是一见钟情,也还是一见就颇有好感的嘛,这,他是不能赖的。但是,要说娶了慧敏,完全是出于自己恋爱之后的选择,他是不能够同意这种说法的。
“女儿在这里跟谁过呢?”章可言又在问了。
“跟我娘啊。”
“那么我们去的是您的老家了?”
李主任摇了摇头,他哪里还有老家。
“对了,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这故事是李主任的女儿给我讲的。”小刘开了口,引出了一个新的话题。
“讲一讲。”一车人都来了精神。
“她会讲故事?”李主任似乎不信。难怪啊,他认识的那个女儿,是个两岁的毛丫头,还讲不出个有头有尾的故事。尽管自己想过多少次,她已经五岁了,五岁了,但那个叫自己叔叔的小小的影子似乎缠定了自己,赶也赶不走的,挥也挥不去了。“是的,上个月我来的时候,她正出水痘,发着烧,不能四处跑,才安安静静地坐在了我的腿上,说奶奶给她讲过一个好听的故事。她讲,你看到那边的山,还有那边的山了吗?那原来呀是一个白胡子老公公砍的两捆柴,是担在他的肩膀上的。那个能通到天上去的柴峰,是老公公好大好大的头变的。奶奶说,他救起了一对小鸳鸯,天神就把他变成了高高的山,让我们天天都能看到他。她问我,叔叔,你知道什么是鸳鸯吗?我说知道,是那种会游水的好看的鸟。她说,你才不知道呢,鸳鸯还会飞。它们是一个美丽的大哥哥和一个美丽的大姐姐变的。它们永远在一起游啊游啊游,不分开。它们不愿意分开,别人也没有办法分开它们。没有它们就不会有我们,这是奶奶说的。你不信吗?问问你的奶奶去!”
一车人都笑了。这个故事的确很美,很甜。鸳鸯戏水是人间自由恋爱的写实,所以,人们画鸳鸯能惟妙惟肖,说鸳鸯能如醉如痴。因此,这个故事任谁去讲,任什么时间去讲,都是那样的动听,令你去遐想。
车在村口停了下来。
一群孩子围了上来。小刘看了看,这里面没有妞妞。孩子们怯生生地用眼神向这些大人们吐露着自己的心声:
“我们想坐一坐车。”
一个脑袋大大的男孩子,也就五岁大小的样子,他毫不认生地瞪起圆圆的眼珠,笑嘻嘻地央求着司机老王:
“大伯伯,让我们到车上坐一坐,坐一会儿就下来,行吗?”
“如果坐上去不下来怎么办?”老王逗他。
“不会的,我们拉勾,说一不二。”他的手指勾住了老王的手指,使劲晃动了两下,简直不容分说。
“喝,还真是条汉子。”人们都笑了。
老王打开了车门,几个性子急的孩子,已经钻进了吉普车。
小刘拍了拍大脑袋男孩的小肩膀:
“小老虎,你先告诉我妞妞在哪儿,再往车里钻。”
“她呀,你们看,那不是吗?”
几个大人的眼睛顺着孩子的手指望过去。不远处是一片菜地,红、黄、绿、紫,色彩鲜艳。一位头上笼着手巾的老妇人在摘菜。
身边一个小姑娘,穿着红花小褂,蓝花小裤,像一只花蝴蝶翩翩起舞。她从黄瓜架下钻过来,钻过去。呦,她是在捉一只蜻蜓,捉住了,捉住了!她叫着,她笑着,像是在敲一只银铃。她又张开了小手,飞吧,飞吧。小蜻蜓飞走了。来的人朝她们走了过去。老妇人直起腰来,摘下了笼头的手巾。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眼角那些挤在一起的深深的鱼尾纹,衬托出一对又大又亮的眼睛。人们走近了,也看清了。小章一怔,他揉了揉眼睛,揉醒了记忆。难道真的是她?
“小刘叔叔,是你来了呀。”小姑娘张开了双臂。
“妞妞,还要不要叔叔举你飞一飞?”小刘也迎了上去。
“不了,奶奶说我大了,会变成一只真鸟,飞得高高的,飞得远远的。”妞妞虽说是不飞飞了,但扯住了小刘的双臂,乍开小腿,让刘叔叔抡她转了三圈,兴奋得大笑,鼻子、眼睛、嘴全挤在了一起。
“娘,我又来看您老人家了。您身子骨还硬朗吧?”老妇人喜欢得眯起了眼,上下打量着眼前的儿子。她生过五个儿子。大儿子死在逃荒的路上。二儿子在阎锡山的部队里,战死在军阀的混战中。
三儿子下煤窑谋生,煤窑坍塌,被砸死了。四儿子给村子里小学校的先生背柴,认识了字,干起了为穷人翻身解放的大事。她的家也成了同志们聚会的地方。她学会了为他们放哨,传递情报。儿子在执行一次任务时牺牲了。她擦了擦泪,把最后一个儿子送给了解放军。她自己呢,像四儿子那样,干起了秘密交通。儿子的首长在打淮海战役时受了伤,从腰里取出了炮弹皮,手术台就在柴峰口。手术失血太多,需要输血,她挽起了袖子。一位母亲的血给了最需要的人。在她的精心料理下,那个人的伤好了,临走时,叫她作娘。
她认下了这个儿子。
“娘好,身子骨也硬朗,就是腿脚没有以前利索了,妞妞要跑了,我是追不上了。倒是你自己,要会操心自己的身子骨。慧敏同志又照顾不上你。她好些了?”
“她的病好了。医生说,她的肺部有了钙化点,不会传染孩子了,所以我这次来,就把妞妞给她接回去。”
妞妞抬起头来,听到有人在叫着她的名字,知道大人们在说她。
“妞妞,你看看,她是谁?”老人指了指李主任。
看着眼前那个陌生的人,妞妞不响。
“我是你的爸爸。”李主任蹲下来,把妞妞揽在了自己的怀里。
“叫呀,妞妞叫爸爸呀。妞妞乖,快叫呀!”奶奶在哄她。
妞妞笑了,从爸爸的怀里挣脱了出来,捉住了小刘的一双大手。
“妞妞,刘叔叔说过的,是爸爸和妈妈让叔叔给妞妞和奶奶送生活费的呀,好让奶奶给你蒸馍馍吃呀,把你养得胖胖的,让你长得高高的,再来接你,对吗?今天呀,我们就是来接你的。”
妞妞想了想,许多事她似乎还想不明白,想起来太费劲儿。本来嘛,奶奶疼她,爱她,还有娘,是她和小老虎哥哥的亲娘,因为他们是吃着娘的奶才长大的,他们的爹在朝鲜打美国鬼子,这不是挺好的,怎么又生出个爸爸妈妈,生活费,接走她。爸爸妈妈在墙头的那片纸上,她从小就认识。生活费,是什么东西?没见过。接走她,这大概是大人们的事。她不想管大人们的事,也管不了。随他去好了。她不点头,也不摇头,只冲着刘叔叔眨巴眼睛。
言已经无法再抑制自己的感情,他抢前一步:
“大娘,您看我是谁?”
老人眯起眼盯住了小章。
人们看着眼前的一幕,好生奇怪。
“大娘,您不认识我了?如果您还记得:
‘大娘,这萝卜的心不糠吗?我还是要大白菜吧。’‘糠不糠,你瞎大爷最清楚。’
‘我瞎大爷出远门了,走的时候交代过,买两棵大白菜。’‘大白菜让虫子吃了帮子,不好放,你还是买萝卜吧。你买了我的萝卜,大娘我再送你两棵大白菜。’”,老人急着向前跨了一步,这是真的?她认出了眼前的人。
“小伙子,你知道我住在这儿?”老人摇着小章的手臂,她激动得流出了泪。
“不知道,我不知道。”是的,他不知道,自从那次脱险以后,他再也没有见到过大娘。
那是八年以前的一个秋天,在燕城的南门外,正逢大集。他去找一位卖菜的老妇人,取一份重要文件。他和老妇人单线联系,不知道老人家来自何方,甚至于过多的问候在他们彼此之间都是没有的。
那一天,集市上热闹非凡,有犬吠,有鸟鸣。这靠城门的集市,是狗市,又是鸟市,还有蔬菜、水果、花卉,有针头线脑小花布,还有各种小吃。小贩们的吆喝声、大人孩子们的嘻笑声、吵闹声和作一团,乱成一片。他在集市中穿行,穿着长衫,头戴礼帽,不时和来来往往的人碰撞着,出了一身臭汗。他很不顺利,早上一出门,屁股后头就有了盯梢的,绕了几条街,黄包车、有轨电车换了几次,又几进几出地钻了胡同,自己认为总算是把尾巴甩掉了。
在老妇人的菜摊前,他收住了脚,弯下了腰。他们像往常那样老道而快速地对完了暗语,他机警地眨巴着眼睛四处看看,并没有发现什么意外情况。待他放好拿到的东西,老人在他的耳边小声说:
“不好,你后边那个卖鸟的不对,不要回头,换个行头快走。”
他迅速拐进一家店铺,自己的同志告诉他,你的尾巴没有甩掉,现在很危险。从店铺出来时,他已换好了西服,摘掉了礼帽,戴上了墨镜。此时,他听到了警车的怪叫,黑狗子们出动了。他,脱险了。但是听说老人却因为他而暴露了。在那险恶的环境里,上下左右的人几经变化,他无从去打探老人的情况。
“大娘,您后来遇到麻烦了?”小章终于可以问那个八年以前的问题了。
老人岂止是遇到了麻烦,她险些送了老命。她进了监狱,让黑狗子打得死去活来。后来,同志们把她救了出来。但是,老人笑着摇了摇头:
“没有,我没有遇到麻烦。”
时间,有时是十分无情的,亲人们相见,它往往不会让他们厮守一阵子,见到了,又要分别了。人们只在一起草草地吃了一顿午饭。是李主任催得紧,他要赶着回去听各路人马的汇报。
分别的时候,最伤心的自然是妞妞。她一会儿抱着娘哭,一会儿抱着奶奶哭,一会儿拉住小老虎哥哥的手就是不放。还有那些曾让妞妞尽情飞飞的她的爷爷、伯伯、叔叔们,为妞妞做花兜兜、梳辫辫的婶子们、大娘们、大姨们,她的小伙伴们,大家都不愿意自己走,但是他们为什么不能留住自己?她大哭,这哭声撕心裂肺。
小老虎哥哥把一只鸡毛毽塞在妞妞的手里。
“好妞妞,不哭,不哭,”可是抱着她的娘分明在哭。最后,还是奶奶说话了:
“妞妞乖,奶奶不是告诉过你,小妞妞会变成一只真的鸟,会飞得高高的,飞得远远的。听奶奶说,今天呀,你已经变成了一只真的鸟,你飞吧,妞妞,飞飞吧!”奶奶在擦眼睛。
吉普车开了。
第四章福窝窝里的乖娃
1958年秋里,狐皮沟的人收拾了一个好年成。
人们正在谋划着成立人民公社。
狐皮沟的农人把种子留够了,牲口料备齐了,公购粮给国家交足了。
节令已是霜降。
一个晌午天,婆姨们忙饭,男人们也没有闲下。
“张叔,你家今年仓窑显小了吧。”师富强在井沿上一碰上张鼎诚,就说开了。张鼎诚笑了。他是狐皮沟的首富,论个成分是富裕中农。狐皮沟没有地主。他家底子厚,两个儿子加上他,都是好庄稼把式,只要陕北逢上好年成,他家的收成,在村里不数一才怪。
这在众人心里是有数的。他收了,也愿意大家伙都收,他是个善良的庄稼人。
“富强啊,你今年收得也不赖,囤也能冒尖了吧?”
这话好听啊,富强像喝了米酒,甜得醉得红了脸。他上有爹娘要养,下边这几年几乎是一年一个添了四张嘴,他和桂花再能干,也是干家少,吃家多。他们这么难,今年也把仓里的囤囤都装上了粮,喜人哩。
“张叔,我家的囤哪能像你家似的冒尖,仓窑里没有空囤,就知足了。”
两个实诚的男人都笑开了心。
“是的,全村的人家里都粮满囤,就连孤寡老人大干妈,社里的小伙子们也给她把粮囤装满了。”
丰收了,大人忙,娃娃也不闲,圆头圆脑的小林昊,在他家的地窖里几进几出,那窖里窖上了红薯、土豆、黄萝卜、白萝卜,林二告诉他,这些个吃食呀,吃到开春都富裕。
“大,茅缸家的地窖看着没有咱家的大,窖的东西比咱家多。
虎娃家的窖可比咱家的大,他家人口也多,吃的多,就要多装。兰兰妹家的地窖我也去看过了。”娃娃们这几天钻地窖,很钻出些瘾头。几乎是成群结伙,钻了这家钻那家。大人们一般不会撵娃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