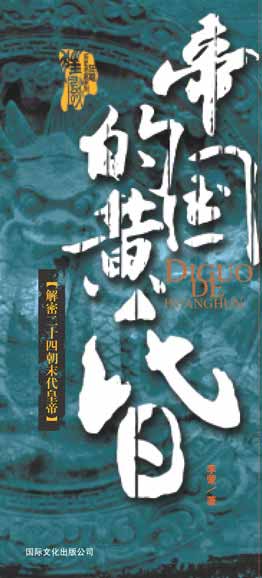厚厚的黄土层 周国春著-第5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林昊是实心实意的。自从离开了江小南,他周围的人可没少给他介绍对象,他见过几个,都只是见上一面就够了。他仍然和小南通着信,他们说彼此的学校,说彼此的同学们。高考恢复了,小南来信让他报考研究生,他拒绝了。也许,人还是要讲究点儿现实的,他不能总在单相思中折磨自己。为了一个女人,他做了太多的牺牲。
他应该成为一个学者,但是他没有在人们为他铺设好的路上迈开自己的脚。到了中学,他忙于教学,教政治课,教历史课,甚至教过外语课,语文课。一位教物理课的老师被开水烫伤了,学校里的教学一时拉不开闩了,他像是一颗万能的钢炮,从容地上了膛,讲起了物理,解了那燃眉之急。教导主任乐了,他问林昊:“川坪中学开设的这些个课程,哪一门,你教不了呢?”林昊认真地想了想,说:
“美术课,我还真是教不了。”是的,他哪里能比的过那个专门人才呢?
“那他妈的是个甚,你小子是个全才哩。我这学校里多少年才遇上你这么个像样的教书匠人。”教导主任一喊叫,更加引起了校长的注意。校长姓钟,中等个头,不胖不瘦的,模样很平常,在人群中晃一晃,没谁能注意上他。因为,能刻出他的那模子,也能刻出成千上万的人,简直是太一般化了。换句话说,他则是一颗没有任何特色的石头子。但是,这石头子却非同一般的,又犟又硬,不把谁能放在眼里,又把那么多的人都揣在怀里。你只要能干,他会把你攥在手心里的。
于是,林昊在钟校长的手心里成了宝。
不过,这钟校长,林昊可是真服了,从里到外都服。钟校长虽说只长他十来岁,但是,首先,他自己是个人才,是五十年代末燕城师范大学化学系的一名高才生,放弃了留在大学任教的优越条件,来到了陕北这座最小的县城,一晃,二十个年头过去了。在这黄土窝里,他娶妻生子,筑起了栖身的小巢,同时,桃李也满天下了。他的教导主任夸林昊,他自己也有眼哩,也长着耳朵,长着腿。林昊一来,他就跑去听过林昊的课。他是个中学的校长,他的教师门门课都教得了,他当然欢喜。他这个人才,搞教育是人才,搞管理,也是人才。其次,他爱才。文革中,省画院的一个通国画的怪才,画起画来能够不吃不睡,犯起糊涂来可以六亲不认,而且不修边幅,只会画画。由于躲武斗,不愿意打派仗消磨大好时光而逃到了川坪的山里。山洞钻过,牲口圈睡过,要上一口,吃上一口,要不上呢,就饿着,人不人,鬼不鬼地混了大半年。他进了山,把这小自己五岁的人请出了山,一口一个兄弟地叫上,安在了他的中学里。这个人档案、工资都在省城,在他这里就成了黑户。
黑户就黑户吧。他的学校他还是说得上话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时,那些个山里人就听他的,如今,贫下中农撤出了学校,他办事不是更容易了?从哪里不能找出几十元钱,给他的画家老弟谭云开上工资呢?再给他发上些个粮票,他还难吗?于是,这谭云在川坪中学是又教书,又画画。画国画的,在这黄土窝窝里,有天,有山,有水,有花鸟树木的,涂去呗。这一涂不要紧,涂出了很多名画,涂出了很大的名声。当然,这所谓的名声,是在这山里人的心上站哩,在这山里人的耳朵眼儿里钻哩。那就行了。钟校长说了,现在还不是时候,时候一到,这谭云是不得了的。他还蔫不叽的从附近一个小煤窑里弄来个现行的反革命分子。那个叫贾番的人,原本是省城一所大学的数学教师,算得上是个人才,课讲得很好,只因为用那张印有副统帅像的报纸糊了抽屉,不知道是哪个小人告了密,于是乎,他一落千丈,到了陕北的大山里。因为会算账,又去了小煤窑。这世上的事又总是有个什么套路的。小煤窑砸死了钟校长学生的父亲,这个学生又是在化学上很有那么点儿灵气的,是钟校长的得意门生。为这学生争取些抚恤金,这关系到孩子能不能把书念下去,于是,钟校长亲自出马,来到了小煤窑,有缘与贾番相逢了。他是以工人的名义把贾番弄到了学校。本来嘛,那副统帅已经自我爆炸了,可是偏偏有人要说,这副统帅,和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不是总在同一幅画面里的吗?你们谁可见过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不在一起的?所以,用来糊抽屉的报纸就不能只是这一个人的像。大千世界,百怪有生存的天地,有啥法儿,只是苦了那些个倒了霉的好人。贾番呢,就只好继续当他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了。钟校长说: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老子看上这贾番,就让他到我这里当个工人,你们谁能说出个甚?”是的,谁也不想说个甚了,打心眼儿里同情贾番的人多了去了。于是,贾番当了川坪中学里有名无实的工人。说他有名无实,是因为他在给川坪中学的高中生们讲数学呢,那书讲得好,懂行的没有不服气的。
是人才,有一个算一个,钟校长攥住了。他也有绝招,要把人攥住,就要给人筑个巢。于是,他为谭云从县文化馆找了个姑娘,这姑娘是跟着父母从省城下放到川坪,三十出头没成家,因为没碰上合适的。她早年也是美院的学生,也会挥毫泼墨,也会涂抹那么两下,这还不算,人还出落得像一轮满月似的,心地善良得羊儿都喜爱。他把这姑娘领到了谭云跟前,这三十大几的人一下就坠入了情网,三下两下筑起了自己的暖巢。贾番是结了婚的人,钟校长就把他的媳妇从陕南的山里调到了陕北的山里。这女人是教小学的,他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先在川坪中学的食堂里安排了她,又深夜去了教育局长的家,那是当年和他一起到川坪县的大学同班同学。
任何时候,图个方便,开一扇后门,还是需要熟人的。寒窗共读,知己知彼,容易吗?处于常情之中,这忙能不帮吗?贾番不是人才难得吗?他的妻子也是一个人才,这调查清楚了。于是,贾番的妻子就成了川坪县里很不错的一名小学老师了。钟校长说:
“贾番,总有一天,我会让你这中学教师也名副其实。”
于是,在钟校长身边,还真聚起了人才。恢复高考了,川坪中学了不得了,考出去的学生,尽是上了名牌大学的。谭云调教出来的几个美术尖子,有两个竟去了国家一流的美术学院。
筑巢的事也该轮上林昊了。可是林昊的眼光似乎是高了点儿。
于是,钟校长找他谈过一次:
“你小子不要眼太高了。”他盯着林昊的眼睛在看,他是研究过人的心理的。林昊没有张口,他能说出个甚?
“你是不是失恋了?”钟校长的神情有几分庄重。
“我就没有谈过恋爱。”
“不对,你恋着人家,爱着人家,你伤过神,我说的对吗?”
“可是人家不爱我。”
“问题就在这里。那你就应该另辟一条路,不能一条路走到黑。”
“我试过,但是不行。”
“因为你总以那第一个姑娘为模式,在那里套啊套,结果呢,套不进你的那个模式,就没有人能称心如意了。于是,你又开始了思念,思念到吃不下睡不香,而这种思念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是一个过来人。我懂得你。”钟校长把眼光移开了,望着窗外。蓝天上,飘过来一朵云,洁白到似乎无人不爱。但是,云毕竟是飘忽不定的,尽管能使你遐想,当然,遐想是美好的,令人神往,然而,它离你太远,用手是摸不到的,用脚是追不上的。年轻人,太看得中幻想,太痴迷那神往之物,他们往往是听不进劝的,愿意遐想,愿意神往,愿意晕头胀脑地去蹈一蹈前辈人的覆辙。当他们从天上掉到地上时,他们才会懂得,什么是实实在在的爱,什么是细水长流的淡淡的然而十分恬静的生活。是的,自己的长辈劝过自己的痴情,这不,自己又需要去劝比自己年轻的人。也许,天上有云彩,人间有遐想,过来人就总会去劝导那些还没有过来的人。从古到今,就是这样的。林昊是心悦诚服的,面前的人把自己看透了。他喃喃地像是在自语:
“也许我不该去爱她?”
“不,你可以去爱,爱总比不爱充实,有所失更有所得。”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从梦中解脱出来,顶着你头上的那一片天,跺跺脚,踏踏实实地为你筑一个巢啊,这巢要支撑起你那颗男人的头颅,这应该是一颗骄傲的然而坚强的、自信的头颅,能支撑起这样一颗头颅的巢,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呢?我想,这个问题要由你自己来解决,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
“我再好好想一想。”
钟校长舒展着自己,他笑了。
林昊想了一晚上。在川坪中学,他有能力,为人尊敬,惹人喜欢。尽管自己是有能力做大学问家的,然而,毕竟是有能力而已,至于做不做得了大学问家,他还没有开始去做。而做一个好的中学老师,他不仅已经在做着,而且做得不坏,继续做下去,会做得很好。况且,这里有与他建立了感情的师生们,这里离他的家他的亲人们是那样的近,这里还有钟校长这样一位良师益友,这样一位让人舒心的顶头上司。离开了这里,情况又会怎样呢?他把握不住。
他一个农民的后代,除了蓝天和土地,就只剩下自己的双肩扛着自己的脑袋,他没有能伸向社会各个层面的触角。那么在这所学校待下去,他能够在最大限度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不就行了吗?
用不着再想其他了。于是他决定在川坪县成家。
就在这个时候,从狐皮沟传来了李北的噩耗。以后,悲痛欲绝的丁胜到学校里来找过他,在他那里住了一夜。两个男人分手时,丁胜说:
“我以为服了刑了,恶梦醒来,会步入一个春天。可是我错了,我的罪过太大了,我承受不起了。”
“你现在不要想那么多,先回到你妈妈的身边去。”林昊安慰他。
“可是,秀秀怎么办?她还生了儿子,我的儿子。从李北到秀秀,这个弯子,我转不过来了。”
“如果你相信我,就暂时不要去想秀秀和这个儿子,一切有我呢。等你度过了难关,振作起来的时候,再去面对他们,行吗?”
“我就这样走了吗?”
“走吧!”两个男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我会回来的。”这是长途汽车跑开来时,丁胜喊出的话。丁胜走了。林昊几乎没有再犹豫,他决定娶秀秀。秀秀聪慧、美丽、能干,和秀秀在一起,一个教书,一个理家,能够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念娃是个乖巧的娃娃,林昊愿意做他的父亲,去疼他,爱他。
现在,他求婚呢。不知为什么,他很有把握地想了:秀秀会同意的。
“昊叔,容我想一想,好吗?”秀秀抬头看着林昊,那眼窝像是两潭秀水,清澈见底,看不到一丝一毫的羞涩。
“好,我等你回话。”林昊说得很干脆,不像是在求爱,倒像是在办一件家常事。
林昊走了。秀秀过了一个月也没有给林昊回话。要说她没有认真去考虑这件事,确实是冤枉了她。她想过不止一遍,但是,总也理不出个头绪,说不清该不该嫁林昊。
这一天,她似乎是漫无目的地在走,走着,走着,竟走到了那钵杜梨树下,是的,就是在这钵树下,丁胜第一次吻了她。自己怎么会走到这里来的?怎么会呢?杜梨树还在,还是这样的粗壮。秀秀的头靠在了树干上,她闭上了眼睛,恍恍惚惚的,像是又一次被人吻得灵魂出壳了。那灵魂仍然在杜梨树的上空盘旋着,盘旋着。
突然,盘旋的灵魂是撞在了杜梨树上,一个声音在耳畔响起: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是胜哥,是的,是胜哥,这是胜哥说过的。秀秀睁开了眼睛,让她的泪水自由自在地流淌了一阵子。是的,自己爱过,也被人家爱过。如今,杜梨树还在,它可以做证。树在,人去,但是,人还在这个世界上,还在。而且,秀秀有他的儿子,有儿子。念娃,他有大,他大会来寻他的,会的。想到这里,秀秀很激动。她不能亏待这个儿子,不能带着他嫁人。昊叔是好人,自己敬重他,可是,这不是爱。和昊叔在一起,她是不会有灵魂出壳的感觉的,不会有。跟了昊叔,他们还会生下娃娃,那娃娃不会是爱的果子,她不会像亲念娃那样去亲她和昊叔的娃娃。昊叔有了自己的娃娃,还会亲念娃吗?不,昊叔不会去亲念娃的。昊叔是同情他们娘儿俩,这不是爱,不是。昊叔在等自己的回话,怎么那么像是集上的人在做买卖,一个愿卖,一个愿买,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