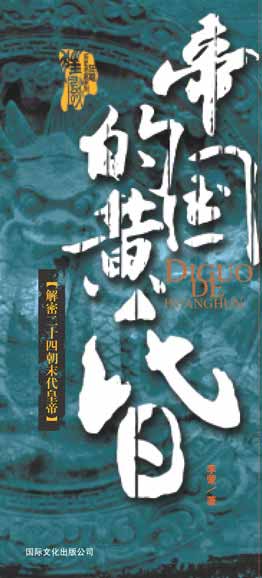厚厚的黄土层 周国春著-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又想儿子了?”他没有作答。
“你在月亮地里走,我知道你有心事。”
“佟哥,我的心苦啊。”
“我知道你苦。”
“我对不起我的儿子,对不起他。”
“我知道,他去了台湾,你没有拦住。”
“不,你不知道。”他说:
“黑毛头,他是我的亲孙子。”这话说出来,他倒平静了许多。
“怎么会呢?”
“他是我们李家的根,是将门之后,这是真的。”第
三
章妞
妞
飞
飞
1955年,小满。
一辆吉普车沿一条黄土路向北方清泉县柴峰口村行驶。
车里一个中年男人,一路谈笑风声。他兴奋起来,右脸颊上的那道疤痕会泛起红色。同车两个年轻人
刘秘书、章科长和他一
起海阔天空。时不时,司机老王也搭腔。
“李主任,这次我们下来,从南到北,跑的都是城市,看工厂,看手工业合作社,开座谈会,听汇报,整材料。今天拐到这个山沟里,还真是别有一番风味。”章科长显然很有兴致。是的,多少天来辛苦啊。他们是一支特殊的工作队,虽然不能有昔日武工队的惊险色彩,更不会有铁道游击队传奇的神韵。但是,他们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为那新的国家是可以呼风唤雨,力挽狂澜的。他们人不多,差一个不到二十,分组行动,分片包干。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从三个人的小作坊干起,直到几百人上千人的厂子,按照调查提纲所开列的几十个项目,在那里下马看花,顺藤摸瓜,收集情况,排查问题。涉及到的行业近百种,去过了几百家大大小小的企业。
“算起来,我们这帮人走了也有近二十个省市了。”刘秘书也来了兴趣。“不过,我们可不是总看城市啊,前一次出去,我们不是还去看了北方大田里的烟草,钻了棉花地,光那个麻,就看了亚麻、剑麻、大麻、黄麻。”他还想说,只要跟上李主任,不管去哪个口子把关,他会干到通宵达旦,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辛苦万分的。近一两年来,光是工作笔记,小刘居然写满了五十六本。他的一些同行们曾经和他打趣说,你跟上了一个大工作狂,干不了几年,你也会因为他而小有名气的。当然,后边这些话,他是不会说出来了。
“拐进这山沟里,你们想着松松套?”说着,老王先笑了。是的,干活的人愿意把自己比作牲口,累急了,常喊叫着要松松套,真让他们松了套,他们会闲出病痛,呲牙咧嘴发牢骚。
“不过,这几年大部分时间,我们是在城市里过的。”小章是不愿意让嘴闲着的。只要有说的机会,他是不会错过的。因为他的表现欲望极盛。
“是啊,这几年咱们鸟枪换炮,住进了城,才转工厂,忙城市。
不熟悉的要去熟悉,不懂不会的要去学习。”李炳彪如今在国家机关负责经济工作。进城才几年嘛,乍一回到农村,就有了鱼儿回到水里的感觉。
“不知为什么,我不喜欢城市。”刘秘书是从东北的深山老林里钻出来的,人称山里通。既然不是个城市通,可不,就不喜欢城市。
“不能不喜欢呀。城市可以把握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哩,那里有钢,有铁,有工业。没有城市,只有小农业,我们的国家就像是建在一片沙滩上,那是绝对不行的。没有根,是不会强大的。你这个山里通,忘了我们才去过的东三省,那可是我们国家的重工业基地,那也是你的家乡呀。”李主任从前面座位上扭过脸,冲着后面两个年轻人在笑。
“可是,城市里也不能没有涮羊肉的,焊洋铁壶的,捏个面人,做个工艺品的人。”老王说出这话,心里沉甸甸的。他想起了这次见到的几个老匠人,他们有的面临失业,有的干脆失业了。一个南方的老艺人,搞的是铁画工艺品。那老哥一脸的褶子,苦着脸说,我们几辈人的手艺,传到我这儿,走到今天,简直就做也做不下去了。他咳得厉害,吐出来的不是痰,那是血,鲜红鲜红的,让人不忍去看。
“是啊,人们离不开那些人。”小章对城市里的小手工业者们更是情厚一层。他曾是个以银行职员的职业为掩护的党的地下交通员。为迎接大部队进城,他在“狗不理包子铺”与来人接头,由“泥人姜”把情报巧妙地做进铁拐李的葫芦里,做进弥勒佛的腹中。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浪头,是不是太大了,太猛了?”
李主任在思考缠绕了他许久的这个问题。他没有了刚刚还涌动的兴致。
章科长的话,再没有谁想说下去了。
车上的人们沉默了。
然而,人和人聚在一起,即就是都沉默了,也只能是短暂的,总有人又会打破沉默的。
“还是说一说你的女儿吧。李主任,接上那小家伙,我们回去的路要变短的,我们也好放松放松了。”章可言想起了此行的一大乐事。
“那个妞妞吗?说起她,我比咱主任要熟悉多了。”提起孩子,刘秘书神气起来。她今年五岁,我见过她五次,这回应该是第六次,几乎一年一次。上个月才刚刚来过的,没想到这次竟是来接她回家的。
“是的,我的女儿,她两岁上我才见第一次,今天是第二回来。”李主任的脑海面浮出了两岁的女儿。
她梳着两个羊角辫,圆圆的小脸,被那山野里的风拈来的土涂得黝黑发亮。这黑里又透着红晕,红得可爱。她好像只会跑,和自己东躲西藏,使你无法看清她的小鼻子小眼。她一声声唤自己叔叔,还扬起小胳膊,喊着:“妞妞,飞飞,妞妞,要飞飞。”原来,这村里的男人们都把他的女儿李北叫做妞妞,只要妞妞按辈份唤他们叔叔、伯伯或是爷爷,再加上一句,妞妞,飞飞,妞妞,要飞飞,人们就会把她高高地举过头顶。一次,她嫌不够,两次,她不过瘾,直到别人累了,她笑出了眼泪,笑得像一颗裂开了的红石榴,才作罢了。自己也被女儿叫做叔叔了,妞妞飞飞了,还骑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叔叔,高高的,飞飞了,你真好!”她夸自己,嗲声嗲气,这声音钻进人的耳朵眼儿里,能痒痒到心上,生出麻酥酥的感觉。女儿的声音,他无论什么时候想起来,都会幸福地闭上眼睛。
“不对,那是爸爸,不是叔叔。”旁人在告诉她。
她搂着自己的脖子,眯起眼睛打量着自己,抿住嘴,在想。只有这时,他这个当爸爸的才看清楚了女儿,柳叶眉,小嘴巴,是个满秀气的小家伙。
“不是,不是,这不是爸爸。”她从自己的怀里跳下地,爬上了炕,又爬上了桌,用手指着墙上的一个镜框:两个军人,女军人温文秀丽,笑咪咪地看着注视着相片的人们;男军人清瘦而刚毅,目视前方。
女儿回头笑着:“这是爸爸,还有妈妈。”
自己是动了真情,抱她在怀里,亲着她的脸蛋儿:“我是你的爸爸,我是你的亲爸爸呀。北北,我的小女儿,叫我一声爸爸呀。”
女儿好像并没有听见他说什么,确切地说,是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女儿摸着他的右脸颊,用小嘴轻轻吹着那伤疤:“叔叔,你疼不?”
“不,爸爸不疼。”他捏住了女儿的小手指头,放在自己的嘴唇上。女儿的手指像人的唇一样鲜嫩,一样柔软。
“叔叔,你不怕疼,就是乖孩子。”女儿亲了亲他的额。
他,语塞了,眼睛里似乎有蚂蚁在爬。他,一个男人家的心,竟被搅得酸溜溜的。
离开的时候,女儿没有向这位叔叔道别,她正在油菜地里捉一只花蝴蝶,她管不了,似乎也不想管这位叔叔是去还是留。在她的世界里,这位叔叔是无关大局的。
这样的爸爸对女儿是有愧的。
“她出生的时候,你在哪儿呢?”老王的问话似乎并不全是出于好奇。
“我刚刚从新疆回来,又和慰问团去了朝鲜,去慰问志愿军。”
是的,他是党的人,身不由己,在他来说,是在情理之中的。这不到六年的时间里,他不仅在新疆过问那素有“东方民族博览会”之称的十四个民族的事务,过问人民的疾苦,和人们一起处理着那里的电力的问题、交通的问题、生产的问题、物资的问题,甚至外交的问题。他在收集整理资料,在感慨那里的地大物博,在感慨明天,那里将是重要的工业基地。当他还不能从感慨中解脱时,又奉命去了朝鲜。三千里锦绣江山,战火硝烟,志愿军战士,阿妈妮,他还来不及理清那些情感和文理的思绪,又回国置身于大西北地区的“三反”、“五反”运动。以后,更是不容推辞地去演国家经济的重头戏。是的,女儿出生,他在朝鲜,回国了,才知道自己当了爸爸。他欣喜,他激动,他也快活。但是,他没有到女儿的出生地去。是不想去看一看吗?哪能呢!他是有血有肉的常人。那么为什么不马上去看呢?为什么直到两年以后才看了第一次呢?还有,这些年,他为什么不经常去看一看女儿呢?只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是没有那么多为什么的。
“您当时把她扔到这么个荒沟里,是够狠心的。”章可言话说得有些结结巴巴的。
“这才不是一个荒沟呢,有山有水,厚厚的黄土,各色的庄稼,你们看嘛。”李主任指点着。
人们看着远处三面环山的坪坝。正北面那峻峭的山峰,就是有名的柴峰。东西两座山,像是两捆青青的柴草。坪坝上,一片片麦地,黄灿灿的透着青色。弯弯的渠水从田间穿过,裹卷着一串又一串银白色的水花,在太阳底下,晶莹透亮,像银链环绕着麦田。路边,地头,院落,有挺头直立的杨树,有垂着绿发的柔柳,有青嫩嫩的刺槐,有伸展着墨绿枝叶的榆树。远远的,已经可以看到错落有序的房舍了,青砖房,黄黄的土胚房,瓦顶子,茅草顶子。真是满有生气的一方天地。
“这是您为女儿选择的地方?”章可言还有问题。
“哪里容得我去选择。人这一辈子,几多事能由自己选择?”李主任摇了摇头,无奈地笑了。当初,北平和平解放在即,他的老首长在办公室里问他:
“你今年也过了而立之年了吧?”他点了点头。
“你该成个家了。”老首长语重心长。
“不急。”他说的是实话。
“我这里有一个现成的,在野战医院里搞行政工作。原来是地方游击队的队长,会骑马,能使双枪,人长得也漂亮,二十多岁,年龄合适。怎么样,我安排你们见一见。”
他在想,女方会不会骑马,使不使得了双枪,这同能不能做人家的老婆有什么相干。自己大小是个知识分子。早年家虽穷,但是爹兄弟三个,就他这么一条根。爹扛活,娘给有钱人做老妈子,大爷给东家赶大车,叔叔下煤窑,四个大人供他念书,念到中学上,差三天毕业,被学校开除,因为他搞学运。从此,他一门心思扑在了革命上,去了延安。给他找老婆似乎要问一问对不对得上他的舞文弄墨的情调。
“先见一见人。”老首长快刀斩乱麻。
于是,当天晚上,还是在首长的办公室里,那实际上是河北农村一间民房。他坐在一盏煤油灯的旁边,那位叫姚慧敏的女同志他记不清坐在哪里了,只知道自己是在灯影里,那个人坐的地方背着光,他看不清人家,可是人家把他看得一清二楚。从声音上,他很喜欢,听上去清脆而甜蜜。他们并没有谈多久,因为有个会在等他出席。第二天早上,他们不期而遇,在井台上,慧敏正摇辘轳,他迎上去帮忙。近在咫尺,他看清了:弯弯的柳叶眉的下面,是一双水灵灵的大眼,滴溜儿,滴溜儿,冲他在转,嘴唇很薄,笑起来,还有深深的酒窝。真美,他的心在说。
“怎么样,看上看不上?”首长的问话也是在那一天的早上。
“先要问一问人家。”
“不用问了。你那次负伤,人家就认识你了,昨晚上把你看得更透彻了。人家没得意见。”
他想,见一面怎么行,总还得再接触接触,了解了解吧。所以他只是瞪大了眼睛,没说话。
“怎么,还不那么痛快?我手头没有再多的了,这个就满好。
要是再多几个嘛,你是可以再挑选挑选的。”不知道为什么,他想笑,这是在找老婆,又不是在领军装,你发我领。他看了看老首长,竟是那么样的认真,还满怀着期待,忍不住笑出了声。记不清自己说了点什么,只记得他的老首长开怀大笑,直笑得把刚喝进去的一口水喷了出来。
“你是答应了?好吧,这件好事做成了。”待老首长喘过气儿来,按照自己的理解,说出了这么一堆话。他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