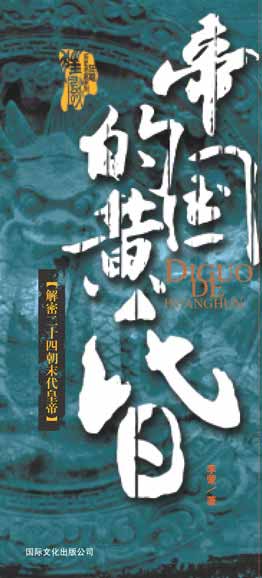厚厚的黄土层 周国春著-第4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咋,公家人要把丁胜带走?”寻老六两口子愕然不知所措。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秀秀妈才对梁支书说:
“这事我和秀秀她大的都晓得,都依了的。”
“你说甚?”梁支书一拍大腿:
“你们早干甚了?为什么不对人家公家人说清楚?你们害了人家娃哩。你们是自愿的,人家娃咋能是强奸哩嘛?亏你们先人哩!”“说是我们知道,我们和秀秀都丢人哩,说是丁胜强迫的,秀秀好活脸面,男人家的面子大哩。谁知道,嘿,他妈妈的,谁知道是这样嘛!”寻老六的鼻涕眼泪都出来了。
案子结得很快,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该走的程序都走到了。一纸判决书下来,强奸罪,判了丁胜五年徒刑。前后二十天,丁胜就从县公安局看守所被押往茶山监狱服刑。
秀秀连惊带吓,彻底垮了。她不说话,不吃不喝,一病不起,愁坏了寻老六和婆姨。他们翻山越岭,请来麻湖湾的老中医为秀秀把脉。此时的秀秀已是皮包骨头,奄奄一息。脉把完,老中医对秀秀的父母说:
“你娃有喜了,身子骨太虚弱,又受了惊吓。喝些汤药调理吧。”
送走了那郎中,秀秀她妈哭天抹泪地对秀秀说:
“这咋好,妈和你大害丁胜蹲了大狱,你又害(怀)上了他的娃娃,日后咋好,咋了哩。”
“妈,莫哭,我好好吃药,我要胜哥的娃,我要哩。胜哥坐五年牢,我等他,等他。”倔强的女子竟然坐了起来。她有了活下去的依盼。她吃着药,病一天天好起来,人也胖了,肚子也日复一日地隆了起来。山里人是很善良的。后庄的婆姨们这个拿些鸡蛋,那个拿来只母鸡。人们爱怜秀秀,喜欢丁胜。人们说,不偷人不抢人,算不得坏人。至于情哥哥和情妹妹的风流韵事,并不坏一个人的德行。也许,中国人的包办婚姻就是风流韵事不衰不败的肥田沃土。怪不得陕北的酸曲那么多,老辈子人唱,小辈子人唱,唱得甜唱得美唱得酸,那是张开翅膀的爱恋。信天游那无遮无挡的情曲,甜哩;青年男女在云端里彼此相望,壮实的后生,俊俏的女子,美哩;情哥哥,情妹妹,睡梦里几回回叙衷肠,搂定了就不能再撒手,两眼睁开一场空,酸哩。人都说,好事难成。这话不假哩。几多多兰兰茅缸啊,难圆夫妻梦哩。所以呀,在山里人看来,秀秀和丁胜一搭里耍,算个甚,就是公家人要认真哩。丁胜是个民办教师,半个公家人,要不,甚事不能有。在山里人的眼窝窝里,山丹丹花花仍然是红红的,杜梨树叶叶仍然是绿绿的,好看哩。秀秀恋着丁胜,丁胜心里有秀秀,那么,秀秀该等他,五年的时间不久长。秀秀还年轻,又有了娃娃,她等得了。
秀秀苦啊,李北更苦。秀秀还有腹中的一条小生命作为精神的寄托,她有爱的果子。李北则两手空空。几十天来一场大变故,她把丁胜送进了大牢。人在爱极了眼的时候会恨的,恨极了眼之后又会悲的。李北变了?不,李北还是李北。她拼命工作。孟书记说:
“李北,为一个负心的汉子不值得伤害自己,忘了他。你要是装喜欢军人,我上县武部给你去找。要是喜欢干部,公社、县上的,你挑,看中了告诉我老孟,我给你操持。我就不信,你娃找不到一个比丁胜强的。”
李北摇一摇头走开了。
梁支书见过几次孟书记,他不在那个人面前提丁胜,也不敢再提这民办教师的事。孟书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不说,我也就不问呗。世界上有许多的事,本来就没有什么对了错了之说。丁胜的事,是人啊弄遭了的事。定了他的罪,还没有人能说出个甚,一切又都是罪该如此。他一个共产党的公社书记是不会再对这件事情说长道短的,只觉着小伙子是个没人能救得了的倒霉蛋。事情弄成这样,他不太好受。要说心里难过,这梁支书是难过哩。他辛辛苦苦把丁胜扶起,在一夜之间又带人把丁胜放倒。
只是苦了丁胜了。他糊里糊涂地在一夜之间成了阶下囚。在看守所里,他要低头认罪,他不该那样占有秀秀。但是说他是强奸犯,他不能接受。他和秀秀之间没有强迫,没有暴虐。但是他又不得不服法,去了监狱,穿着半边粉红半边白色的囚服在大田里耕作,接受政府的改造。为什么会是这样?还是少问的好。安安稳稳地服法吧,毕竟只有五年。在那个年代,有多少人的十年、二十年生
以致更长时间的囹圄活,是能问为什么的吗?问得清楚吗?然而有一点儿,丁胜是清楚的,他,是黑五类子弟,在陕北没有根基,与权势者不沾亲也不带故。爱他的人们都无职无权,帮不了他。也许这只是问题的一半。那另一半呢?他丁胜陷入了爱的泥沼,既然陷进去了,就只能越陷越深了。
第二十二章狱中花絮
家,丁胜没有了。狐皮沟后庄的秀秀,毕竟不是他的合法妻子。那些逮捕书、判决书等一切要下达给家属的法律文书全部给了梁支书。
他上囚车去监狱的那一早,梁支书和李北为他送行。李北眼里噙着泪。丁胜不敢正视他的北北,那目光惨淡,却刺眼,像强烈的电光,仿佛能刺透他的五脏六肺。据说,梁支书和李北能在他走前见上他一面,是因为李北央了孟书记,找到了县公安局长。
“娃,好好改造,好好服法。到了大牢里,比不得这山里。嘴要软哩,要猫起腰为人哩。刑满回来了,你还是我狐皮沟的社员。”
梁支书的声音沙哑着。他一个男人,在人前,是不兴掉泪的。
李北哭了。在狂风暴雨之后,她的铁石心肠就被儿女之情吻得软成了一摊血肉,她十分理智地痛哭了一场。她不能失去丁胜,不能。丁胜,他还能回到自己的身边吗?顾不得这些了。在他走之前,要见一见他,见一见他,这个念头强烈到不能作罢,以至于半夜三更的,她敲响了孟书记的窑门。孟书记失眠,一夜睡不了三个钟头。这一夜他刚刚幸福地迷糊上了,又被无情的声响震灵性了。
怕是有了什么急事?才下过雨,是沟里的几个坝出了事?于情急之中,他光着膀子,穿一个大裤头开了窑门。当他看清李北时,尴尬得进退两难。姑娘红肿的眼睛可怜巴巴地看着自己。孟书记急忙把李北让进了窑,披上衬衣关切地问:
“咋了?谁欺负了你?”
“孟书记,丁胜,丁胜,他,”姑娘大声哭了起来。
“丁胜判完了,你,咋的了?”
“我想见他,想见见他。”孟书记先是一愣,回过神来明白了八九分了。
“你还挂念他?”
“我想他。”李北抽泣着,她是那样的委屈。
“你呀,”孟书记不说了,他摇了摇头。虽然他也年轻过,但是有许多事他没有经历过,尤其是青年男女死去活来的爱,刻骨铭心的恨,还有负心的汉汉一走了之,多情的女子却无怨无悔。李北是大城市的女子,她的爱,也许让人更难琢磨。最后,他轻轻地说:
“我帮你见一见他,再叫上梁支书。”孟书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此时在丁胜的面前,她的泪由着性子流淌。她无法控制自己。
二十天的时间,丁胜老了许多。虽然自己有几个月没有见他了,但是,他老了这许多,是在这二十天里。李北坚信。他眼圈发黑,脸色苍白,面孔肿胀着,胡子头发都长了,硬茬茬的毛发一根一根都在扎她北北的心。
“我服法,好好改造。”五分钟里丁胜只说了这一句话。
“我会去看你的。”李北也只说了这一句话。
只有在这时,丁胜才抬起头来看了一眼李北,心一紧。她瘦了,脸上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雾,两只眼睛痴呆呆的,眼珠被淡红色的血丝缠绕着,眼泡肿得变了形。她是刚刚回来的?她被自己害惨了,还要来为自己送行?自己已经永远地失去了她,自己从灵魂到肉体也永远不再是她的了,不再是了。她恨自己吗?用不着再恨了,已经遭了报应了。不,天大的报应也解不得她的恨。可是,我是爱她的,爱她的,不是为了这份爱他低下了头。还有那个秀秀,他不该这样要了秀秀的贞洁。两个女人都被他所害,罪过啊!
他什么也不去想了,想谁也帮不了谁,爱谁都只会爱出灾祸。他咬紧了牙根。此时,他麻木得像一截疙疙瘩瘩的老榆树根,就是用火来烧,也见不着火苗,只能慢慢幻化为灰烬。
与丁胜同车去茶山监狱的还有一个人,叫田留,黑黑壮壮,高高大大的,一脸的本份,说句话都脸红,却放火烧了设在他们村的县蚕种场。要说作案的动机也简单极了,因为县蚕种场建窑占了他家的自留地,那自留地在山洼的阳面,队上给他倒了一块背洼洼里的地。自留地是农民的命,他全部的心思,都扑在了自留地里。在那里,能结出拳头大小的洋芋蛋蛋(土豆),尺把长的玉米棒棒,洗脸盆大小的老南瓜,还有那豆角、洋柿子(西红柿)、黄瓜、茄子、白菜、萝卜,红的、黄的、紫的、绿的、白的,那是农民织出的锦缎。自留地里的庄稼和蔬菜,那是山里人的金娃娃哩,都是用最上等的粪肥奶出来的,用十二分的精心从颗粒侍候到大的。谁想,一张纸头飘下来,田留精心用茅粪奶肥了的自留地换了块照不见日头的瘦土。一年下来,洋芋蛋蛋比羊粪蛋蛋大不了多少,玉米棒棒没有人的中指长,一切带颜色的菜都是灰暗的。这一年,大田里的庄稼也旱结实了,没什么收成。婆姨急了眼,娃娃老娘都要吃哩。她摔摔打打骂田留,骂得星星都躲了,还在不住嘴地骂:
“你个窝囊鬼,是个连块自留地也护不住的死狗,我跟了你倒了八辈子的霉。这日子没法过了。”她又哭又闹。田留本来就窝一肚子的火,那火自打换了地的那一天就窝上了。他又不爱说,那火不往外烧,作践得自己恨不得死一回。他这个人,又是最听不得娘们哭的,娘们一哭,像是小狼的爪子挠他的心。他一肚子的火再也窝不住了,大叫着冲出了窑门。婆姨傻了眼,她从未见过自己的男人像疯子一样地傻跑,她麻利地追着男人的屁股撵,死活也撵不上。田留一把火将蚕种场烧了个惨,那火光映红了漆黑的天幕。以后的事田留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婆姨捶着他的背号哭着:
“这咋活啊,你把我也烧了吧!”田留一直站在山墚上,望着那火烧起,望着人们将火扑灭,望着启明星升起,没挪地方。人们向他围过来,他不动。公安局来人带他走,他跟上走了,才知道这事做大了。把他宣判了,他才像是刚刚做了梦,现在醒来了。
“我这十年大牢一蹲,可怜了窑里的婆姨和三个碎娃,那小的才出了月子,大的才五岁。炕上还有个七十岁的老娘,她瘫在炕上。等我熬出来,还不知能不能再见到我的老娘。”田留淌下了泪。
“可你为甚要烧县蚕种场?那是国家的财产,就不怕犯法?”丁胜问他。
“说的是呢,人急红了眼,干了瞎事,后来也怕哩,那得用多少钱才能赔哩,怕是得做牛做马,几辈子人的力气都搭上,也赔不起国家的那蚕种场。我可没有想到要我去蹲大牢。我又没偷又没抢又没杀人。”田留不应该委屈,按他的理,不让他下苦力赔国家的蚕种场,只去蹲上十年大牢,岂不是便宜了他!但不是这么个事呀。难道只有偷只有抢只有杀人才犯法?中国的法,不能说没有。
可是在山里人的心里,它是十分模糊的。一旦被绳之以法了,这绳头是怎么打的结,打的什么结?公家人说山里人犯了罪,犯的是哪一条哪一款的罪?要服什么样的刑?量起刑来,别说山里人不懂,他丁胜一个上过高中的人,又能懂得多少呢?他与秀秀做了不合法的夫妻,就犯了强奸罪。强奸这两个字,在他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结结巴巴地看过冯德英写的小说《苦菜花》,曾经读不懂这两个字,查了字典,看了那解释,对所谓的暴力、性交,还是稀里糊涂的。他追着老师问过,那么有学问的老师却支支吾吾似乎无法加以解释,后来是这样说的:
“不要问了吧,你长大了,会懂的。”
他又去问爷爷,爷爷用十分鄙夷的眼光扫着墙角,对孙子说:
“男人欺负女人,很下流,很无耻。爷爷最恨这样的男人。你长大了,会懂的,现在,你还太小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阅历像他的年龄,一年一年的长,一年一年的大,他对这两个字由似懂非懂,渐渐的,一天比一天明白了起来。尤其是来到了农村,听到山里人的打情骂俏,看到羊儿踩圈,叫驴发情,牛儿交配,他才算彻底弄懂了善良的人们不愿意说道的这两个字。强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