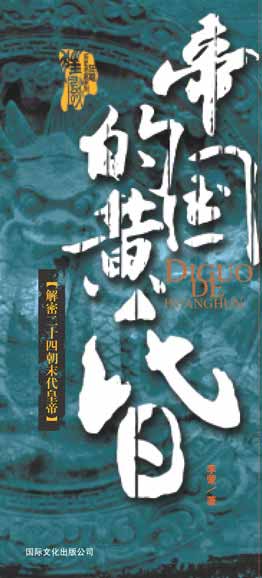厚厚的黄土层 周国春著-第3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她累极了,终于偎着那老人睡去。她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猫,蜷曲着身子,缩在一个暖窝窝里,正在听林昊讲《悲惨世界》。第
十
六少女的太阳
露出云端
章了
秋去冬来了。
俗话说,一九二九不出手。天冷,山里人手抄起,捅在棉袄的袖子里。开始征兵了,狐皮沟验上了三个兵,前庄两个学生,徐末末和黄源源,后庄寻老六的大儿子寻根柱。寻老六,就是狼毛的那个狗剩。狼毛到阴间与男人团聚,已走了三年了。
徐末末和黄源源要走了。他们这批兵去新疆。在那个年头,当兵,去军营,是知识青年们梦寐以求的。末末和源源拿到入伍通知书是心安理得的。这兵是靠自己当上的。
吴欢欢和江小南都赶回来送行。他们见面后的第一句话竟是:
“哎呀,你的头上长了虱子!”李北对着江小南惊叫了起来。
“还有虮子。”吴欢欢比李北更细致,她叫起来让人感到有些毛骨悚然。
“我说我怎么这么痒痒。”也许,忙起来,兴奋起来,紧张起来,人身体的微妙变化就不算啥了。江小南一天最多走过一百二十里山路,路经水利建设工地时,还拉上几车土。山里的干部,官大官小,都是这样干的。她迎着纷飞的大雪赶过山路,伸出棉衣袖子里那双僵冷得没有知觉的手,在山里人的灶火窝烤着,细细体会着什么叫做温暖。她写第一篇通讯报导稿件时,在农村跑了一个星期,熬了两个晚上,兴奋地将稿子交到了岳皖的手里。岳皖是山东大学中文系的高才生,李希凡和蓝翎他都见过。那两个人当年敢于向反动学术权威俞平伯挑战,是毛主席大加赞赏的很有生气的“小人物”,这是红卫兵们十分崇拜的。岳皖还告诉小南,有一个叫孙达人的,也是他们山大的学生,他反对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论”,写出了很有见解的论文,毛主席看了他的文章,给予了肯定,说地主阶级对农民哪里有什么让步,只有反攻倒算。山东大学,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小南在崇拜山大的才子李希凡、蓝翎、孙达人的同时,也崇拜出自山大的岳皖。薛主任和高主任都夸岳皖是人才,而岳皖则说她一点红是错不了的。自己的稿子他会喜欢的。小南一阵激动,长夜难眠。第二天一早,她起床后就去打扫政工组的办公室,倒纸篓时,一低头,看到了一卷稿纸,那卷纸没有被揉搓,没有被撕扯。她把这卷纸从纸篓里抓出来,原来竟是她昨天才交的稿子。是岳皖扔到纸篓里去的?她似乎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她被大大伤害了,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不管不顾地夺眶而出,哭着哭着竟哭出了声来。
“怎么了?”一脸倦容的岳皖出现在她的面前。
小南不理他,继续哭。岳皖看到了她手里的稿件。
“呦,我知道了,哭你的文章呀!也不看看你写的是些什么东西,狗屁不通的,害得我不得不重写,直熬到下半夜。我还没哭呢,你倒先哭了。好了好了,擦擦眼泪算了。”他连挖苦带乖哄,小南却越哭越凶。
“你干嘛欺负我们一点红?”郝平走过来,拿过小南手里的文章念道:
“工地上的人把小车拉得飞快,飞啊飞啊飞,连云儿都停下了步子,赞叹小车比它飞得快。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他忽然忍俊不禁,把脸笑得通红,直笑出泪来。小南擦了擦泪,仰起了脸,“笑什么笑!”岳皖也笑起来。最后,郝平终于止住了笑,很认真地说:
“一点红啊一点红,你很会幻想嘛。不过,我们的报导,必须是拉土的车子在地下跑,实打实的一车是一车,拉得多还是少,快还是慢,说清楚了就行了。岳皖呀岳皖,你也不对,怎么能这样发落人家的稿子,要耐心地帮助。”没有等岳皖说话,小南已经气鼓鼓地跑掉了。她把稿子又送给了老马和慕生林,那是两个笔杆子。
他们两个人细心地看了并修改了那稿子。二十页的稿子,经过修改后,有用的东西剩下两页半。于是,小南开始了写写和改改的虚心学习。县城十点钟以后停电,她就点上煤油灯干。老马说不行,她重写;慕生林提了修改意见,她再改;岳皖皱眉头,她撤回来再写。一遍不行,再来一遍。文字朴实简单几乎到了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渴了要喝,饿了要吃的份儿上。岳皖终于说话了:
“不简单,这文字功夫比常是春都强了。”陈鸿则说:“一点红是有潜力的,写出的东西生动、活泼,发展下去,将不会亚于你岳皖的。”郝平也服了姑娘的倔强和勤奋。小南跨出了一大步。她写的东西,县广播站播出了,地区小报也刊出了。她没有时间清洗自己,也没有条件和长虱子的人隔离。现在人们说她长虱子了,连吓带惊,令她浑身瘙痒,竟一刻也不能容忍了。她忘记了什么叫克制,她十分不得体地扭动着。李北一把把她拽进了女生窑,吴欢欢烧了一大锅开水。清洗过的江小南,头上还是痒得难受。
“如果你不反对,我给你把头发剃短吧。”高小龙的建议,语出惊人。当时的女生几乎都是一个打扮,头发从脑瓜顶往后,分一条中缝,编两条短辫儿,辫梢搭拉在肩膀上。这好处很多,干起活来头发不会耷拉到眼睛上,冬天好戴帽子,夏天,利利索索的,凉快。头发长了,只要自己把辫梢剪短就行了。另外,两条短辫在微风中招摇着,既潇洒,又有女人味道。心灵手巧的女生,把头发的中缝分直,小辫子编上四股的五股的甚至七股的花样。当然,一些懒家伙,则把那条中缝分得歪七扭八,小辫子编上三股还毛毛草草。同样打扮,并不掩饰女人各自的特色。小辫子是不能没有的。
三个女生都愣了一下,其他几个男生也把眼睛瞪圆了。“好吧。”出人意料的是,小南同意了。
“你再想一想。”吴欢欢在劝。
“不想了。”小南很坚定。于是,高小龙拿出了剃头的工具,下了手。一缕又一缕乌黑的秀发飘落了,一个漂亮的男孩子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不能再短了。”李北终于又叫了起来。吴欢欢则是用一副伤心的模样对着小南。徐末末则笑了起来:
“又多了一个男子汉。”
“确实的,反正江小南穿的也是四个兜的蓝制服,还真的像是一个男人哩。”丁胜同意徐末末的见解。
“不过,江小南当男孩子还是蛮漂亮嘛!”黄源源像是在欣赏一件艺术珍品,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看。
“你不说是我的理发技术高,却说是人长得好,岂不是亏了我这理发师了?”高小龙乐呵呵的。当林昊、茅缸、大宝、二宝和兰兰这一帮人赶过来串门时,见了江小南,竟笑得扭成几团。
“笑什么,笑什么,哪儿不好看?这样难道不精神吗?”小南歪着头喊。
“江小南,你也不想想,我们山里人,生虱子的多了,都像你似的,女人们都剪短了头发,这,这,这怎么行。男不男女不女的。”林昊嘴上说着,眼睛却一刻也没有离开小南的脸。她黑了,但是,像大山里的一棵成熟了的谷子,更加饱满,更加秀美,更加迷人。
“高小龙你怎么搞的,把女娃娃给剪成这副模样。”梁支书在人们不知不觉中走进了学生们的院子,粗脖子大嗓门地吼着,接着又一个劲地说:
“不好不好不好不好。是的,女人就是女人嘛,山里人是懂得欣赏女人的。”只有程果平,看到江小南,先是一怔,又一惊,是她吗?像春风荡漾起湖中的涟漪,眉毛、眼睛和嘴都笑得弯起来。
是她来到了这里?不,他难过地闭上了眼睛。多么像自己的妻子,那个跑起来像羚羊一样可爱的女人。她就是这样的,头发剪得短短的,精干中透着挠人的魅力。
“怎么不好。你们没有见过女运动员吗?一个个不都是这样吗?
她们不可爱吗?”程果平这样说。
“不过她的头发比运动员还要短。”吴欢欢很不满意。
“长长就好了。”程果平像一个善解人意的老大哥,他赞许地向小南点着头。这是一个把自己投身的事业看作太阳的女子。她的太阳已经露出了云端。为了她的太阳,她只会往前走,欲罢是不能的。这一点,也太像自己的妻子,太像了。他仿佛又听见妻子在说,果平,我不愿意离开我的研究课题,它是迷人的,我离不开它。
七个人在一起团聚了一天,不得不各奔东西了。
像一场梦,醒来后,只剩下李北、丁胜和高小龙了。
到了三九四九冰上走的时候,高小龙也走了。一个赌输了的卡车司机,酒后开车撞塌了一堵墙,而高小龙的爸爸正靠着那堵墙在给人修鞋。爸爸的双腿被锯掉了。小龙在冰上走,要去踏破坚冰,呼唤春天。
已经是五九、六九了,该是到河边去看垂柳的日子了。那一天的晚上,丁胜吃完饭以后,李北没有急着去刷锅洗碗,而是久久地注视着他。这窑里是他们两个人的世界。你不要走,不要走,再陪一陪我,陪一陪我。姑娘用眼神在乞求着。丁胜也根本没有要走的意思。他直立的身躯微微向姑娘弯下,一步一步向前移动着自己的步子。从那个神话似的月夜里走出,早桃花含苞欲放,已有三五回了吧。他几回回梦见那个月夜,自己在用荷叶遮盖那嫩如鲜藕的玉体。然而,当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不敢正视那个梦里搂定的人,远远地躲着她。自己还不是一个坚强的男人,还没有长出有力的臂膀,还不能去顶风抗暴。他还没有能力去耕耘自己的家园。他,还稚嫩,还软弱,还单薄。然而,是庄稼,就会长出饱满的籽粒,是一棵树,终有成材之日。上苍用黄风在雕琢他,黄土地用母亲的乳汁在哺育他,山里人用纯朴和憨厚在酿造他。他在长大,而且十分欣喜地发现,姑娘也在一天天长大。如今站在这里的,已经不是一个羞怯而娇小的女孩,而是一个婷婷玉立的少女。
李北向他靠过来,靠过来。多少个不眠之夜,她在为那个勇敢的年轻人流泪。丁胜不是亚当,自己并非夏娃。但是,一个少女却在自己喜欢、熟悉的少男面前做了一回夏娃。于是,她愿意做那个人的一根肋骨,与他相伴,从日出走到日落。这愿望随着她的成熟与日俱增。但是,当昔日的同学一起相处时,她没有勇气靠近自己心爱的人,那个月夜,毕竟是天地为证的两个人的秘密,北北居然连妈妈也不曾告知,她把这秘密小收藏在一个少女内心世界的最心
底层。在只有她和丁胜两个人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她一次又一次羞怯地躲开了。今天,春情升腾,犹如喷薄而出的朝日,势不可挡。那是少女心中的太阳,她露出了遮羞的云端。终于,李北大胆地扑进丁胜张开的臂膀里。两个人紧紧地搂抱着,彼此只听见对方激动地喘息,怦怦,怦怦,你一下我一下和拍的心跳。
“还记得那个月夜吗?”姑娘仰起了她的唇,像一颗熟透了的樱桃,滴着诱人的蜜汁。她的声音很轻,像一根琴弦在被人拨弄。
“记得,你是那样的美,美得我无法承受。”小伙子颤抖着闭上了眼睛。
“我爱你,就从那个月夜开始。”姑娘情意绵绵。小伙子仿佛又看到那个泪眼模糊的少女吻着他那缠满绷带的伤腿。他忘情地俯下身,将那熟透的樱桃含进口里。他抖得厉害,身不由己。他热烈地吻着姑娘,像在梦里。李北身上有一股奶香,清醇,甘美。两个人全都醉倒了。
七九了,冰开了,先是老寿星大干妈走了,她是寿终正寝。后是林二过世,晚上,像往常一样睡下了,第二天,林昊烧热了锅,他已经凉透了。程果平说,许是夜晚突发心脏病猝死的。狐皮沟的人都去了。在收拾老人的遗物时,林昊看到了一床小花被,看到了一方纸,那纸板正得像一张画片,上面有几个漂亮的毛笔字:正月初一生人,属虎。
谁是我的亲大大?谁是我的亲娘?这个满二十的人在打问自己的出身。
“娃呀,你是我们狐皮沟人的亲娃娃。”桃花抱着他奶大的人哭成泪人。
“昊啊,以后遇到难办的事,找你大哥我办,找你茅缸大侄子相帮。”梁支书在对那个曾在他的怀里小得像个猫崽子的人说话。
不知为什么,丁胜觉着自己和林昊真的是同病相怜呢。谁是我的爸爸,谁是我的妈妈,天底下,只有最不幸的人,才会这样去问的。
这是他问过莲花妈妈的问题,他没有问到结果。但是他懂了,疼他爱他的人就是亲人。林昊也应该懂得,应该懂得。丁胜直视着林昊。两个男人对望着。林昊说:
“养大我的人就是我的亲大大,我懂得我该做啥。”程果平和山里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