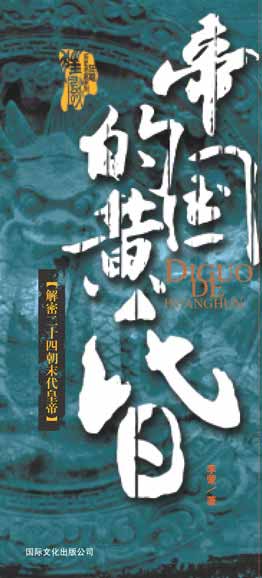厚厚的黄土层 周国春著-第2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收工的人们在过一条山涧。
上面下了几天雨,水流得挺急。程果平几步跨过了这条涧。老丘已经过去了,忽然一抬头,只见龙似的山涧上边冲下来几块石头。上边有个石场,是几块石头滚进了山涧,它们跳跃着,翻滚着,折着斤斗,顺水而下。不好,兰兰和黄源源在后边。她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大喊:
“快走,危险!”她一把拽过兰兰,把她推过了涧,又一次地扭过了头。说时迟,那时快,几块碗口大的石头已经飞到了她的身边,黄源源这时离她也只有一尺远。不知是哪里来的力气,她扑了上去,把黄源源扑倒在地。黄源源的头被她压在身子底下。一块石头砸在了她的头上,另一块石头从黄源源的小腿擦过。走在前边的人听到了喊声在往回返。
“老丘,老丘,血!血!”兰兰边喊边向老丘靠近。黄源源从地上挣扎了起来,他抱住了老丘。老丘的头在冒着血。
“没有事了,就冲下来那么几块石头。”老丘晕了过去。“老丘!老丘!”黄源源在喊。程果平跑过来,用黄土止住了老丘头上的血,背起了她。人们一个个围过来,抢着背老丘。程果平喘着粗气儿说:
“算了,我背,你们跑不稳当。”张鼎诚的布衫脱了下来,人们在行进中,用它裹住了老丘的头。
老丘在昏迷中。人们进了村,套上了最好的骡子,驱车赶路。
山里人上了公路,居然拦住了一辆卡车。猴娃抱着老丘挤进了驾驶棚,其他的人在支书的带领下踩着月亮的影子往县城赶。
老丘被推进了抢救室。她的意识在恍惚中。
拳头,砸在了玻璃像框上。红色的,是血,金色的,是星星。
一张脸扭曲着,他怒视着自己,像是用锥子在扎脑髓,疼,疼,疼呀。老丘在哼,她哼出了声。儿子,镜框里还有儿子,是她和田群的儿子碎了,和镜框一起碎了。女儿呢?女儿的头在她和田群的中间,是在中间,不对,找不到了呀,在,她还在镜框里。女儿的手在挠,挠了她的伤口,钻心的疼痛,一团黑云笼罩着她她冲出了黑色的云团,她努力在想,想呀想,终于想起来了,田群在被群众批斗,组织上和她谈了,要她是的,划清界线。于是,他们离婚了。她的头在炸,她找不到自己了。儿女们找得到她,不找她,她想,想那个她砸碎的镜框,想那五张笑脸。她又砸了一个新到燕城不满三个月的副市长不是砸,是抄家,革命有理,造反无罪。她,红小鬼,造反派,她在革命。她在一间屋里,在看一本天天在记的,日期,天气一个男孩子一把夺过了那个本子,那是他的是的,不会错的这是我的我的日记本他的眼珠瞪了出来,他的眼珠变成了钢钉,向她飞过来,扎在她的头上,像万箭钻进了她的脑仁。她找不见自己,她是在哪里?那个男孩子在黄土窝窝里,他的眼珠又瞪了出来。不对,明明是黄北峰,是她在战争年代阵亡的丈夫,活着,没有死,怎么,竟是那不曾谋面的黄副市长。她晕了,她又一次晕了。她在云里走,她在雾里飘。她在问苍天,我和黄北峰有一个儿子,儿子,我的儿子,他在哪里老丘的脑袋越来越沉了。她突然看到了一团云,是田群站在那里。他在说话:
“淑贤,我不记恨你,你没有错。”是的,他被结合了,和黄北峰同一天,同一天自己呢?自己呢?在看,看他的信复婚不,对不起不能,错了?不毛主席革命路线
红小鬼永远,永远,应该画一个句号,要圆,要圆。
老丘还在抢救中。猴娃敲开了薛主任的窑门。
“小兄弟,你深更半夜来,有急事?”
“住队干部受了重伤,快,救救她。”狐皮沟的人赶到了,薛主任带着县委的一些干部也赶到了,最好的医生上了,最好的药用了。
医生们疲惫地走出了抢救室,他们在摇头。黄源源冲进了抢救室。老丘睁开了眼睛,看着黄源源,仿佛在问,你认出了我?肯原谅我?她的瞳孔放大了。黄源源痛哭流涕,他好悔呀!
老丘,老丘啊!人们在哭泣。
狐皮沟举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浩大的追悼会。薛主任为她致悼词,称她是我党优秀的党员,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忠贞不渝地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外村的社员、干部来了,燕城的干部,省里的干部,地区的干部,县上的干部,公社的干部来了。人们臂缠黑纱,献上花圈默哀。
老丘埋在了狐皮沟的阳洼洼上。梁支书说,让太阳天天看着她。
“这该是今生今世不会离开咱狐皮沟了吧?”桃花问哩。
“还有什么今生今世,这该是永远的留驻了。你没看见,她的坟前立了碑?”梁支书哽咽着。
“她的亲人呢?怎么没见?山里人不明白,她没有成家?”
老丘家里来人了。一行四个。男的叫田峰,带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那个男人说:
“淑贤,我来晚了。”三个孩子跪在坟前喊妈妈。
“这下好了,她该合上眼了。”张鼎诚是这样说的。
第二年的清明,狐皮沟的社员和学生们(两个住队干部年前就走了)为老丘来扫墓。
第十五章离村并没有离土的人
1970年的秋天,地区的一些工厂开始招知识青年进厂做工。
全国已有个别重点院校进行招生的试点工作,鸟儿展开了翅膀。
“吴欢欢第一个离开狐皮沟,进了地区的一所钢铁厂。”
“吴欢欢老子的是工人,那女子比旁人强,捧上了工厂的铁饭碗了。”
“那几个呢?”
“说不好。”乡里人唧唧咕咕地议论着,他们开始注意到学生的出身了。
吴欢欢要走了。能挣工资应该是好事。爸爸老了,不能总让他贴补自己。当时,狐皮沟的十分工只值三角钱,这不仅在米家山公社是头一份的,在川坪县也是排在前边的。因为,大队有苹果树,有猪场。但是,这三角钱对于知青是什么概念呢?一年辛苦之后,学生们除了给自挣了口粮(五谷杂粮三百来斤,不算土豆和红己
薯),男学生每人分得六七十元现金,女学生分得五十元左右。江小南拦了几个月羊羔,公社、县上、地区、省上出席了几次积代会,于是,没有雨天的误工,少了些做饭的误工,尽管她一天只挣八分工(老丘死后,梁支书在一次会议上提到了她的一个关于同工同酬的建议,那两个住队干部一致赞同。于是,男学生开始挣十分工了,山里男人能拿起的活,他们也都拿得起,没有一点儿含糊;女学生开始挣八分工了,尽管她们也揭地、拿粪、拉车,但是,她们毕竟是女人,拿到女人的最高工分,也应该没有意见了),一年下来,所挣工分竟是学生中的第一。于是,她分得了八十三元现金。
春节,学生们拿自己分的钱买车票回了家。
七个人回到狐皮沟以后,在一起分吃糖果,述说与家人的团聚。李北去了江西的五七干校,在妈妈那里住了二十八天,和干校的叔叔阿姨们挑了十八天河泥,跟一个干校的卫生员学了八天打针、发药。晚上,在妈妈的指导下,读一本《农村医疗保健手册》。
因为她对妈妈说起了老丘,妈妈告诉她,如果离医院近一些,如果生产大队医务室条件好一些,为老丘止住血,她是不会死的。李北深感遗憾。所以,她想学习一点医疗知识。妈妈还带她乘着江西老表的木船,顺着一条叫沅江的水到桔香镇去,用了两天的时间,买了药,买了书。江西的清水、红壤、黄桔,还有性情豪爽的撑船老表,给她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她为伙伴们和山里人背回了几十斤蜜桔。山里人从来没有见过桔子,茅缸拿起一个就啃,又苦又涩又酸,他一脸的难堪相。学生们告诉他要剥去皮。他吃了以后还是不满意,说那比不上山里的杏,好看好吃还不用剥皮。
丁胜去了胶东农村,在爷爷奶奶和妈妈那里,他很幸福。亲人们让他留下来,那里倚山傍海,景色宜人。但是,他钟情于陕北的黄土窝窝。他带回了花生米、海米、虾皮。山里人吃了丁胜带的海货,直摇头,这米米皮皮的,腥哩,赶不上咱这里的牛羊肉块儿和肥猪肉片子香哩。
黄源源回燕城了。他是黄家的娇儿。哥哥长他十岁,如今是野战部队里的一位营长。妈妈十分疼爱他,因为,只有他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最长。他没有像哥哥似的从小放在老乡的家里,后来又住在寄宿制学校里。可是,他穿补丁衣服,从小就会给自己钉钮扣,会烧稀饭,拖地板。他和爸爸谈了一次话,从晚饭后谈到深夜。他问爸爸记不记得一个来抄家的阿姨,爸爸说不记得了,因为他在挨整的时候,是很少抬起头来的,斗他抄他的人太多了。他告诉爸爸,那个阿姨叫丘淑贤,成了狐皮沟的住队干部,为了救他而牺牲。丘淑贤,他分明听到爸爸重复着那三个字,后来又连连摇头。他临走时,爸爸又突然问他,你难道没有那个老丘的相片吗?他有。在给老丘开追悼会的时候,他们加洗了许多老丘的正面相片,他留下了一张,还放在了随身带的一个小小的塑料夹里,他翻出来递给了爸爸。爸爸看到了这张相片,竟一下怔在那里,如一尊雕像。
“您认识她?”黄源源很是惊讶。
“是的。”
“她是谁?”
“爸爸的战友。她居然还活着。”爸爸的眼睛亮起来。
“她死了呀。”
沉默和沉默在一起,长时间的。
“晚了,一切都晚了。”爸爸的眼光暗淡了下去。
黄源源忽然想起了老丘的丈夫也说过晚了。
黄源源带回来的奶油糖很好吃,他带回来的信息,更令人玩味。原来是这样,老丘是你爸爸的战友,你的救命恩人。学生们又一次认识到这个世界并不大。当然,黄源源省略了抄家那一段,这是需要忘掉的。
江小南也回了燕城。爸爸在研究所还没有什么科研项目搞,可是他进了所的领导班子,因为他毕竟是老党员。他还是孤身一人,没有再向女儿提后妈的事。也许,他尊重女儿的意见。小南的两个弟弟也回来过年了。爸爸和儿女们在一起非常高兴。年三十,他为孩子们唱了一首他们那个年代在大学里流行的歌曲《山楂树》,竟唱出了两行热泪。小南知道爸爸和妈妈当年同在北固大学读书,在两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里,妈妈选择了爸爸。她说,两个小伙子,一个刚愎自用,然而犹如一团永不熄灭的火;一个优柔寡断,然而犹如一湾源源不绝的水。妈妈最终投入了那水的怀抱。她说过,源源流水,平淡,但是不会断头。小南忽然固执地想到了一个问题,爸爸当年难道没有在两个漂亮的姑娘之间进行过选择吗?女儿在临走时终于这样说:
“爸爸,为了您的幸福,不要再问女儿可以不可以接受后妈了,这是您自己的事。”江小南为人们带回来一大包铁蚕豆,咸味和甜味相交,硬硬的,很难咀嚼。人们说,这铁蚕豆真有嚼头,有滋有味。是的,人生难道不像是一枚令人难以咀嚼又有滋有味的铁蚕豆吗?
徐末末的爸爸是城独立师的政委,他走的时候,爸爸就说燕
了,下乡去吧,你老子当年就是从那里打进城的,你的老祖宗们都是修理黄泥巴蛋蛋的,你是在认祖归宗哩。徐末末这次探家,竟探了个齐全。他家里五个孩子,末末在正中间,上面一个大姐,一个哥哥,如今,一个在医科大学毕业,进了大山里的一座野战医院。
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红卫兵大学生,虽然只上了一年大学,却成了一名海军军官。军人难得过一次春节,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军人,这次却凑到了一起。徐末末的下面,是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弟弟去内蒙古大草原插队落户,成了一个新牧民,已经会骑着马儿驰骋牧场了。妹妹留在父母的身边。那时有这样一个政策,一家可以留一个子女在身边。于是,她这个初六八的中学生便进了燕城的一家火柴厂。除夕的晚上,家里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有鸡,有带鱼,有红烧肉和酱牛肉,还有几盘青菜。一只囫囵的清炖母鸡,由徐末末进行分配。两只鸡腿,一只是爸爸的,一只是哥哥的。妈妈和大姐最爱吃鸡翅膀,弟弟最爱啃鸡头和鸡脖子,鸡肝鸡心鸡肫子,还有母鸡肚里那么多的小鸡蛋和鸡皮,小妹妹当小孩子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是她的(鸡身上的肉,大家随便吃)。最后,剩下了一对鸡爪。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家人都认为末末最爱吃鸡爪。实际上,他并非喜欢,别人都喜欢了,剩下的对于他就无所谓喜欢不喜欢。末末记事的时候,就学会了迁就弟妹的无理耍赖,忍让哥哥蛮横的拳头,服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