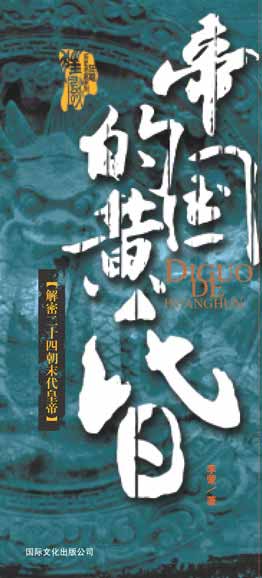厚厚的黄土层 周国春著-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还是包产到户好,这话你说过?”老马先问。
“说过。”是的,程果平不想赖。在田间地头,这话他没少说过。
“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老丘问他。
程果平不响。什么是包产到户,什么是责任制,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他不想和任何人去理论了,不可能有结果的。
“问题是十分严重的。你的右派问题,历史上作过结论了。而这可是新问题。”小慕在向他标明问题的严重程度。程果平瞥了他一眼,他心虚了。他和暑女躲开锄地的人,在玉米林里肉压肉滚在一起,插在一起,程果平偏巧就见了。于是,小慕带人在一天的晚上围住了小学校曲静波办公的那孔窑洞,把窗户纸戳开了一个又一个的眼,而人们却大失所望。因为,两个人,竟是衣冠楚楚,落落大方,争论着一个有趣的问题。接着又去了几次,依然是大失所望。现在,他终于在政治上揪住了程果平的小辫子。也许他能取胜一时。是的,慕生林并不是坏人。但是,被人窥探出隐私的人,为了自己的那张脸,往往是会扭曲了自己的灵魂的。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只是,程果平看不起这样的人。程果平的一瞥,使他很不自在。他,一个年轻有为的地区行署办公室的主任,正当春风得意时,文化大革命的狂飙一扫他无量的前途。先是陪着专员们接受造反派的各种提问,然后是揭发专员们的大小问题。人说他是黑笔杆,可是要说反党反社会主义,真还是什么问题也找不上他。他被解放了,于是打起了杂。打扫会议室,发送报纸。最后,需要去各县住队,人们想起了他。离开妻儿老母,来到了狐皮沟,说假话,说套话,他够了,他腻了。忽然,他发现,在山里女人裸露的乳峰间,润滑的曲径里,他能够发泄,酣畅、淋漓;他能够沉醉,恬静、舒适;他能够幻想,甜蜜、美好。于是,他忘乎所以了。当他的丑陋为人所见时,先是羞愧,羞愧得无地自容,后来固执地想,你十年右派,比我更感空虚无望,我就不相信,你会是无暇美玉。
但是,他错了。因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希望你能认识自己的问题,接受人民群众的批斗。”老丘对他说。梁支书没有说什么。程果平下去了,张鼎诚被叫了去。
“你是富裕中农?”老马开门见山。
“这是土改时定的成分。”张鼎诚话中有话。如今,入社都十几年了,大骡子大马归了社,我和大家都一样,是干一天活挣一天工分的社员。
“因为你是富裕中农,发家致富的念头就总也搁不下。”老丘给他分析。
“我们农民想着多打粮食,过好日子,有什么不对吗?”张鼎诚不服气了。“人说社会主义是康庄大道,共产主义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就为了去奔那好日子嘛。”
“这不对,社会主义的农民,不能只想自己过好日子,而应当首先考虑党和国家的利益。所以,我们不能分田单干。”老丘帮他分析。
“那你说一说,为什么自留地的庄稼长得比队里的庄稼好呢?”
张鼎诚想起了他和程果平议论过的,你在自留地里出了一分力,就会有一分的收获,你就有了种地的积极性呀。因为,多劳多得,你看得见呀。
“因为有的人太自私了,给生产队干活不出力,给自己干活下死力。”老丘继续着她的分析。
“你们说我们自私?我们不好好种自留地,青黄不接时我们吃甚?不就是那自留地里能想吃点儿吃点儿,队里的庄稼你想吃点儿能吃上了?”
“可是,你知道不知道,你的想法要不得。你想走分田单干的路,就是走回头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老丘越说声音越大。
“啥?你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张鼎诚支起了他的耳朵,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日你们先人!”他跳起脚大骂,跺跺脚走了。人们一惊。三个干部惊的是山里人的厉害,梁支书惊的是气恼了张干大,别把老人气坏了。
“不能手软,开他的斗争会,那么嚣张!还有那个右派。”老丘十分果断。
“开批斗会?批他俩?他俩是阶级敌人?”梁支书的不满一股脑儿倒出来。
“我早就想说你这个支书了,同志,你的阶级斗争的弦为什么不绷一绷紧?你看看你这个狐皮沟,阶级敌人猖狂到何等的地步,你却可以不闻不问。你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你的屁股坐到哪里去了?”不知道为什么,老马还着实有些服气。别看老丘文化水平不高,写几个字像狗刨,可是说起阶级斗争的套话,说得流畅、痛快,不用写讲话稿,随便一讲就够味了。他看着老丘,仿佛看到了革命样板戏《海港》里的方海珍,仿佛看到了革命样板戏《龙江颂》里的江水英。他感到好笑。
开斗争会的事定了下来,就在地头开,这是很时髦的。标语牌要做的,口号要呼的,发言稿要写的。写标语牌的事,自然是慕生林去干了。从他一进狐皮沟,村里的大幅标语就都是出自他的手笔。他的字像他一样标致。呼口号的事交给了二宝,发言的事学生出两个人,社员出一个人。徐末末尽管十二分不愿意,用几根大棒一敲,什么你是革命军人的后代,向阶级敌人冲锋陷阵,你不去谁去;你是一名共青团员,要站稳立场,现在是考验你的时候。徐末末只能上。另一个发言的是江小南,她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批判要带头,这更是没的说了。社员出一个人,稍微困难了些。想让林昊发言,老马嫌他个子太小,形象不好。林昊后来曾对江小南吹说过不止一次,谁说个子矮了没有好处。可是找谁好呢?
最后找到了茅缸,这真是如同祸从天降。兰兰的亲大大他怎么能去批判,那是梦中磕拜了几回回的丈人大大。可是,谁让你是支书的儿子。茅缸为此掉了泪。桃花说:
“儿呀,有啥法?如果真是千不该万不该,就活该天打五雷轰吧。”
开批判会的那一天,乌云密布,老天爷一副风雨欲来的嘴脸。
程果平和张鼎诚低着头站在地头,站在山里人的脸前。梁支书虎着脸,人说他眉眼发青。发言的人,眼睛都看着手里的纸,不愿意正视面前的俩人。张鼎诚的妻子儿女以及媳妇们都没有露面。茅缸最后一个发言,他面孔黑黄,声音打颤。二宝在川坪县中参加过批判大会,让他呼个口号不是难事,但是今天却无论如何也呼不出个气势来。最后,老丘进行总结发言,她说得磕磕绊绊的,她的话不时被天上的炸雷打断。人们记不得她是不是说完了,因为震耳欲聋的雷鸣唤出了刺破天穹的闪电,黄豆大的雨点打在人们的头上、脸上、身上。人们叫着跑开了。
张鼎诚没有跑,他在大雨中移动着僵直的步子。流淌在面颊上的有雨滴,也有他的老泪。他终于可以哭出来了,他终于可以大声号叫了。他丢了人,丢了人呀。该批斗的是谁嘛?是那个逼死杨白劳,把喜儿变成白毛女的黄世仁,那是该千刀万剐的,该批斗的是他呀!怎么,自己如今也与黄世仁同罪?这是造了什么孽嘛!老天爷呀,我一个汗珠子摔八瓣儿地干,我亏待了谁?这不公道,不公道啊!雨水把他浇透了。他还在走。走在一条年轻时走过多少遍的路上,一步一滑,终于进到一个小小的山洞。这是他当年和婆姨霜花幽会的地方。就在上个月,他扶着大病初愈的霜花还来过这里。
像是昨天发生的事。他们俩儿一起坐在洞里。
“我说过的,阎王那老儿的还不会要你。”他好幸福。
“那是你硬拽着我,不让那老儿的领我走。”霜花仰起他的脸。
那曾经是一张花儿一样的脸,现在已皱巴成核桃皮儿,只有那双眼睛依旧,像天上最亮的星。
“公家的大医院还是好,不然,你那瘤子就会勾去你那小命。
你死了,我的心也就死了。”他用大拇指刮着霜花的老脸蛋儿。霜花很是惬意。人老珠黄?不,霜花在男人的眼里,永远是一颗晶莹清亮的水珠,是鲜活水灵的一朵山丹丹花。当年,就是在这个洞里,他们私定终身。在这个洞里,他开启了霜花那扇处女的门,走进了一个神秘、美妙、痴醉的世界。为了梦想成真,他抗争了,他奋斗了,他也成功了。他娶了那个倔老头的独生女。那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庄稼把式,横挑鼻子竖挑眼地顶走了多少个有模样、通情理、有房有地有手艺的好后生。他跟着老丈人也做成了一个好庄稼把式。他的窑里,婆姨汉汉恩恩爱爱,两个儿子一个赛一个的精明能干。上了五十了,霜花又为他添了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和霜花年轻时一模一样,人见人爱。他窑里的人,让他感到一个山里汉子的骄傲。在霜花手术之后,多少人又在羡慕他的精明和果断。可是,今天,今天人们又做了什么呢?批判他,开他的斗争会。人们羞辱了他。他的鼻涕老泪如泉水一般。他活到这把年纪,眼见着该往七十上奔了,这是第二次流泪。第一次也是在这个洞里,为了他的霜花,为了梦想成真的那份艰难,他和她抱在一起,痛痛快快号上过那么一回。而这一回,他一个人在这里,他一个人,为了自己失了一个山里男人的那份尊严。
雨停了,山里人走出了避雨的洞穴,却不见了张鼎诚。
“张干大!张干大!”人们满山喊叫。
“张干大!张干大!”只有黄土山的回声。
张鼎诚的儿女们也都上了山。
霜花上山了,她赶不上年轻人了。她不慌,她的男人,她心里有数。
在那个似乎只属于他和男人的山洞里,她的男人坐着,一身的泥水,一脸的泪水,现在,都快要干了。他闭着眼,像是睡着了。
“走,咱回,回咱的窑去。”女人说。
“霜花,是你?”男人睁开了眼。
他们互相搀扶着,在太阳的笑脸下,踩着泥泞的黄土地。
“找到了!找到了!张干大在这儿!”人们向他们跑了过来。有山里人,有学生,也有那三个住队干部。
张鼎诚大病了一场。人们开始骂丘八,骂马骡子,骂小生。是他们,搅得狐皮沟乱成一团,糟成一堆。连张鼎诚、程果平这样的人都斗了,将来还不知道会斗到谁们头上呢。山里人觉着安宁的日子似乎没有了。
就在这个时候,老丘收到了一封信。三个女学生看到的,她在油灯下,把这信看了一遍又一遍。白天,和山里人在地里锄谷子,歇下的时候,她躲开众人又掏出信来看。李北见到她在擦泪。几个月来,她和山里人一起下地,那张白净的发面脸,已经被大自然用风儿和泥土涂成了黑黄的颜色。现在看上去像是一个老倭瓜。
还是在这个时候,因为要慰问驻军,公社要狐皮沟宰杀十头骗过的羊。那是一些长得半大不大的羊羔,人们说,那羊的肉是最嫩的。人们残忍地进行了屠宰,又剥下了羊皮。江小南像个孩子,对着血淋淋的羊尸痛哭流涕。那是在自己身边欢蹦乱跳长大的生灵,怎么说杀就杀了呢?杀羊的几条大汉劝不住她,她不停地喊着:
“你们残忍,残忍!你们还我的羊,还!”学生们也拿她没有办法。
“你看,你又不是孩子,怎么连这个简单的理都不懂。在这个世界上,人就是要主宰一切,人要宰杀生灵,要吃它们的肉。反正,它们会很快地繁殖,明年,新的羊羔就又出世了。”林昊坐在她的旁边,耐心地劝她。
“老丘来了,为她梳理着头发。”
“傻孩子,这还有什么想不通的。”江小南靠着她,想起了妈妈。
“老丘,你也有女儿吗?”
“有,我也有像你一样大的一个女儿,还有三个儿子。是三个儿子。”
她喃喃地说道。她擦起了眼睛。
“老丘,你”
“我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张鼎诚的病好起来了,但是精神头远不如以前了,还经常长嘘短叹。猴娃想起了薛主任,他说过,有事去找他。我要去找他告状,告这些住队干部。猴娃的决心下定了。明天锄完山上那块谷地我就去县城。
山里的糜谷是广种薄收,有的偏远些的地角,只能草草锄上一遍。这一块谷子长得不赖,所以锄上了第二遍。这一天,张鼎诚也上山了。半个多月了,他终于又和人们在一起劳动了。张干大长,张干大短,人们问候他,住队干部也问候他。张鼎诚心里好受多了。一天的活儿并没有干到日头落山。因为这块地离村子最远,干完了,短时间里不用再来了,所以人们格外卖力气。
收工的人们在过一条山涧。
上面下了几天雨,水流得挺急。程果平几步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