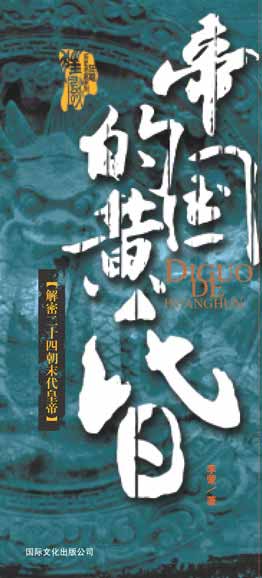厚厚的黄土层 周国春著-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没有。他是志愿军的团长,战败了,做了俘虏。”
“不投降,能做俘虏吗?”
“爸爸说,他没有投降。”
“做了战俘,怎么样呢?”
“没有了党籍,没有了军籍,爸爸说,像是人民的罪人。”
“他不是没有投降吗?”
“没有用。我偷听过爸爸对妈妈说的话,他说,投降派是中国人深恶痛绝的,他这辈子是跳进黄河了,洗不清白了,还不如战死。妈妈说,别说了,好死不如赖活,认命吧。”
沉默。两个孩子,一个是国民党军官的后代,一个是志愿军战俘的后代。他们也许还不懂,这对于他们,将意味着什么。但是他们已经隐隐约约地窥见到他们头顶上的天空,并不是蔚蓝色的。
如今,考试成功了,两个孩子陶醉在人生的一个胜利之中。李树槐得到了爷爷的奖励,要带他去看大海。临走时,他见了小龙。
小龙尴尬地一笑:
“你去看大海,我要去卖冰棍,要给我自己挣够学费。姐姐的心脏病更重了。”李树槐顿时没有了要去看大海的喜悦。
“你比我强,因为你有一个当大官的爷爷。”小龙用舌头舔着嘴唇,他在想,这个世道对我不公平。就在那一天的晚上,黑毛头给爷爷讲了小龙的爸爸,讲了他和小龙都说不清的战俘。爷爷轻轻地拍着他的背,喃喃地说:
“胜败乃兵家常事,兵家常事。”
“爷爷,没有投降,也叫战俘吗?”爷爷在点头。
“那战俘和战俘不能是一样的,对吗?”
“孩子,这太复杂,太复杂了。”爷爷在摇头。
旅行开始了。
这是一次有趣的旅行。黑毛头在爷爷、佟辉爷爷、吴奶奶和莲花妈妈的带领下,来到了海边,来到了吴奶奶的老家。从熙熙攘攘的都市来到海天一体的天边地角,对十三岁的孩子来说,反差巨大,使他的眼、耳、鼻、舌、身,简直应接不暇。沙滩上的贝壳五颜六色,他捡不过来了,干脆全扔了。一想,不对,给小龙带一些吧,他不喜欢可以给小娟,还有小青和小松呢,还有很多同学们呢。于是,他把扔掉的贝壳又一个一个地捡了起来。但是最能打动他的还是成山头那呼啸着撞击山石的海涛。爷爷说,到了成山头,就是到了天的尽头。他看到了,那“天尽头”三个大字是刻在巍然屹立的一块石碑之上的。
“这里为什么叫天尽头?”
“因为古人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天是有尽头的,地也是有尽头的。既然这里可以最早看到日出,人们就认为成山头是太阳升起的地方。”爷爷在给孙子讲一件古老的事情,老到没有开始,没有结尾。
“那么,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是天的尽头了?”
“是的,古人是这样说的。”
“所以秦始皇要到这里来两次吗?统一中国的始皇帝,黑毛头很佩服。”
“是的,统一中国的第八个年头,他来到了这里。第二次来,就是公元前的210年了。”
“爷爷,他离开成山头一年就死了,还死在了路上。”对于这段历史黑毛头是熟悉的。
“可是秦始皇第二次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求长生不老的药。”
“他没有能长生不老。”
“是的,因为他对人民实行暴政,焚书坑儒,把事情做绝,走到天的尽头,没有了退路。”
“爷爷,现代科学说,地球是圆的,宇宙是无限大的,所以,谁也走不到天的尽头。”
“但是,人的生命是有尽头的。”
“爷爷,那还是雷锋叔叔说得对,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是的,就在这一年的春天,毛主席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苏联的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曾使他激动不已,现在,中国的普通一兵又在激励着他。
“海也是有尽头的。”爷爷看着远方,他在想儿子。
“爷爷,还有谁来过这里?”黑毛头不想让那个海岛牵走爷爷的思绪。
“汉武帝也来过这里。”
“他也是一个厉害的皇帝。”爷爷带黑毛头去陕西看过武帝的陵墓,那里还有霍去病的陵墓和墓旁马踏匈奴的大型石雕,爷爷说,这石雕实际上是在诉说汉武帝的功绩。
“是的。”爷爷爱抚地摸着孙子的头。
“爷爷,坐江山的皇帝为什么那么爱海呢?”
“因为海是国家的防线。”
黑毛头在成山头看到了邓世昌的一尊像。当年,中日甲午战争在成山头外海激战,邓世昌是为国捐躯的,他葬身大海。爷爷说了:
“守土将士,魂系大海。”
在吴奶奶的家乡,人们很开心。除了好吃的海鲜,黑毛头最喜欢吃的是无花果,绿色的衣包裹着粉红色的,黄白色的果实,甜甜的。吴奶奶告诉他,无花果不张扬自己,它的果实人们可以从春天吃到夏天,从夏天吃到秋天,从秋天吃到冬天。它不会开花,只会结果。二十天的时间过得飞快,黑毛头一家人又回到了燕城。
开学的第一天,李树槐知道自己和小龙分到了一个班里。他盼小龙到来,想给小龙讲成山头,讲无花果。但是小龙没有来上学。
一个姑娘和自己同桌,她叫李北。这个名字他听说过,是在哪里听说的?他没有心思去想。小龙怎么了?是学费没有挣够?不会。是病了?他很结实。是他家里有事?会是什么事呢?下午,天下起了雨,他望着雨水涂抹着的玻璃窗,心里乱糟糟的。突然,他看到一个人冒着雨跑过了操场,向教室跑了过来,没有背书包,不像是来上课的。他又分明看到,那个人像小龙,是的,确实是小龙。随着一声报告,湿淋淋的小龙进了教室。
“老师,我姐姐死了,今天我不能上学了。我的入学手续已经办好了。”没有来得及听老师说什么,李树槐站了起来:
“小龙,小龙,你说什么,说什么?是高小娟死了,她死了?”
李树槐哭了。他的同桌也哭着站起来。他记起了,小娟说过李北是她的好朋友。
小龙说,姐姐得的心脏病叫动脉导管未闭,医生说可以做手术,但是爸爸妈妈没有这笔钱。那个叫李北的同学哭得很伤心,小龙交给她一本《简爱》,这书是小娟还她的,书里夹着一片红色的枫叶。
1965年的冬天,爷爷正在南方参加一个会议,突发脑溢血,竟死在了会场上。爷爷的追悼会十分隆重。他安静地仰卧在鲜花翠柏之中,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及他的亲朋好友来为他送行。黑毛头站在爷爷的遗体前。许多他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有的亲他,有的抚摩他,有的搂抱他。
按照爷爷的遗愿,他不进燕城郊区的陵园,要去成山头海葬。
佟辉爷爷和吴奶奶就要启程了。爷爷的一位挚友,从海外回归,他带回了一封几经辗转的信,是海外的儿子写给爸爸、妻子和儿子的信。黑毛头读了这封信,爸爸把莲花妈妈称作“云霞”,信的开头写道:
“爸爸、云霞和我不曾见过的儿子。”信写得很短,字里行间让人读出的是十二分的想念。为什么莲花妈妈以前叫云霞,这对他并不重要,因为爷爷说过,名字就是人的代号,他早年在一所医院里治病时,医院里所有的人都喊他5床,5床就短时间地成了他的名字。所以莲花妈妈以前也可以叫云霞,这是大人们的事。重要的是,他请求佟辉爷爷把这封迟到的信和爷爷的骨灰一起带到大海边。
就这样,黑毛头送走了佟辉爷爷和吴奶奶,他们老了,想回到海边去安度晚年。他也送走了爷爷的骨灰,让那骨灰带着爸爸的信飘向大海吧。黑毛头想起爷爷在成山头说过的话:
“守土将士魂系大海。”
第九章这路曲里拐弯的
人们都如同做了一场恶梦。在这场恶梦中,从身心到神情都被极大伤害了的人,他苍白,他憔悴,他潦倒。一切懊恼、沮丧、悲观、失望、疼痛、愤怒(然而,这里没有悔恨,一丝一毫没有,因为他坚信自己的无辜,他不认为自己曾经错过)残酷地折磨着他。
但是,他最终还是第一个从恶梦中醒了过来,他要面对现实。
第二个从恶梦中醒过来的是北北。她的太阳病得没有了光泽,病到了足不出户的悲惨境地,无声无息地在这个家里存在着。北北的四周静悄悄的,那些笑闹的声音都藏到哪里去了?妈妈的脸,阴云密布。姜阿姨只低着头匆匆忙忙地做那些做不完的家务活,有时甚至于连头也不抬。空气令人感到窒息,她憋闷,她烦躁,她伤心。
突然的一天,书房的门慢慢地打开了。爸爸从书房里走了出来,他简直判若两人。那炯炯的目光变得有些呆滞,头发乱蓬蓬的,胡子拉拉碴碴地倒伏着。但是,他在冲北北笑,笑得很认真。
你的病好了吗?北北仰起脸用眼睛在问。他点头,他张开了手臂。
北北哭着扑过去。爸爸的胡子扎了她,扎了她的脸,扎了她的脖子,她笑了,她不能不笑得咯咯咯咯的,像小母鸡在叫,很是滑稽。就连姜阿姨也抬起头笑了。爸爸刮了胡子,修理了头发,又神气了起来。幼稚的孩子想欢呼,我的太阳又亮起来了。只有妈妈没有笑。北北很奇怪,她为什么不开心?
慧敏是最后一个从恶梦中醒过来的人。该想的,她都想了,能想的,她都想到了。走到了今天,做了多少违心的事,她不想再一件件去清理了。一切都过去了。炳彪,他精明强干,是兢兢业业的实干家,前途无量,这都是事实,都得到过证实。但是,今天怎么样了呢?他从山上跌了下来。于是,踏破门坎的人不见了。谈工作的人不来了。叙旧情套近乎的朋友不叙了不套了。什么叫世态炎凉?慧敏从那个属于剥削阶级的父亲那里没有体会到的,如今,却从她的那个共产党人的丈夫身上,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是有人在害炳彪?她没有理由这样想。刘秘书,曾对她说过,李主任太尖刻,太直率,太能击中要害了。而上一级领导是可以随便顶撞的吗?刘秘书常常会为他捏一把汗。如今,这个常常为他捏一把汗的人,也在那里交代问题,接受审查。刘秘书还不是因他而蒙难的吗?自己也曾提醒过丈夫,做事不要做得太冲了,有不同意见,要学会把握分寸。而炳彪呢?他摆一摆手,神气十足地说:
“发表不同意见,这是党内的政治生活。开会的时候,领导就说了,共产党人要敢于讲真话,成绩讲够,问题讲透,还鼓励大家,要有舍得一身剐的精神,不怕杀头,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说到这里他搂住了慧敏,大笑了起来,他说:
“不过问题不会有这么严重,既然让人家讲话,还会去整人家吗?”他未免太幼稚了。他是在从政,不是在搞科学研究。前者没有1+1=2,后者,必须是1+1=2。不信吗?一落千丈,不是事实吗?他这么快地从重负下解脱出来,笑对家人,慧敏又想不通了。他会从失败中走出来吗?他会再造一份辉煌吗?他会官复原职吗?于是,慧敏是笑不出来的。
然而,夜深人静时,在炳彪一次次真挚、热烈地抚弄下,慧敏终于抱紧了他。因为她毕竟是女人,是失去太多人情,仍依恋人情的女人。
月儿缺了又圆了,他和炳彪手挽着手,在庭院里溜达。没有太多的话说,不用说太多的话,他们安静地肩倚着肩,踩着月亮光,走进深深的夜色中。路漫漫,他们会一起走下去的,不甘寂寞,不怕冷落。没有了昔日的忙忙碌碌,没有了门庭若市,彻底换了一种活法,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来到了他们的家。
当这个人的身影撞进炳彪的视野里时,他感到惊奇:
然而,来人并不尴尬。
“章可言,是你?”
“你好!我前不久路过柴峰口,大娘托我给你捎来一包东西。”
他是那样自然,挂在他嘴边的“李主任”也消失得不让人感到突然。
“请坐。”主客落座,保姆端来了茶。慧敏和北北也走了过来。
“大嫂,大娘问你好,他们一家人都想念你们。”章可言的话说得热乎乎的。
“娘还好吗?”慧敏对老人家的事是关心的。
“好。她老人家很硬朗,看个门,做个针线,都还可以。”章可言轻松作答。
“你看见小老虎哥哥了吗?”章可言把北北揽在了自己的膀弯里。
“看见了,看见你的小老虎哥哥了。他比你高出半头。我走的时候,他想让我给你带一对兔子,我告诉他,城里不能养兔子,如果把兔子带到城里,只好杀了吃肉。”
“那多么悲惨呀。”
“是呀,所以还是让小兔在它们的家门口玩吧。”北北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