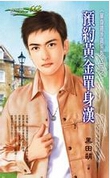伯顿的替身-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个瘦高个是他们的头儿,他预订房间的用名是詹姆斯·法罗。他很快和我交了朋友。当然,他做得并不过分,他仅仅是像大多数客人那样给予老板的儿子应有的关注。
我不知道他们玩的是什么把戏,我看不出他们想要杀我。如果他们是需要钱,我会明白的。不过他们看来已经有了好多钱了。所以我仅仅监视着他们。是的,先生,法罗这家伙的确不好对付。不过我以前跟这种人打过交道。另外,我还有几个优势,他们不知道我已经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也不知道我是个神枪手。
我总是带着枪——无论什么时候,不仅仅是我认为有麻烦的时候才带。您瞧,要我办事的这个家伙交了那么多坏朋友,而且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来找他的麻烦。
几乎每天晚饭后我都和玛丽恩开车出去,我们常常在岛上到处兜风。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这么玩的。有时我竟忘了正事,认为现在情形不同了。我见过好多女人,但没有一个像玛丽恩的,从我上学那时到现在都没见过。当然,这仅仅是记忆。
我们常常是边开车边谈话。她总爱问我去过的地方是什么样,这问题很容易回答,因为我哪儿都去过。
后来,一天晚上,大约在那三个人到这儿十天之后,我真的受到了袭击。我们已经跑了一程,正开车回去,大约九点半左右,突然——嗖——一股尖啸声传来,汽车的挡风玻璃上打穿了一个洞,又一股尖啸声,我看见玛丽恩颤抖了一下。
这对我不是什么新鲜事,我即刻就识别出了这种声音。是无声枪。有人正从远处向我们射击。我把车速挂到最高档朝镇上飞奔而去。我在路灯下停下车,转向玛丽恩。
血顺着她的脸一滴一滴地流下来。她面色苍白,但伤势不重,仅仅擦破了皮。我买些药物给她擦洗了一下。
她是个勇敢的姑娘,既不发抖;看上去也不是那么紧张不安。但我却是有生第一次不能自制了。我的手抖动着。当时我没有迅速拔出枪来。但事后我镇定了下来。我满腔怒火,几乎要发狂了。倒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有什么危险,也不是我认为他们想杀掉玛丽恩,而是因为仅仅由于她喜欢我,我们一起出去,我把她拖到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
回旅馆的路上,我告诉她可能是有人在打兔子,别的什么也没说,因为我想在第二天早上提出控诉。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我知道她不相信我的话。
“如果这就是你想告诉我的一切,伯特——好吧,我不会向任何人提及这件事,你可以相信我。”
就这些。我们一直到旅馆把车停下来也没再说话。我们站在旅馆例门的楼梯下头。她转向我,把手放在我肩上。她的脸色已经恢复正常,但我能看到那块子弹擦破的红斑。
“你可以相信我,伯特。”她的语气似乎在向我发问。
“我当然相信你,玛丽恩,”我的声音似乎是从很远的一条小路上传来的。
这之后发生的事是那么突然。她的头靠我很近,柔软的头发拂掠着我的脸。她抬起头看着我。紧接着我俯下身子紧紧地抱住她,吻她。她没有抽身,我们就这么站了好长一阵子——孤独地站在那儿,非常孤独。
突然传来一阵马达声,一束灯光扫了一下。玛丽恩很快跑开了。法罗和他的两个朋友走进旅馆的时候我静静地站在阴影里。
他们是否看见了我们?我想是的,因为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他们脸上挂着笑容。他们笑了,但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未日已经到了。
首剧的序幕已经拉开,演出开始了。在这以前,我一直睡得很安稳,因为我对自己的危险毫不在乎。但现在玛丽恩也有了危险,而且——好吧,我决定夜里把他们三个解决掉。
十分钟之后我回到了卧室,但是没有睡。我关掉灯,坐在那儿,一直到十二点。这时整个旅馆死亡般的沉寂。
我走到窗外,顺着太平梯爬下去。我知道法罗的房间在哪儿。我一直走到他房下,然后再顺太平梯爬到三楼。他的窗子没有关。半分钟以后我跳进他房间里,在他床头坐下来。
我打开灯,等着他醒来。他对我的拜访确实不害怕,因为他又继续睡了五分钟。后来他慢慢转过身,睁开眼睛。他一下子就清醒了,因为他看见了我的枪口。
他也很聪明。他用一只手揉眼睛,装作还没有睡醒,而另一只手却伸到枕头下。这时我大笑起来,他又抽了回来,手里什么也没有。
“法罗,”我说,“今晚上你大难临头了。如果刚才我没把你的枪取走,现在我就要敲碎你的脑壳。”
我真希望还把他的枪扔在那儿,因为这将是我枪击他的借口。一个无力的借口,但仍是一个借口。如果他手中没有武器或是没有准备,要我对他下手是很难的。但是在他正取枪的时候事情就好办了,因为这是个你死我活的时刻。
法罗当时应该好好想一想,但他却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他说我正冒很大的风险,而且我不可能从这地方逃掉。
但是我制止了他。
“住口,”我说。
他看到我愤怒的眼神就停了下来。这么做相当明智,因为他不能肯定一个人像我这么恼怒时下一步会做出什么来。然后我给他说了几句话。我告诉他今晚发生的事,并且说我知道是他干的。他只点点头。
“你杀了我兄弟,”他说“他在越狱的时候被打死了——是你把他投进监狱的。”
“那么说是我杀了你兄弟,嗯?很遗憾,我对这事一无所知。不过我得告诉你,我的朋友今晚上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干掉你,绝不会失手。我不射车窗,也不射无辜的人。如果我向你还击,老弟,你已经死了。”
我可以看出他有点地惊奇。这不是他预料中的伯顿·康勃斯会说的话。但我明白他注意到了那女孩的情绪。他知道他给了我打击,但我不在乎这个。
“明天早上六点半以前乘客轮离开这里。”
“如果我不离开呢?”他用那种令人恶心的声音道。
因为我没有马上毙了他,他可能认为我有些手软。如果他处在我这个位置上,我想他是不会犹豫的,除非他认为自己逃不了。
“如果我不离开呢?”他又问道。
“如果你不离开,”我一字一句地说,同时想着玛丽恩。“我就敲碎你的脑袋。客轮一走,我就会盯上你,詹姆斯·法罗先生。除非你射得比今晚好一些,否则就让你去见你兄弟。”
我转身走出房间。我真想把他敲了,这诱惑力太强了,可我下不了手。
我夜里没有睡,仅仅是把灯关掉,坐在房间里抽烟,边抽烟边思考。我知道那三个家伙会碰碰头,谈谈怎么办,然后可能决定离开这里。但我只是坐在那儿,盯着门和窗子,把枪放在膝盖上,等待着。
如果他们从窗户跳进来,事情就容易解决了。人人都会认为伯顿·康勃斯只是为了保护他父亲的财产。现在我明白了,他们真的想杀掉我。在这整个事件之后有一种家族情感,家族情感和荣耀——这种潜在的奇异的荣耀总要惩处那些败露它的恶迹的人。康勃斯这么做了,而法罗的兄弟送了命,康勃斯则逃之夭夭。
我听到时钟敲了两下。到两点半的时候,我听到走廊里传来一阵脚步声,然后有人在门上轻轻敲了一下。我没有开灯,而是走过去突然打开门,同时闪到一边。但是没有人进来。
这时我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起初我以为是玛丽恩,但我看到的却是那寡妇。她两目圆睁,看上去非常惊恐。
“是玛丽恩,”她喊道,“她在我屋里——太可怕了——我想她是昏过去了!”
我突然想到那三个人可能会对她下手,我真后悔刚才没把他们宰了。
“快走,”我对那寡妇说。我抓住她的胳膊飞奔下去。她的房门开着,我抢在她前面跑进去,手里拿着枪。
“那儿——在床上,”寡妇说。
我转向床——什么也没有。我突然明白了。但已经晚了——我落入了圈套。一支枪抵住了我的后背。我听到一阵奸笑声。这时法罗说话了。
“把枪扔到床上。”
我把枪扔到床上。完了。我第一天看见那寡妇的时候就该怀疑她,因为她不属于那个阶层。是的,她和法罗是一伙的。而我,我从来不提防女人,现在倒被女人抓住了。我想保护玛丽恩,寡妇知道这一点。现在您瞧这把戏是怎么玩的。无论是好女人还是坏女人现在都帮不了我的忙。而我愿意为小玛丽恩冒任何风险。法罗又说话了。
“现在,康勃斯先生,我们准备带你去兜一圈儿。你最好放老实点儿。谢谢你把枪还给我。”他边说边把枪从床上捡起来。
是的,那是他的枪,我的还在口袋里。我真想拔出来给他来一下,只是我看见那寡妇正拿枪对着我。
“快走,”法罗说。他用枪抵住我的腰走出去。“如果你喊叫,我就毙了你。”
我就没准备喊叫,我口袋里还有枪,我仍然有机会向他们还击。
我们从后面的楼梯走下来,然后朝我的车库走去。
“上车,”法罗说,“我们出去转会儿。”他死死地盯着我,接着便怪笑起来。这笑声隐含着杀机。
他要我来开车。我们驶出大门,走上一条横跨海岛的孤零零的长路。过了几分钟,他要我停下车,然后站起身。
“我得把你的枪取走,”他说。他从我口袋里掏出枪来。“今晚上我们俩只能有一只枪。”
他把枪扔到车后。我听见它砸在座位上,又落到车板上。
我们开着车静静地往前走。法罗一句话也不说。但是我清楚地感觉到,似乎他已经告诉我,前面等待我的就是死亡。他让我带着枪直到平安地走出旅馆,可能他认为没有它我会喊叫。我不知道。但我承认我一直想着它。
我不止一次地想告诉他我不是伯顿·康勃斯,因为我敢肯定他会杀掉我。但他不会相信我;再者,康勃斯跟我的签约还在旅馆房间里。
一路上空空荡荡,我们没看见一个人。月光黯淡。我们行驶了半个小时,或者更长些,突然,我看见前方停着一辆车。
“停下,”法罗说。他的声音冷冰冰的。“你已经走到头儿了。天亮以后他们会发现你,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我们已经走了。”
我在路中间把车停下来。前面那辆车是法罗的,我认出里面的两个家伙是法罗的朋友。我敢肯定他们现在要杀掉我,但我决心绝不失风度。法罗命令我下车的时候,我侧过身把手伸到后座上,碰到了冷冰冰的枪管,我迅速把它抓在手里——它是我的了!
我一生中有过很多美妙的情感,但我认为此时此刻是再美不过的了。我没去想那支枪是怎么又跑到车座上的,我没时间想这个。我紧握手枪,感到热血沸腾。
我不能转身向法罗射击,因为他的枪抵着我的腰部。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害怕的,但他是个谨慎的家伙。
“打开门出去,”他命令道。
我侧身把手放在门柄上,这时我想到一个主意。
“我打不开,”我说。我故意把话说得有点儿颤抖。但我的左手紧握手枪。感谢上帝,我是个左撇子!
“十足的胆小鬼,”他说。他向我侧过身,用那只空闲的手来开门。您别说,这门还真的有些不好开,因为岛上的夜晚潮气很大——是这潮气救了我的命。
仅仅一眨眼的工夫,他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到车门上,与此同时,我对着他的心脏就来了一枪。门一下被撞开了,他滚出去,摔到公路上——死了。
我不需要任何借口,因为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要么他死,要么我亡。
那辆车里的两个家伙简直震惊了。在他们还没弄清怎么回事的时候,我已经跳出去干掉了一个。另外一个家伙反应挺快,我感到右臂上刺骨地疼。但他仅有机会发一枪,我迅速向他还击——一枪就够了——他倒下了。我是个神射手,我开枪射击的时候从不失误。
我不能浪费时间去检查他们是否已经到了。我掉转车头朝旅馆疾驰而去。二十分钟之后,我回到了房间里。就我所知,这件事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把肩上的伤擦了一下,伤不太重,尽管我觉得很疼,因为子弹从中穿了出声。
早上醒来时,肩膀还是很疼;但是我仍穿好衣服,去楼下用了早餐。经理告诉我,那寡妇乘早班客轮走了。
九点左右,新闻传来了:公路上发现三具尸体。我知道我把这三个都结果了。
人们议论纷纷,报界的人和侦探也陆续来到岛上。第二天早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