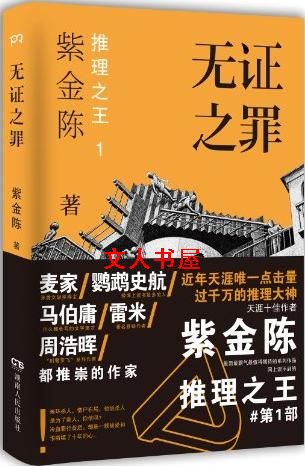欲加之罪-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家四口在半睡半醒之间,匆匆忙忙地奔出屋子,只见院子里白烟弥漫,搞不清究竟哪里是起火点。
这时,风向改变,一阵晨风将白烟吹向另一边,四人这才看见浓烟的源头就在厨房的后方,小木屋的方向。
四人相视一眼,便前往一探究竟,邱逸萍边走边说:“那不是防火建材吗?难道宗霖表哥和建商勾结,骗取普通建材和防火建材之间的高额差价?若是如此,等他从欧洲游学回来,我一定不饶他。”
当四人到达起火点一看,个个都傻了眼!
梅映雪看见四人都已起床且一起到来,立刻慌乱地站起,解释着说:“你们都起来啦?对不起,因为这些柴不怎么干燥,所以不容易点燃,不过只要再等一会就好了,我马上去淘米煮稀饭——”
“等……等一下。”吕淑雯一眼就认出那些糊灶的白色卵石很眼熟,下意识朝她的宝贝鲤鱼池看去,果然看见她亲自堆砌的池围边已缺了一角,不由脑中一阵晕眩。“天哪!我的宝贝……”但旋即又喃喃语:“没事、没事,鱼应该还好好地活着,还活着……”
在同一时间,邱政铭也发现他最照顾的猫柳树已成了秃枝,虽心疼已极,但看见梅映雪娇颜煞白,一脸不知所措的神情,便不敢把心疼表现在脸上。
邱舜翔则拾起散落地上的几页A4纸张。
这……不是他最重要的研讨会报告书吗?转眸瞄向那灶口的纸张灰烬,又睇了眼面色苍白、神情惊慌的她,只得抿紧双唇,暗暗自我安慰:没关系的,反正有存档,再印就有了,只是上头修改过的东西得再重新来一次就是了。怪不了人,谁教他要把报告书乱摆呢?
丘逸萍看见那架在灶上被熏得乌黑的陶铜时,本能地惊呼出声——
“啊——我的暑假作业!”片刻却又自我安慰:“不要慌张,没有破,只要洗一洗就干净了。”
虽然丘政铭和丘舜翔没有惊呼出声,但心眼剔透的梅映雪怎会看不出父子两人似在强忍心疼,她心知自己的一番好意已闯下了大祸,真不知该如何向四人道歉求原谅,因而急得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
这时,一阵阵高亢刺耳的笛呜声快速地由远而近,最后在墙外停住,只见几条人影迅速地翻墙进来,拉着一条长管子飞快地往这方向跑来。
“有人报案,说你们这里失火了,请问起火点在什——”
第一个拉着消防水管到达的消防人员,看见有几个人站在浓烟前,便开口询问,待看见真实的情况,下面的话只得倏然打住。
犹穿著睡衣的一家人,还在心疼所有重要对象遭毁的心情下,面对前来灭火的消防人员,却只能露出无比尴尬的苦笑。
一向机灵的丘逸萍,抬手抓抓后脑的短发,面露尴尬的微笑说:“呃,对不起,我们正在进行野炊,结果……情况好象有那么一点点的失控了,呵呵……”
随后赶来的消防人员不由彼此互视,一脸啼笑皆非。干了这么久的打火急先锋,也不是没碰过乌龙事件,但就属今天这件最为乌龙。
小队长无奈地摇摇头,上甫看看这奇怪的一家人,便好言规劝说:“你们在自家的院子野炊并不是什么坏事,不过还是请你们注意一下,免得造成邻居的恐慌。”而且还是一大早……
“是、是,我们保证不会再做这种事了,实在非常地抱歉。”丘逸萍猛向消防人员道歉。
既然只是一场乌龙事件,消防人员便收队走人了。
这时,四人才同时松了口气,丘逸萍看着双亲和兄长。
“幸好没有惊动那些好事的记者,否则一定成为头条,晚报我们就可以看见斗大的新闻标题写着:法国某精品服饰台湾总代理公司董事长吕XX女士、某市立国民中学校长邱XX先生,某大学农业经济学系讲师邱XX,清晨家中失火,查明原因之后,原来只是乌龙记一场。哈哈……”末了还哈哈大笑两声。
她嘴巴说得轻松有趣,三人却是捏了把冷汗,若真让这乌龙事件上报,保证家中的电话会成天响个不停。
愧疚不已又不知如何是好的梅映雪,含泪上前低声道歉。“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本来只是想为大家煮早饭的,可是厨房里找不到灶,我只好在外面做一个简单的,没想到却……对不起……”
邱政铭和吕淑雯相视一眼,无奈一笑。邱政铭抬手轻抚她头顶,慈爱地说:“这不是你的错,你也是一番好意啊,别再自责了。”
邱逸萍接口说:“是啊,现在最重要的是赶快湮灭乌龙证据。”
于是,五个人便开始动手恢复原状,当这一切只是黎明前一场不可思议的梦境。
早上,吃过早餐,丘逸萍在屋后的水龙头下,用软布沾洗洁剂,刷洗陶锅上的熏烟。
一旁,梅映雪低着头,依旧对一大清早惹的祸愧疚不已。
邱逸萍看她一眼。“你不要再自责了,我们都知道你是一番好意,是我们没把生活习惯详尽告知。”
虽然她这么说,但梅映雪依然无法释怀。
丘逸萍再睨她一眼,迳自把洗好的陶锅放到一旁阴干,起身说:“我现在要去我的工作室,你要不要一起来?”
梅映雪下意识朝客厅看了眼,虽想进去向丘舜翔道歉,却又怕被他所讨厌,意念运转间,心想还是跟着丘逸萍似乎比较妥当,便起身跟着她往花园的另一头走去。
丘逸萍领着她,穿过花园小径,来到位于庭院较空旷处的一间木造小屋前,小屋用数根巨木桩垫高,门前有台阶,屋前的廊下有盆开着数朵紫色莲花的盆栽,清澈的水中可见数尾小鱼在游动着。
梅映雪只觉得这盆栽美极了。
“那是我爸种的,为了怕病媒蚊在里头繁殖,还特地放了几只小鱼进去吃孑孓。”
丘逸萍用钥匙打开小屋的门,推开大门举目所见都是动物花草、还有人像等等的雕刻品,个个栩栩如生,有的色彩璀璨亮丽、有的朴实无华,上前细看才知这些全是陶制品,可见其做工之精巧;架上还有好些呈砖红色的素烧,另一旁置有电窑、手拉胚机和一张大型工作台,以及各式各样的工具。
丘逸萍看着这间她最引以为傲的工作室。“这工作室是我老妈为我建造的,我常在想,我今生能生而为我母亲的女儿,肯定是前三辈子修来的福气;也或许是她从小在重男轻女的环境下长大,所以她不要她的女儿也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邱逸萍转身望向外头占地千坪的庭院、屋宇。“你觉得我家够不够大?”
梅映雪点头。
“这全是我妈妈的,不管是房子、土地,包括那辆白色的宾土车,全是我妈妈的财产。”
梅映雪不可思议地看着她,印象中有财产的都是家里的“爷”字辈才对,女人的东西最值钱的大概只有首饰而已。
丘逸萍看着她笑笑说:“虽然我爸也是‘长’字辈的中学校长,可是和我妈妈的董事长相比,年收入可是相差好几十倍呢。如果今天我爸也同你的相公一样搞外遇,一无所有被扫地出门的一定是我老爸。”
梅映雪不可置信地看着她,光看外表实在看不出吕淑雯有那么厉害。对了,她说她的相公搞外遇,外遇又是什么东西?不觉就问:“你说我相公有‘外遇’,请问那是什东西?”
“喔,意思就是他在外面有别的女人,简而言之就是金屋藏娇啦,而且对方一定是个比你更有利用价值的女人。”
梅映雪听了不禁骇然,遂问:“你为什会这么认为?”
“这其实很容易理解的,让我来逐一分析给你听。”邱逸萍拉来两张椅子,给她和自己坐。“这个婚姻从头到尾,你都是只受摆布而不自知的棋子,为什么你的后母要趁你爹不在的时候,赶快把你嫁给一个胸无大志又好赌的穷书生呢?我想她八成是怕你和她儿子分家产。一旦拜堂成亲,生米煮成了熟饭,就算父母看走了眼,让你嫁错了郎,只消一句‘这是你的命,你就认命吧,谁教你的生辰八字不够好呢’,就可撇得一干二净。”
梅映雪听了,惊愕得两眼圆睁。
“至于杜家为何要和媒婆联手欺瞒门不当、户不对的事,那是因为你的相公想靠你发达富贵呀!你想想,你爹爹那么疼爱你,一定会不忍心看你在夫家被穷困所迫,要让你脱离穷困的方法,不是直接给你钱财和好处,那只怕屈辱了女婿的颜面,反而对你变本加厉,所以就改而给你相公好处,好间接让你脱离苦日子,你婆婆图的就这个。”
听完这话,呆愣的梅映雪只感到心房一阵阵的冷意翻腾。的确,婆婆是在有意无意间,向她询问过娘家布庄经营的状况,还常以闲话家常的语气暗示她说,相公其实挺有做生意的才干,只是没机会罢了。
丘逸萍见她发楞,心想她大概也想起了些迹象,虽然揭开表象是残酷的事实,但不这幺做的话,她大概也难以了解,她之所以会以七出之罪被休,并非是她的错。她想帮助她重新在这个新世界建立自信心。
“说句残酷而实在的话,不管你对夫家如何地尽心尽力,甚至奉献、牺牲自己,他们也都视为理所当然而已。反之,你只要稍有懈怠,没有第二个想法,就是你懒惰、不尽妻子和媳妇的本分,甚至像你相公一样,罗织不孝罪名,堂而皇之地赶你出门。”
邱逸萍这话真是说到了她的痛心处,梅映雪只能低头不语,不争气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再说,你婆婆既然从未说过你是个不孝的媳妇,为什么你的相公要休离你的时候,她一句为你说情的话也没有?”
双目早已泪水盈眶的梅映雪,本能地抬首追问:“为什么?”
丘逸萍看着她说:“我想她是早已知道内情的了,只是帮着儿子对你隐瞒而已。在很多父母的心目中,女儿将来是要拨出去的水,成为别人家的媳妇,注定永远不是自家的人;在公婆的心目中,媳妇总是别人家的女儿,不是自己的亲骨肉,儿子才是自己的人,当然是一切以儿子的利益为重,所以当女儿成为媳妇的那一天起,就已经‘里外不是人’了,待熬到成为婆的那一天,你就会不自觉把婆婆曾加诸在你身上的那一套,一样不漏地用在另一个女人媳妇的身上,世世代代的女子就在这种无奈的循环下被束缚了。”
震撼!实在太令她震撼了!这是梅映雪从未想过、也没听过的事,原来所谓天经地义的事,却是一张牢不可破的人为枷锁。
当思路渐渐清明时,梅映雪已能稍稍明白,那就是女人一生的宿命。自幼即被灌输要乖顺听话,稍长尚在懵懂之时,即出嫁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媳,在婆婆的指导下学习如何持家、照顾丈夫、养育孩子,遵循社会期待,教导女儿如何成为他人的好儿媳,训练娶进门的媳妇如何遵循夫家的生活规则……
梅映雪呆愕地看着地板,好半晌还无法回神,转首看着丘逸萍,眸中净是无比崇拜。
“逸萍,你好厉害,你说的这些都是我以前未曾深思过的事,那些我本来以为天经地义的事,原来是那么地不公平。”语毕,她神情一黯又说:“就像我,尽心尽力地操持着家务,却得不到丈夫的感谢和疼惜;不让我知道原委,轻易地就用七出之罪,把我休离……”
“可是啊——”邱逸萍虽然知道自己有幸出生在这个女权逐渐被重视的年代,可是仍不免感慨地说:“你别看我们这个时代,女性好象有很大的自主性,但还是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智商高的女子陷在传统性别既定的迷思中的。”
“哦?”她不解。
丘逸萍将头往后仰,无声地叹口气。“犹记得一位政治名女人说过一句,听似矛盾却是至实不过的话——‘女人最大的敌人还是女人’。为什么呢?‘沙文主义’的受益者或许是男人,但执行者却绝对是女人,因为一直以来女人比男人更不厌其烦、更严厉地打压着女人;可悲的是,这群女人不但毫无自觉,甚至还坚信她们维护的是‘正义真理’,殊不知这群‘婆婆妈妈们’就是迫使数千年来中国女性无法翻身的元凶。”话落不禁重叹一口气,心里有着深深的无力感。
梅映雪看着先前傲睨万物、气概不让须眉的她,对女子从古至今的处境,似乎也有着深深的无力感和无奈感。
当晚就寝前,梅映雪覆着薄被,抱膝坐在床上,脑中不停地想着今天上午丘逸萍对她说的话。
邱舜翔换过睡衣从浴室里出来,看见似在苦思的她,遂轻问:“怎么了?有什幺烦心事吗?”
梅映雪从沉思中回神,转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