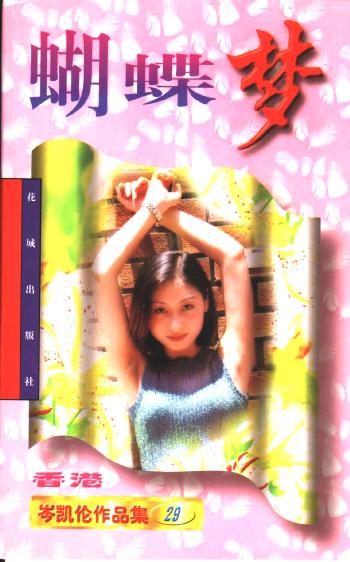蝶梦-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要从昨日讲起了。京兆府抓了一名犯人,因他人面兽心,为了独占家产竟谋死生身父亲。这样肮脏的事情,君子自然不齿,但对于酒楼中那些称不上高雅的闲人们,倒真是喜闻乐见,抓住这题目大谈特谈。认识那犯罪者的,一开始慨叹,‘以前没看出他如此毒辣’,立刻有人反驳,‘这人品质低劣,从他终日流连风月场所,便可见端倪’。于是,一名同样酷爱寻花问柳的公子哥儿,讲述起在青楼与他偶遇时的情形。这么一来,话题可就转到了娼馆去,不多时已在探讨长安哪些名士是那边的常客。似乎有人提说,您与落花居的花魁牡丹姑娘交情匪浅……”
“所以,你便以为,这位牡丹姑娘,迟早会踏进我封家大门?”封乘云无聊地摇头,“这真是从何说起啊?不错,我确实常到那落花居去,却不是为了私情,只是一般的应酬而已。人常称我为‘儒商’,但并不是每一个和我做生意的,都读过圣贤书。一位大主顾,千里迢迢跑来长安,要与我谈一笔买卖,人家就想见识见识花红柳绿的地方,我又能怎样?至于每次都要牡丹姑娘接待,也是因为她艳名远播。名头越响,要价越高,越能表示我待客的盛情,场面上也更过得去。再说,那种地方不许外来女子入内,离馆主当然没有涉足过,难免有些误会。怎么说?并不是走进那扇门,就一定要找人侍寝。何况,落花居还是较为高级的,招待的多是文人墨客。在那里,通常只能喝酒吃菜、欣赏歌舞,里面的姑娘都是卖艺不卖身。我敢说,虽然在那里出没的时间不短,但绝没有作出对不起玉蝶的事来。”
“我自然相信您的人品。”离春点头道,“不过,这些事情,如果传到大理寺官差的耳朵里,只怕不大好办。为了保险起见,我认为您应该自己向他们坦白。”
“这,”封乘云错愕,“他们查的是玉蝶之死,我看不出这两件事情有何关联。”
“死者是您的妻子,而您在外面又与红颜纠缠,情势对您不利啊。”
“馆主多虑了。”封乘云淡淡一笑,毫不在意,“他们还能疑我杀妻另娶不成?别说我与牡丹姑娘清白无虞,就算真有瓜葛,只须知会玉蝶一声,封府里便可多一个二姨太了。男子三妻四妾,天经地义,妻子在世,也可以广纳姬妾,又何必害死她?再说,我并无意采撷几朵野花回家,只愿能与玉蝶一人长相厮守,举案齐眉。怎奈天不遂人愿……”
说着,眉毛又沉重地往眼睛上压下,脸颊的轮廓也显得益加脆弱。离春急忙安慰:
“您别又想起伤心事了。我就是不忍您在这样难过的时候,还要被官家人骚扰,这才好言提醒的。大理寺前些日子找乱神馆的麻烦,那位杜大人的难缠,”深深叹息,用力摇头,“我可是见识过了。劝您千万不要重蹈我的覆辙啊!”
“可我听说,杜大人他是个断案奇才,不像不明事理的人。”
“正因为他太过明理了,性子才多疑啊。本想举几次我遇到的刁难为例,但前因后果牵扯太多,说了怕您听不明白,索性就说您家的事。他若在这里,听说您反对抓红翎回来,而这名女子又很可能就是凶徒,他便会认为您是有意包庇。”
“哎呀!这可真冤枉了!”
“他一定会厉声质问您,”离春的声音变得严峻,“‘你为何坚信,红翎不是凶手?难道,在你心目中,行凶者另有其人?’”
可能是腔调太像,封乘云真像上了公堂般惶恐起来:
“不,不是。这,这可叫我怎么说?”
离春幽然一笑:
“您不必紧张。我只是个巫婆,又不是审案子的。”
封乘云一楞,随即笑开:
“真有官老爷这样问我,我也只能支吾了。因为我明白,我的解释即使说了,他们也是不信。但若是馆主你,倒可能解我心意。”
“不妨说来听听。”
“那日早上,我见到玉蝶陈尸井边,顿觉天地之间一片昏暗。一群官差在我眼前来来去去,却仿佛离我很远。不知不觉间,我好像走起来,也不知要往哪个方向去,只是随便迈着步子。等我稍微清醒,发现自己已在刚才那间卧房中了。我躺上床,瞪着帐顶,很奇异地并不伤心,只是不知所措。也不知过了多久,我忽然看见了玉蝶!当时真是欣喜:谁说她仙游去了?这不是还在眼前?她慢慢走来,我伸手去迎时,却掉到了床下,方知是南柯一梦。这时,终于隐约体会到——我妻子她真的离我而去了。思及此,立时从心底冲上一股愤恨,浑身颤抖,极想砸坏什么东西,甚至是自己。”封乘云两眼发直,瞪着自己手掌,状似疯狂,“到底是谁害了你?是谁害了你?红翎,是!一定是她!”
一直默立一旁的红羽,看得心惊,上前畏缩地伸手阻拦,却被一掌挥开。离春断喝一声“封、乘、云!”,这才震回他的神智,茫然望着身边两名女子,随后扭过脸去:
“抱歉,失态了。没吓到你们吧?”
离春毫不在意:
“我的胆子,倒没那么容易破的。倒是刚才直呼老爷名讳,失了礼数。”
“事急从权,不碍的。”自嘲笑笑,稍稍转过身子,“其实那一日,我的狂态还犹有过之呢,一心只想着怎么把红翎抓回来剥皮拆骨。就这样一直发疯,折腾到累极,才又睡去。这一次又梦见玉蝶了,却不是向我走来,而是背对着我,任我怎么叫,她也不应声,似乎在与我生气。醒来后懵懂不解,直至忆起一件旧事,恍然大悟。”
“旧事?”离春的眼睛,黑得深湛。
“那是玉蝶还待字闺中时。她有一名贴身丫鬟,自幼父母双亡,被卖到她家为奴。由于事主忠心,又聪明伶俐,让玉蝶的父亲收为义女。就这样,主仆二人一起长大,情同姐妹。后来,在我追求未来妻子时,这丫头突然找到我,说了些在我听来很不着边际的话。我随口敷衍两句,想她就此作罢。谁知她见我不放在心上,竟翻来覆去,讲个不停。我急起来,就训斥了她。结果为了这个干妹妹,玉蝶可跟我赌了很久的气。”
“夫人还真是护短呢。”
“是啊。记起她那时的背影,与梦中见到的,竟出奇相似。想到这里,灵光一闪,觉得这两件事简直雷同!一样是贴身丫鬟,一样的身世坎坷,一样受玉蝶疼爱。以前责备了那个兰儿,被玉蝶冷漠相待;而现今我疑心红翎是凶徒,她便以同样姿态在我梦中现身……”
“您认为是夫人托梦,要您别冤枉了好人?”
“正是!”封乘云坚定点头,言语间透出欣慰,“我早说离馆主能懂得的。”
“所以,您肯定红翎没有杀人?”
“玉蝶这样暗示,自然不会有错。红翎既然是无辜的,离开封府就必有她的道理。再说,又没有真的签下卖身契,人家不愿意留在这里做事了,还找回来干什么?”
这一句说得万念俱灰,仿佛再无精力理会这些琐事。
“您有没有想过,夫人如果不是红翎害死的,那到底是谁下的毒手?”
“我怎么没想过?只是心中一片混乱,不知该怎样去思考,只好反复回忆那晚的情形。可我左思右想,都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难道,您就不曾怀疑,这家里的人?”
“可家里又没有别人。当时呆在这府里的,除了我一家三口,不算红翎,就只剩下管事、红羽、莫成三名下人了。你说我能怀疑哪个?玉蝶生前心肠好,对底下的人一向和颜悦色;现在去了,不也还护着红翎?我是怕,胡乱怀疑了一人,当晚睡下后,她又在梦里摆背影给我看啊。”
封乘云抽嗒一声,语气更加惨切:
“现在想见到她,也唯有午夜梦回时了。我还想多看看她的脸呀。除非能在余下三仆人中,找到一个不受玉蝶庇佑的,否则,我是不敢妄动疑心了。”
这一段,红羽在旁边听得流下泪来,背过身去,牵着衣袖擦拭双颊。离春哈着腰,好像愈加愧疚:
“看我这人,怎么不长记性,一错再错,竟又惹您伤心了。”说着抬起头来,拙劣地想岔开话题,于是故作愕然,“等等,什么时候说起这些的?这完全挨不上啊。”
封乘云也是一阵怔愣:
“是啊,方才还在说什么闲言、青楼,怎么不知不觉间离题万里?”
“一句赶一句,就说到这儿了。”
两人相视苦笑。 离春正色说:
“还是言归正传吧。今日求见,其实是想了解,您与夫人是怎样互许终生的。若您不介意,可否说与我知道?”
“这和招魂有关?”
“不错,大有干系。”
封乘云沉吟片刻:
“方才听馆主的气血论,讲得头头是道,可见对阴阳两界之事极为在行。既然你说招来玉蝶魂魄,需要我吐露当年之事,那我岂能隐瞒?”
说着眼神远眺而去,寻不着一个落点,脸上微微泛起凄迷的笑容:
“在我们成婚之前,我称玉蝶为‘表妹’。我娘是她爹的亲妹子,她的姑母。幼时我曾见过她,粉妆玉琢的,煞是可爱……”
离春听得动容,眼中悄悄闪着泪光:
“表兄妹,确是容易走到一起。您刚才这几句话,倒让我想起一首诗,正与这情境吻合。”
“不知馆主说的,是哪一首?不妨吟出来我听。”
“只是用嘴来念,未免少了味道。”
离春摇头,走到书案后,眼神在案上扫来扫去。
红羽早已擦干泪水,现在听话听音,知道她的意思是要写出来,急忙跑上前把纸铺好。待要磨墨时,离春一摆手,从那“阴阳扇”的长柄上,拔下一节竹管,往砚中倾倒,一缕墨汁徐徐流出。不多时插回原处,又拧下另外一节,竟然是一杆毛笔。
封乘云赞道:
“馆主的构思,倒真奇巧!这东西也带得齐全。”
“有备无患而已。”
离春持笔掭上黑墨,在纸上书写。刚写完“郎骑”二字,封乘云便已诵出整句: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您也读过这诗?”
“李太白的新作《长干行》,谁人不知啊?刚开始流传时,无数人争相传抄。许多读书人,都以与他活在同一时代为荣。他真是当今最伟大的诗人,他的诗作,千秋万代之后,也必定被人奉为经典,永世不朽。”
“您这般推崇的文人,定是不俗的。可惜我对此人了解尚少,他的诗作也读得不多,到底是才疏学浅啊,比不上您的见地。刚才引用这句,也只是觉得,‘青梅竹马’四字,简直就是您与夫人当年的写照。”
封乘云抬起眼来,温柔笑道:
“我的确见过儿时的她,却并非一起长大。那一次,舅舅来看望我娘亲,顺便带了她。自那一别后,虽同在闽南,但阴错阳差,再也未曾见了,直至我长大成人。某日,母亲突然害了一场大病,险些驾鹤西归。最后虽是救了过来,她却心有余悸,担心什么时候双眼一闭,竟来不及见至亲之人最后一面。就这么,越想越是后怕,恨起平日疏于联络,对自家兄长也更添思念。于是,我便护着双亲,举家去探望舅舅。那一次,我才又见到她。”
离春轻柔一笑:
“赫然发现,昔日那小姑娘,竟已出落得婷婷玉立,貌美如花?”
封乘云眼角噙泪,脉脉点头。
“那时,实在惊讶,却也喜出望外。舅舅见了他妹子,惊喜之情更是溢于言表,盛情邀请我们多盘桓几日。我父母欣然同意,一家人便留下来作客。”
“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离春再度写下诗句,抬眼道,“既已近水楼台,您就没有动作?”
“离馆主知道,我大唐风气开化,仰慕上一名女子,继而想求她为妻,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与玉蝶重逢的那一眼间,便已心动;安顿下来,急忙贿赂了下人,打听她脾性如何,有何喜好,闺房何在等等。得知她每日会到花园一游,就算准时间,在必经之路上守候。‘表兄表妹’地熟络几日,我见她对我也颇有好感,便作了一首情诗,想借此表明心迹。可惜,花园之行,她身边总有那个兰儿陪伴,简直寸步不离。多一人在场,想暗渡陈仓,把诗稿递到她手里,便不容易了。那诗在手心攥了几日,始终送不出去,只得另想办法。我已知道,她的住处离我所居院落不算遥远,只是……唉!还是那兰儿,她对我虽并不厌恶,但对她家小姐却是万般回护,让我怎样也觑不到机会。又拖了些时候,我瞧见一名长工模样的男子,经常出入她的居所,才想起玉蝶喜爱侍弄花草,但搬运盆栽这些粗重活计,自己作不来,又不忍劳累如亲姊妹般的贴身丫鬟,只有另找人做。我一见有机可乘,立时去收买那小哥,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