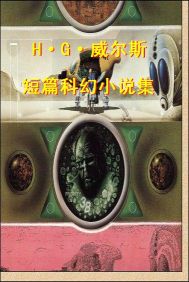外国中短篇科幻小说1000篇 (第九辑)-第4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马克西一语不发。
“你相信英雄那套说法吗?”他问。他重新在烂泥里躺下。此时,黑暗已笼罩了四周,星星不见了,又湿又冷的感觉消失了。“你认为我们会成为英雄吗?”
马克西笑了。他的嘴巴在半张苍白的脸上就像一个松弛的黑洞。“扯淡!”他大笑起来。
《我握着父亲的爪子》作者:'美' 戴维·D·莱文
接待员本来长眉毛的地方是一丛羽毛。羽毛混杂着绿、蓝、黑三色,就像孔雀羽毛那样色彩斑斓,而且它们在空调的静静微风中轻柔地颤动着。
“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想问,先生?”
“没有。”詹森回答着举起手中的杂志,但在同一篇文章读了三遍却记不得一个字后,他又把它放下了,“实际上,我是有个问题。嗯,我想问你……啊……你,你是否正在转变?”他的问话像片纸样落在候诊室那修剪考究的柔软草地毯上,詹森希望自己能把它收回,装进口袋,然后离开。只是离开,再也不回来了。
“噢,你是指眉毛?没有,先生,我没有做转变,这样的眉毛只是时尚。我很高兴做个人类。”她温和地对他微笑着,“你很久没来旧金山,对吗?”
“对,我今天早上刚到。”
“羽毛在这儿很流行。事实上,这个月我们有做特价。你想看看产品小册子吗?”
“不!啊,我是说,不用了,谢谢。”他低下头,发现手中的杂志已经被弄皱了。他笨拙地想抚平它,但随后放弃了努力,把它塞回咖啡桌上的杂志堆里。这些杂志都是最新一期的,咖啡桌看着像是实木的。他用肮脏的拇指甲检查着:真的是实木的。然后,被自己的行为吓坏了,他把那一堆杂志挪过来盖住那条小刮痕。
“先生?”
接待员的声音让詹森惊跳起来,把杂志滑曳了一桌子。“什么?”
“您是否介意我给您提一个善意的小建议?”
“啊,我……不介意。请说吧。”她可能会告诉他:他的纽扣儿开了,或许在这种场合必须打领带。她自己的领带同墙上的壁布很相衬,一种栗色和金色的豪华印染品。詹森怀疑自己那已经褪色的工作服上衣领口甚至能否围着他那粗脖子。
“你不该问任何我们的病人他们是否正在转变。”
“那不礼貌?”他想钻桌子,死了算了。
“不是的,先生。”她再次微笑着,这次带有真正的幽默意味,“只是他们中有些会喋喋不休,就最微不足道的东西给你做展示。”
“我,噢……谢谢你。” 钟声响起——那是个持续时间很短的嘹亮声音,同候诊室的古典音乐混杂在一起,一点也不突兀——接待员瞪了一会儿虚无处。“我会告诉他的,”然后她对着空中说,接着把注意力转回詹森身上,“卡梅尔可先生出手术室了。”
“谢谢。”听到一个罕见的名字让其他人叫出来太陌生了。二十多年里他都没见过另一个卡梅尔可。
半小时后,候诊室的门打开了,露出一个走廊,走廊的地板光滑、锃亮,墙壁是精良的米白色。尽管布置很新颖,而且无疑——那古典音一直继续着,但微弱的消毒剂味道还是提醒詹森自己是在哪儿。一个穿护士服的年轻男人领詹森扇标有劳伦斯·施泰格医生的门前。
“你好,卡梅尔可先生,”桌子后面的人打招呼,“我是施泰格医生。”医生比詹森瘦小,色的眼睛,蓄着整洁的斑白胡须。他的手,就像的声音,有力而粗糙;他的领带以外科医生的精确打着结。“请坐下。”
詹森倚坐在椅子边,不想屈从于它的豪华。不想太舒适。“我父亲怎么样了?”
“手术很成功,他很快就会醒过来。不过我想先同你谈谈。我相信你们之间有些……家庭内部矛盾。”
“什么让你会这么说?”
医生瞪着他那金制的个人信息管理器,一直重复着啪嗒打开再关上。“我为你父亲治疗了近两年,卡梅尔可先生。医生和病人在这种合作关系中,必须是相当亲密的。我觉得我已经相当了解他了。”他抬眼看着詹森的眼睛,“他从未提及你。”
“对此我并不吃惊。”詹林能听出自己声音里的苦涩。
“我病人的家庭不愿承认他们是相当平常的。”
詹森猛然、唐突的笑声让他们俩都很震惊。“这和他做转变没什么关系,施泰格医生,我父亲在我九岁时就离开了我和我母亲。从那时起,我就没同他说过话。一次也没有。”
“我很抱歉,卡梅尔可先生。”他似乎很真诚,不过詹森怀疑那是否只是医生对病人的职业态度。医生张嘴想说什么,然后却闭上,瞪着角落一会儿。
“这可能不是家庭重聚的最佳时机,”他最后说,“他的情况可能有一点……一点让人吃惊。”
“我从克利夫兰走这么远的路来,不是想仅仅转身回家。我想同我父亲谈谈。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是吗?”
“最后的手术安排在五周后。当然,也可能被推迟。但是所有的文件都已经签署好了。”医生把手平放在桌子上,“你不是想劝他改变主意吧。”
“我只是想看看他。”
“如果他想见你……我会让你见他的。”
对此,詹森没有再说什么。詹森进去时,他父亲侧躺着,脸背对着门。这儿消毒剂的味道更浓些,仪器的电池发出哔啪哔啪声。
他的头秃了,头后面只在边上长着些泛白的头发。头皮光滑、粉红、锃亮,而且非常圆——同詹森自己的圆头相同,詹森的头就他工作服配置的标准安全帽来说,太大了。他自己的头盔里用黑颜料在黄塑胶安全帽里写着“大头杰斯”。
尽管他父亲的头很大很圆,但随他呼吸颤动的肩膀却很窄小,他胸下很快就是臀部,臀部仍很窄小。看不见腿,那位于他身体前面。当他走向床边时,詹森吞咽着唾沫。
他父亲的圆脸是褐色的,脸上很粗糙。从他鼻子到两个嘴角有深深的褶皱,他紧闭眼睛上的眉毛灰白而且很浓密。这张脸比他想象中的年老些,那想象只是在二十年前一个旧记忆上加上二十年的时光流逝而已。
詹森目光下滑,滑过他父亲那刚刚刮过的下巴,滑到他脖子上那浓密的灰白色颈毛上。然后向下更远,是他平放在床上的灰白色毛腿,脚爪在踝骨处交叉,放松地放着,趾甲干净整洁,趾肉没有任何磨损。
他父亲的身体像狼或者是獒,宽大、强壮、充满肌肉。但不知怎的,有些不对:他的胸膛,尽管很窄,却仍比任何正常的狗要宽,他的皮毛像是赝品——太干净、太精致、太齐整。自飞机上读的资料詹森知道那是从他父亲自己的头发,经过工程技术处理制成的,只是近似于真正狗那毛层不同、毛种类也不同的自然皮毛。
他是一只华美的动物。他是个可悲的畸形人。他是生物工程的奇迹。他是自大的自我放纵者们的偶像。他是一只狗。
他是詹森的父亲。
“爸爸?是我,詹森。”他身体的一部分想去抚摸那满是毛的肩膀,但他管住了自己的手。
他父亲的眼睛张开了,但接着又闭上了。“是吗?医生告诉我了。”他的发音有一点儿含糊,“你到底来这干什么?”
“我在奥黑尔机场撞上了布列塔尼姑妈。我不认识她,但她立刻认出了我。她告诉我关于……你的一切。我直接就来这儿了。”
他是我父亲,他在电话里告诉他老板:他住院了。我得在一切太晚前去看看他。
他父亲的鼻子嫌恶地皱着:“永远不能相信她。”
“爸爸……为什么?”他再次张开眼。它们像詹森的眼睛一样是深蓝色的,它们开始完全聚焦。“因为我能。因为宪……宪法赋予我对自己身体和金钱随心所欲的权力。因为我想在余生中放纵一下。”他闭上眼,手爪交叉捂在鼻梁处。“因为我不想再做任何该死的决定。”
詹森的嘴张开,又像条鱼样合上。“可是爸爸……”
“卡梅尔可先生?”詹森抬起头,他父亲转过头去,看到施泰格医生站在门口。詹森不知道他已经站在那儿多久了。“对不起,我喊的是詹森。”詹森的父亲再次把手爪捂在脸上。“卡梅尔可先生,我想你该让你父亲单独呆会儿。麻醉剂还没有失效。上午,他或许更能畅开来谈。”
“想都别想。”声音传自交叉的手爪下。詹森手伸出——想抚摸一下父亲的前额,或者揉揉他的皮毛,但他不确定为什么——随后手又缩了回来。他说:“明天见,爸爸。”
没有回答。
当身后的门一关上,詹森沉重地倚着墙,然后下滑着坐在地上。他觉得眼睛刺痛,他揉着它们。
“我很抱歉。”詹森睁开眼睛看着发出声音的地方。施泰格医生蹲在他面前,手里举着一个带夹子的写字板,“他通常并不这样。”
“我从不了解他,”詹森摇着头说,“从他离开后一直就不理解。我们生活得很幸福。他不喝酒,也没有别的不良嗜好。也不是钱的问题——总之,那时不是因为钱的问题。妈妈爱他,我爱他。但他说‘这儿对我没什么重要的’,然后就走出了我们的生活。”
“你提到钱,是因为那吗?你知道他给慈善机构捐了很多钱。剩下的仅足以支付颅面手术,一个信托基金为他支付手术后的微小需要。”
“不是钱,从不是钱的问题。他甚至要支付离婚后的赡养费及孩子的抚养费,但妈妈不肯要。那并不是很现实的决定,但她真的不想再用他的任何东西。我想那是因爱生恨。”
“你妈妈知道你来这儿吗?”
“她八年前已经去世了。白血病。他甚至没有参加葬礼。”
“我很抱歉!”医生再次说。他也坐下,把他那带夹子的写字板咔哒一声放到他旁边那闪光锃亮的地板上。他们一起安静地坐了一会儿。医生说:“让我今晚同他谈谈,卡梅尔可先生,我们明天早上再看事情会怎么样。好吗?”
詹森想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好吧。”
他们互相扶着站起来。
第二天早上,詹森的父亲轻轻推开医生办公室的门,他那柔软的新身体随着平稳的四腿步伐来回动着,轻松地跳上一个铺有地毯的平台。在上面,他的头可以与詹森和医生的处于同一水平面。但他拒绝与詹森眼睛对视。詹森自己坐在医生的椅子上,但仍感觉不太舒服。
“诺亚,”施泰格医生对詹森的父亲说,“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困难,但我想让你明白,那对你儿子甚至更困难。”
“他本来就不该来这儿。”他回答,但仍不去看詹森。
“爸爸……我怎么可能不来?你是我唯一的家人了,我甚至不知道你是死了还是活着,而现在……却是这样!我不得不来。即使我无法让你改变主意,我……我只想同你谈谈。”
“那么,谈吧!”最终他的脸转向了詹森,但他的蓝眼睛很冷淡,嘴巴紧闭,“我还能听。”他把头放低到趴在身前铺有地毯平面的脚爪上。
詹森觉得自己腿上的肌肉在绷紧。他可以站起来,走出去……不再面对这种尴尬和痛苦。他可以回到自己那寂寞的小屋去,努力忘掉关于父亲的一切。
但他知道有这最后一次相聚机会真好。
“我告诉他们你死了,”他说,“我学校的朋友们。是我们搬去克利夫兰后新学校的朋友们。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说。许多他们的父母也是离婚的,他们会理解的。但不知为什么假装你已经死了会让情况容易些。”
他父亲猛地闭上眼睛,眼和额中间显现出深深的皱纹。“我不能说我怪你这样说。”他最后说。
“无论我对多少人撒谎,但我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我一直想知道你在干什么。你是否会想我,你都去过哪儿了?”
“布法罗(美国纽约西部一城市)。”
詹森一直等着直到确定不会再有更多的详细说明才问:“你这些年一直呆在那儿?”
“不是,我只在那儿呆几个月。然后去了锡拉库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部一城市)。也在迈阿密呆了一阵子。我没有在那儿长时间定居下来。但最后的十一年我一直呆在加州湾区。”他抬起头,“为诺曼提可销售外形控制软件。那是真正让人激动的东西。”
詹森不在乎他父亲干什么,不过他感觉这是个好机会:“给我讲讲那吧。”
他们谈了半个小时的外形控制、源码控制以及员工的认股特权——都是些詹森不理解也不想理解的东西。但他们一直维持着交谈。他甚至设法让这个话题看起来很有趣。当他意识到自己是在听一条狗做销售介绍,詹森的嘴上泛出扭曲的傻笑——条长着他父亲头的狗。
詹森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