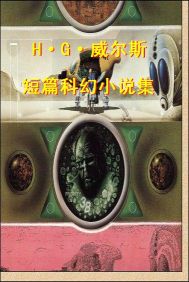外国中短篇科幻小说1000篇 (第九辑)-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把手伸向她的肩膀,摸到了她衬衣的布料,我的手沿着她的身体侧面摸下去。摸到长裤时,布料的质地改变了,可她的肉体并没有裸露在外。我知道,自己没有产生幻觉。幻觉发生在剧痛之后,比如现在。不是之前。
“你会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吗?”我问道。
“你跌倒了。”
“别跟我装傻,”我说,“这么聪明漂亮的人不适合装傻。快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试着歇会儿,”她说,“我们以后再谈。”
“你昨天跟我说不会对我撒谎。你说的是真话吗?”
“我永远不会对你说谎的,格莱。”
我盯着她的脸看了很久,然后说:“你是人类吗?”
“目前是的。”
“这到底算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是我需要做的东西,”她说,“你需要我做的。”
“那不算回答。”
“我是在说,我现在是人类,我是你需要的一切。那还不够吗?”
“你是个变形体吗?”我问道。
“不,格莱,我不是的。”
“那你为什么看起来能这样?”
“这是你想看到的。”她说。
“我要是想看看你的真面目呢?”我不依不饶地说。
“可是你不想,”她说,“这个”——她指了指自己,“才是你想看到的。”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格莱啊,格莱,”她叹着气说。“你以为我是用自己的想象创造这张脸和这副身躯的吗?我是在你的心灵里找到的。”
“瞎掰,”我说,“我从没遇见过长得像你的人。”
她微微一笑: “可是你希望自己见过,”她停了一下,“你要是见过,你肯定想她名叫瑞贝卡。我不仅是你需要的一切,还是你想要的一切。”
“一切?”我疑惑地问道。
“一切。”
“我们能不能……呃……?”
“你滑倒的时候,我没有防备,”她答道,“我摸起来是不是像你希望我做的那个女人?”
“我有话直说吧。你的衣服和你一样是错觉?”
“衣服是错觉,”她说,突然之间,衣服消失不见,她站在原地,面对着我,赤裸着,“我是真的。”
“你是个什么东西?”我说,“你不是一个真实的女人。”
“此时此刻,我和你认识的所有女人一样真实。”
“让我想一分钟,”我一边看着她,一边试图思考,我意识到,自己完全没在想正事,于是我把视线投向地面,“把夜行兽赶跑的那个东西,就是你吧?”
“那时候我就是你需要的东西,”她答道。
“把树顶上的叶子扯下来的,那也是你吧?”
“你需要叶和草混在一起来抗击炎症。”
“你的意思是,你被放在这里,完全是为了满足我的需求?”我问道,“我觉得上帝不会那么大方。”
“不是的,格莱,”瑞贝卡说,“我的意思是,照料需要照料的人,是我的天性,甚至是我的冲动。”
“你怎么知道我需要,或怎么知道我在这行星上?”
“发出求救信号有很多种方法,有些你根本就想象不到。”
“你的意思是,如果有个人在五公里之外受苦,你就会知道?”
“是的。”
“超过五公里呢?”我接着说道,她只是注视着我, “五十公里呢?一百公里呢?整颗星球呢?”
她看着我的眼睛,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如此悲伤,我都把她的其余部分完全忘了。她说道:“不只是这颗行星,格莱。”
“你跑开几分钟的时候,是去解救其他的什么人吗?”
“这行星上就你一个人。”她答道。
“哦,然后呢?”
“一只小型有袋动物断了一条腿、我为它减轻了痛苦。”
“你没去那么久,”我说,“你意思是,一只受伤负痛的野生动物会让一个陌生的女人接近,我觉得那很难叫人信服。”
“我没有用女人的模样接近它。”
我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我觉得自己隐约希望她会变成某种外星怪兽,可她看上去依然美丽。我打量着她的身体,想找到几处瑕疵,以显示她并非人类。但是我什么都找不到。
“我得好好想想。”我最后说。
“你想要我离开吗?”
“不。”
“我要是重新造出衣物的错觉,是不是会不那么让你分心?”
“是的,”然后我说,“不!”我又说,“我不知道。”
“他们总能发现,”她说,“可通常不会这么快。”
“除你之外,还有……还有像你这样的东西?”
“没了,”她答道,“我们以前是个庞大的种族,我是留在尼基塔的少数之一。”
“其他人怎么了?”
“他们去了需要他们的地方。有的回来了,大多数则从一个求救信号前往另一个。”
“我们的飞船六年没来了,”我说,“他们是怎么离开这行星的?”
“银河里有许多种族,格莱。在这里着陆的不止地球人类。”
“你救过多少人?”
“几个。”
“帕楚卡人呢?”
“帕楚卡人也有。”
“我想,对你来说,我们都是外星人。”我耸了耸肩说。
“你不是外星人,”她说,“我向你保证,此刻的我是完全的地球人类,就像是你梦中的瑞贝卡。实际上,我就是你梦中的瑞贝卡,”她很快地微笑了一下,“我甚至想做那个瑞贝卡想做的事。”
“这可能吗?”我好奇地问。
“你有一条断腿的话不行,”她答道,“但那是可能的,不仅可能,而且自然。”
我一定是一脸怀疑,因为她补了一句:“感觉起来完全像是你希望的那样。”
“你最好再把衣服穿上,免得我做出什么很傻很傻的事情,再把自己的胳膊和腿弄坏。”转眼之间,她又重新把衣服穿上了。
“这样好点?”她问道。
“至少安全点了。”我说。
“你去沉思吧,我要开始为你做早饭了,”她一边说,一边扶我走到了树影下,然后回到定居泡里去找H口粮。
我一动不动地坐了几分钟,想了想自己听到的一切。我得出了一个至少在当时显得惊人的结论——她就是我梦中的女郎。她是个绝色美人,至少我觉得是。我们有许多共同爱好,她对这些爱好的热情和我相当。和她在一起我觉得舒服,得知她其实是某种异类后,我还没有自己想象中的一半烦恼。如果她只有在我出现的时候才是瑞贝卡,那也比从来没有一位瑞贝卡要好。而且,她喜欢我,如果不是真的喜欢我,她不会这么说的。她走了过来,递给我一只碟子,里面盛满了大豆制品。在她的烹饪下,这食物成了外观和口味都与大豆截然不同的制品。我把碟子放在地上,把她的手握在自己的手中。
“你没有把手抽回去。”我一边说,一边轻轻抚摸她的手。
“当然不用啦,”她说,“我是你的瑞贝卡。我喜欢你的抚摸。”
“我也没有把手抽回来,”我说,“也许这有点儿更加奇怪吧。我坐在这里,抚摸着你,看着你,闻到你在我身边,完全不在乎你是谁,不在乎我不在的时候你是什么样。我只是想让你留下。”
她弯下腰来吻我。如果这感觉和被人类女性亲吻有什么不一样,我也肯定感觉不到不一样在什么地方。我吃了早餐,我们聊了一早上——关于书本、关于艺术、关于影院、关于食物,我们的兴趣共同点大概有一百项。我们聊了一天,到晚上还在聊。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但我在半夜醒了过来。我侧身躺着,她在我身边缩成一团。我感觉腿上有什么温热平坦的东西,不是绷带。那好像是在……说“吸”太难听了,应该是“抽取”……从我的腿上抽取了一点感染液体。我有一种感觉:这是她身上某个我看不见的部分。我决定不去看。等我早晨醒来的时候,她已经在收集木柴,准备给我热早饭了。
我们在那个营地过了七天世外桃源的日子。我们聊天、吃饭,我开始拄着她做的一对拐杖行走。她有四次告辞跑开,我知道她一定是收到了空气中的另一条求救信号,但她总是几分钟后就回来了。在七天结束之前,我就明白:尽管折了腿、碎了胳膊,这七天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日子。
第八天,那是我在尼基塔上的第九天了,我和她一起缓慢而痛苦地回到了飞船将在第二天早晨接我走的地点。我在晚饭后设置了我的定居泡,几个小时后爬了进去。沉沉睡去的时候,我感到她在我身边躺下了,这一次衣服的错觉消失了。
“我不能,”我不开心地说,“我的腿……”
“嘘,”她小声说道,“都交给我好了。”
我全都交给了她。
我醒来的时候,她正在做早饭。
“早安,”我一边说着,一边从定居泡里出来。
“早安。”
我—瘸一拐地走过去吻她:“昨晚谢谢你。”
“希望没有碰坏你的伤口。”
“有的话,也值得,”我说,“飞船还有一小时不到就要来了。我们得谈谈。”
她看着我,等着下文。
“我不在乎你是什么,”我说,“对我来说,你就是瑞贝卡,我爱你。飞船没来之前,我得知道你是不是也爱我。”
“是的,格莱,我爱你。”
“那么,你愿意跟我走吗?”
“我是想走的,格莱,”她说,“可是……”
“你以前有离开过尼基塔吗?”我问。
“有,”她答道,“每当我感觉到和我有过关联的人的身体和情感上正受苦的时候。”
“可你总是会回来?”
“这是我的家。”
“你在西摩离开尼基塔后去看过他吗?”
“我不知道。”
“什么叫你不知道?”我说,“你要么去过,要么没有。”
“好吧,”她不开心地说,“我要么去过,要么没有。”
“我还以为你永远不会对我说谎。”我说。
“我没有说谎啊,格莱,”她一边说,一边伸出一只手搭在我没有受伤的肩膀上,“你不明白连接的工作原理。”
“什么连接?”我不解地问道。
“你知道,我长这个样子,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我无法抗拒地被你的痛苦和需要吸引,”她说,“我们是联系在一起的,格莱。你说你爱我,也许是真的。我也有那样的情绪。可我之所以有那样的情绪,和我能谈论你最喜欢的书本和戏剧是一个原因——我在发现瑞贝卡的地方发现了它们。当这联系中断的时候,当我不再和你交往的时候,它们就会被我忘记,”她的脸颊上流下了一颗泪珠,“而且,我此刻对你的感觉也会被一起忘记的。”
我只能看着她,试图理解她说的话。
“抱歉,格莱,”她过了一会继续说道,“你不可能知道我有多抱歉。现在我只希望能和你在一起,照顾你一可当联系中断时,一切都会结束,”她又流了一滴泪,“我甚至都不会有失落感。”
“所以你不记得有没有到地球拯救西摩?”
“我可能去了,可能没有,”她无助地说道,“我不知道。也许我永远不会去了。”
“没事的,”我说,“我不在乎其他人。只要你和我在一起,别断开连接就好了。”
“我控制不了啊,格莱,”她答道,“你最需要我的时候,连接最牢固。当你的伤口愈合的时候,当你不再需要我的时候,我就会被拉到更需要我的人或物那边去。也许是另一个人类,也许是个帕楚卡人,也许是别的什么。可那样的事会发生的,一遍又一遍。”
“直到我比任何人都更需要你。”我说。
“直到你比任何人都更需要我。”她确认说。
那一刻,我明白了西摩,丹尼尔斯,还有其他人为什么要踏入必死的境地。我还明白了塞莫上尉和帕楚卡的历史学家Myxophyl不知道的事:他们不是要让自己被杀,而是想让自己几乎被杀。突然之间,我看见了头顶上的飞船,它正准备在几百米外降落。
“此刻有什么人或物需要你吗?”我问道,“我是说,比我更需要?”
“此刻?没有。”
“那就跟我走,越久越好。”我说。
“这是个好主意,”她说,“我是可以开始旅行,可是你正一天比一天健康,而且总是有什么东西在需要我。我们会在一个太空港着陆换乘,你一转身,我就会消失。六年前的地球人类和帕楚卡人幸存者就是这样的,”她的脸上现出了伤感,“银河系里的痛苦和折磨太多了。”
“可是,就算身体健康,我也需要你,”我说,“我爱你!”
“我也爱你,”她说,“今天爱,可是明天呢?”她无助地耸了耸肩膀。
飞船着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