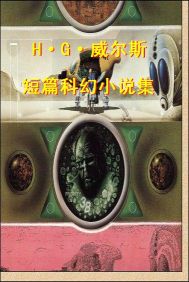外国中短篇科幻小说1000篇 (第九辑)-第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外的人守在那儿。
大洋港距离迈阿密海岸八公里,急救飞船不到一分钟就把我们送到了那里,可为了不对伤者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又花了四十秒才把飞船轻轻停稳。
我已经抽出他的钱包和身份证仔细看过。他名叫迈伦·西摩,四十八岁。他身上还留着参军时候部队植入的芯片序列号。其他特征同样平淡无奇:身高中等、体重中等、这个中等、那个中等。
他看上去并不太像英雄人物,然而,我以前从没见过一位名副其实的英雄,所以英雄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也说不上来。
“上帝啊,”出来帮忙把西摩抬进急救室的一名护工说道,“又是他!”
“他以前来过?”我吃惊地问道。
“三次,兴许四次,”他答道,“我敢发誓,这混蛋是想自杀。”
西摩进手术室的时候,我还在为这句话感到莫名其妙。三小时后,他出来了,深度麻醉,情况严重。
“他会挺过来吗?”我问了刚才那个护工,他正在把充气担架推进康复室。
“没指望了。”他说。
“他还有多少时间?”
他耸了耸肩,说:“在外面的话一天吧,可能更短。一旦我们把他连上所有这些机器,就不要往好的方面想了。”
“有没有开口的可能?”我问道,“或者至少听得懂我对他说的话?”
“不知道。”
“我留下可以吗?”
他笑了笑说:“你走路带着臂章,身上带着致命武器,我能看见的有三把,我看不见的兴许更多。我算老几?敢说你不能留下?”
我在医院的食堂里拿了个一个三明治,然后去了康复室。病人之间是相互隔离的,我花了几分钟才找到西摩。他躺在那里,几十部机器监测着他的生命指标,五根管子往他的手臂里注入五颜六色、或浓或淡的液体,他的鼻孔里接着氧气,身上缠满绷带,绷带里开始隐隐往外渗血。
我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觉得他永远没有苏醒的可能,可我还是又呆了一小时,为的只是向这个解救小女孩的男人表达敬意。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他的眼皮颤抖着张开了。他的嘴唇在动,可我听不见他在说什么,于是,我把椅子拖到了床边。
“欢迎回来。”我轻声说。
“她来了吗?”他小声问道。
“你救的小姑娘?”我说,“没有,她很好,和她父母在一起。”
“不,不是她,”他的脑袋都快不能动了,可他试着看了看房间四周,“这一次,她一定会来的!”
“谁一定会来?”我问道,“你说的是谁呀?”
“她在哪里?”他用嘶哑的声音说,“这一次我就要死了,我知道的。”
“你会好起来的。”我撒了个谎。
“除非她很快就来,”他试着坐起身来,可他太虚弱了,又瘫倒在了床上,“门是不是没上锁?”
“这里没有门,”我说,“你是在康复病房里。”
他困惑地问:“那她在哪儿?”
“她可能不知道你受了伤。”我说。
“她知道的。”他的语气绝对肯定。
“她在太空港里吗?”
他微微摇头,说:“她甚至都不在这行星上。”
“你确定不要我去问问前台?”
“没法问,她没有名字。”
“每个人都有名字的。”
他叹了口气,说:“随你怎么说。”
我开始后悔当初留下了。我没能给他带来任何安慰。
“你能跟我说说她的事吗?”我问道,我是想在罢手回家之前,试着再帮他一次。
他看上去肯定是要说什么话,可接着他就昏了过去。几分钟后,连在他身上的所有机器全都开始震动,几个年轻的医生冲进了房间。
“他死了吗?”我问道。
“出去!”其中的一个医生下令。
他们开始实施急救。我觉得再呆下去就会碍手碍脚,于是,我走到了外面的过道里。没过多久,他们就从房间里出来了。
“他死了吗?”我又问道。
“是的,”其中的一个答道,“你是他朋友?”
我摇头说:“不,我只是把他从太空港那里带了过来。”
几名护工抬着充气担架出现了,其中的一个是先前和我说过话的那个。
“我跟你说过,他不会撑过一天的,”他说,“这些人怎么会觉得自己冲进水流一样的子弹和镭射当中还能完完整整地出来呢?”
“这些人?”我重复着说。
“是啊,这已经是这个月的第二个了。三个月之前还有一个男的。他遇上了银行劫匪,没有打电话给警察,而是朝四个带枪的家伙冲了过去,”他用力出了一口气,摇了摇头,“那可怜虫没能接近他们身边二十米的范围。”
“是不是到达前死亡?”我问道。
“差不多,”护工答道,“他一口咬定有人会来陪他,还坚持要门口的每个人都知道该把那女的送到哪儿。”
“女的?”
“我觉得是女的,”他耸了耸肩, “也可能我搞错了。他没说几句清醒话。我觉得他有那么一会儿都不记得自己叫什么了。丹尼尔·丹尼尔斯,是他的全名,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们得把这家伙拉到地下室做尸检了。我们现在在休假,但是这个礼拜人手有点不够。”
我走到一边,让他们进了房间。出于好奇,我离开之前在入口处停了下来,打听了是否有人问起过西摩。
一个也没有。
回到办公室以后,我还是觉得好奇,就到电脑上找了些关于西摩和丹尼尔·丹尼尔斯的零星信息。’西摩找起来简单,出生和成长都在迈阿密,在这儿上的大学,太空上服役九年,在俗称尼基塔的柯本柯夫二号星上的一次交火中中弹,身受重伤,然后载誉退役。回家后,从事海滩房产销售,两年前,他突然铁了心要证明自己不是英雄就是防弹人,或者两样都是。从那以后,他曾三次试图丢掉性命;头两次是医院帮他保住了命,但这一次没能保住。
丹尼尔斯就不那么简单了。年初的时候,其实有四个丹尼尔·丹尼尔斯住在迈阿密。有两个还在此地。另外两个,一个在三十九岁的时候死于相对自然的原因,剩下的那个就是护工跟我说的那个。
他死的时候三十九岁。十六岁时退学,签过两份小联盟足球的合同,两次都被开除,二十岁的时候参加太空部队,服役七年,伤病退役,此后换了几份工作。 我查看了那份伤病退役记录。他在尼基塔上重重挨了一发高射炮。身体是康复了,可四年里他一直都在因抑郁症看心理医生,一天晚上,他试图和一群不良少年动手,并因自己惹的麻烦而烧伤了。花了一年时间,他的皮肤恢复原状,但这死人一个月后跑到外面又做了一件同样具有自杀性的事。连警察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发现他的时候,射击已经结束——他身中各种口径的铅弹,肯定是单挑了六个带枪的男人。
事情是这样:两个不起眼的男人,除了居住的镇子和服役的行星之外,互相之间却没有任何共同点,两人都甘愿面对死亡,原因不明;还有,被救之后,两人又都重新面对死亡。
我还在沉思的时候,塞莫上尉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交报告。我跟他说了我看到的情形,其他报告都和我的见闻相符,然后我想,没我的事了。
“等一下。”他说话的时候,我正要转身出门。
“什么事,长官?”我说。
“你跟他去了医院,为什么?”
“我当时希望他能告诉我为什么自愿冒这个险,”我答道,“我原以为他对我们击毙的人有所了解。”
“那他了解吗?”
我摇了摇头,说:“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了。他在术后只恢复了大约一分钟的意识,然后就死了。”
“他到底为什么要那么做呢?”塞莫上尉沉吟道。
“我也想知道,”我说,“于是我在电脑上查了他和丹尼尔斯……”
“丹尼尔斯?”他突然问道,“谁是丹尼尔斯?”
“是另一个用同样方式结束生命的男人,”我说,“两人唯一的共同点是,都居住在这里,都目睹过柯本柯夫二号星上的行动。”
“柯本柯夫二号,”他重复了一遍,“就是他们叫做尼基塔的那个?”
“是的,长官。”
“那倒挺有趣啊。”塞莫上尉说。
“怎么了,长官?”我问道。
“大约两年前,我在火星港上管安保,那时有过同样的事。四个男人抢劫一家餐馆,有个男的在等去泰坦星的航班,他决心赤手空拳和他们打。他还没走近,他们就打中了他。我们在这四个人伤害其他人之前制服了他们,可这男人中了太多子弹和能量脉冲,几个小时后就死了,”塞莫上尉停了下来,皱起了眉头,“那时候,我得填张表格,也就是说得弄清楚被杀的是谁。我之所以要提这件事,是因为他在尼基塔上呆过。”
“伤病退伍?”
“是的,”他答道,“奇怪,对吗?”
“非常奇怪,”我说,“你知道那次是不是他第一回那样拼命?”
“不,我不知道,”塞莫上尉说,“我想你这样问是有原因的吧?”
“是的,先生,是有原因的。”
“给我一分钟时间检查记录。我说过,是两年前的事了。”他激活电脑,调出我们正在讨论的文件,对死者的身份进行了调查。十一秒后,有了答案。克莱顿·木藤僧二世曾经四次面临必死的境地。他仿佛奇迹般地逃过了前三次,命运之神在火星港上才履行了诺言。
“上尉,”我说,“如果我告诉你:西摩和丹尼尔斯也是几次拼命才成功的,你会怎么说?”
“我会说,他们在尼基塔上遇到了某种非常有趣的事,”他说完后,打印了一份柯本柯夫二号的材料,仔细看了一会儿,然后耸耸肩说,“它的大小大概是地球的四分之三,重力更小,氧气有点少,但呼吸不成问题。我们在和帕楚卡联军打仗的时候,发现他们用尼基塔临时屯放军火,我们派了一小队人登陆,炸掉了屯兵处,双方都伤亡惨重。剩下的几个幸存者分散各地,我们花了大概三个礼拜的时间才找到了他们,最后,他们回到了大部队。那里有些动植物,但是没有人类,也没有帕楚卡人。”
“不知道上面究竟出了什么事,”我说,“大多数在战争期间中弹的人都不会愿意重新经历战斗——这三个人却特地寻找这样的机会。”
“用你的电脑查找幸存者,然后再发问。”他说。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整理报告,试着按照塞莫上尉的提示,找出尼基塔上的那些幸存者。帕楚卡战争已经结束,所有文档和记录都随之解密,但它们并没有派上多大用场。那时候,我们派去的是一个由三十名男女组成的秘密小分队。那场行动异常惨烈。二十五人在尼基塔阵亡,剩下的五个——其中包括西摩、丹尼尔斯、和木藤森——身受重伤。他们显然是分开了,每个人都设法依靠自己活了下来,直到几周后救援小组到达。我试着找到另两个幸存者。两人都曾向死神献殷勤,直到死神命中注定地与他们会面。
从两人的履历中,完全看不出格外勇敢或者格外愚蠢的迹象。除了丹尼尔斯的抑郁症,他们两人都没有因为情绪或心理问题接收任何治疗。据我所知,他们在退伍后都没有与其他任何人联络。
尼基塔上的战斗发生后的六年之内,他们都死了,死前置身的环境只能用“自录性”来形容,就算是最好的外科医生、最好的医院也没法保住他们的性命。
第二天,我向塞莫报告了我的发现。看得出来,他和我一样吃惊。
“你觉得是什么让他们放弃生命呢?”他沉思后说道,“还有,如果他们那么想死的话,何不干脆在脑袋上放一枪?”
“要发现真相只有一条路,长官。”我说。
“我不能把你派到尼基塔去,”他说,“我们是大洋港的安保,尼基塔在一千多光年之外。”
“可是如果是那颗行星上的什么东西引发了这种行为……”
“别想了。如果那里的食物、水或者空气有问题,太空部队和海军早该发现了。”
可是我没法不想啊。要怎么忘记这样的事呢:一群完全没有共同点的人,在分享了同一段经历后,就用完全相同的行动毁灭了自己?
每天晚上,我都会在工作结束后回到我的住处,试着寻找更多关于那颗行星和那些幸存者的信息。问题是,可供寻找的东西实在太少。那些人在室外呆了三周,或许四周。一共只有五个人,行星在战斗后就被帕楚卡联军抛弃了,从那以后,再没有人回去过。战争已经结束,我给几个帕楚卡的历史学家发了信,希望他们能告诉我些什么——不是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