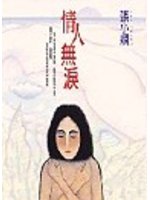今晨无泪-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必说感谢的话,你知道我在你身上也能受惠。我不是个纯感情用事的人。”
说罢,才走下车去,为我拉开了车门。
一整夜,我出奇地睡得安稳。
已经很久没有人跟我坦率地把感情问题摊开在面前讨论与研究。
通过与陈家辉那一席话所能得到的发泄,令我仿似做完一场运动,疲累,却是打通整体脉搏地舒畅。
我需要休息,好好地睡上一觉,再算。
然而,天才微微发亮,我就蓦然转醒过来。
我霍地坐起来,以为自己在做梦。
没有,不是梦,是现实。
又要正视活生生的一天了。
能安处于熟睡之中是那么安乐,那么了无牵挂的。难怪有些伤心失意的人但愿长眠不起。
没有梦,不要紧,只要不再转醒过来最好。
醒后的颓然惆怅,也是一种难堪。一念及还是要一无进展,有日过日的活下去,心就灰,意就冷。
即是富贵荣华仍不敌伤感,不期然就恨父母为什么把自己生到世上宋。
我立即跳下床去,赶快脱离一个可以纵容自己胡思乱想的地方是正经。
我换过便服,差不多是夺门而出。
太早了,天才发着鱼肚白。
连司机都未上班,我把自己开惯的车子驶出来。
那是一辆曾迷倒一位美少年,竟经营出卖肉体的勾当,为了占有它的林宝坚尼。
活在世上的所有人,原来都在追求自己手上所没有的东西。
那辆通体银白的名车,在深水湾道上奔驰,一直开出跑马地。
我打算去拜祭亡父和亡友。
我曾悉心地安排,把蒋帼眉安葬在父亲身边。
生前,我的童年好友跟父亲的一段忘年之恋,是如此缜密地包藏起来,不为人知。
殁后,让他们紧紧地偎依在一起,相依为命,亮相人前,也许是一个补偿。对活着的后人,感觉的确如是。
清晨的坟地额外的孤寂寒伧,好比穷透了的人踯躅在午夜街头,环境与时分都加添了压力,而倍觉凄凉。
我已记不起何时曾在父亲墓前跟他说话了。
这天之所以来访,是为胸臆已有承载不下的疑难困扰,昨夜被陈家辉撩动起来,需要进一步的发泄。可是,找谁去当这倾诉对象呢?
除了父亲,除了蒋帼眉,我还是只有他俩。又即使他们已长眠地下,亦复无人可以取代。
因而,我只有来了。
多么的无奈与伤感。
走了一小段的路,已到墓前。
奇怪,竟有鲜花。
在那镶嵌在墓坟上的大理石花瓶上,插了一大蓬粉蓝和白色的毋忘我,那些嫩润明亮的花瓣承接着清晨的露水,显得异常清丽。
谁会来拜祭他们?谁又有此心思,作此敬礼?
我忽而觉得墓地的周围阴风阵阵,地上的残枝败叶,随风而微微飞动所发出的声响,加添的不是生气,而是苍凉。有太多不可知的事在这儿发生着似,这令我不寒而栗。
父亲江尚贤与好友蒋帼眉之间,总是蕴藏太多的秘密,不为人知。生前如是,死后也是这样吗?
我拿手扫着手臂,企图给自己带来一份温暖,跟着缓缓地蹲下去,抚触着那冰冷的大理石花瓶,再拿起一枝花,轻声地说:
“毋忘我。”
耳畔立即听到了一声回响,道:
“对,是叫毋忘我。”
跟着我看到身旁有一双漆黑的皮鞋与一对深灰色的裤管出现。
我吓昏了。
很自然地颓然坐跌到地上去,再昂起头来,竟见到一张不应该在这儿、这个时刻见到的脸。
对方伸手把我拉起,还未曾站稳脚步,我又清清楚楚地听到他说:
“我每天早上都在这儿候着你,我知道你终归会来。”
我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然而,来不及细想,事情怎么会发生的?我已经整个人酸软得像一团棉花,被簇拥在对方的怀抱里。
固然是为了我的措手不及,引致的惊骇与惶恐,也为对方是一股强大而不能阻挡的力量。
我吓得闭上了眼睛。
眼角随即渗出了泪水,沿着脸颊而下。
是期待已久的解脱,因而喜极而泣?抑或是束手就擒,屈服于命运之下,准备接受另一次挑战的决断,因而使我落泪?
对方不会明白,不会知晓,甚至不会留意。
他只是迹近疯狂地,啜吸着我的双唇,使我隐隐作痛,而又不能摆脱。
他像深具魔力的魔鬼,在这个天朦胧、地朦胧的清晨,决心把我体内的精血一次过抽脱。
之后;我就有如一具行尸,完完全全地听命于他,属于他了。
坊间的传说,总是认为那些无辜者,在被害之后,就像上了毒瘾,非常心肯意愿地跟着那厉鬼一辈子了。
现今来问我:你的情况也如此吗?
答复差不多是肯定了。
像过了一千一万一亿年,他才放开我。
瞳眸相对。
地下仍是沙沙沙,那些枯叶微微被吹动而碰触到我的脚跟时,还觉得有点湿濡,是露水吧?
每一个微细的感觉都如此清晰,自然就不是梦。
我的眼泪无休止似的汩汩而下,鼻子开始寒宰作响,我昂起头,望着一片淡灰的天空,企图不让泪水再滴湿衣襟。
是有首民歌这样说的:
“昂起头来走路,为了不使眼泪在人前滴下。”
是的,尤其是跟前的这一位。
然而,一切都显得太迟,对方重新拖起我的手,拍着,说:
“别哭,流泪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信我。”
是信他的时候了。
我的精血被对方噬吸之后,我是他的信徒、忠仆、拥护者,当然得信他了。
我们手牵着手,缓步向前走。
天还没有大亮,然而,在我的感觉上,满眼都是阳光。
我们面前的光源似乎来自非常遥远的一方,二人肩并肩一直向着光源走去,前景是光明而乐观的,又像走进时光隧道,开始重温多年前曾拥有过的浪漫与温馨。
走得很轻快、很曼妙、很写意,也走了很久,我们才停下了脚步。
邱仿尧终于把我带到一处属于我们二人的天地里,他重新捧起了我的脸,细看之下,情不自禁地再俯首下去,轻轻为我吻干泪痕。
当我接触到对方裸露的肩膊时,我浑身因紧张和兴奋而微微颤动。
那宽阔的肩膊,结实的胸膛,曾于多年前在菲律宾一个蕉风椰雨、景色秀丽的岛上,向我展示。我明知道几夕缠绵,数朝眷恋之后,就得分离了,然,我还是抵受不了深情热爱所牵动起的诱惑,伏到邱仿尧的怀抱里去。
当年,陪伴着我们的是海浪声,海水涌上来,退下去,那种波动一如相恋人儿身心所承受的紧张与松弛。
如今,耳畔只有两个历劫重逢的爱侣那细细的嗟叹与喘息,气势和感受一样有如澎湃的波浪,翻上来,覆过去,终于把狂燃的爱火扑灭。
当激动的情怀获得了宣泄之后,一刹的平静,让当事人的头脑缓缓地清醒过来。
在回味着刚才丝丝甜蜜的当儿,我已晓得问一些跟现实有关联的问题。
“你真的每天早上到坟地去吗?”
“嗯。”邱仿尧答应着。
“从哪个时候开始?”
“回港来之后不久。”
我笑,说道:
“回港来,就为上我父亲的坟?”语调明显的是得意的。
我看邱仿尧没有作答,一个翻身,抱住了他,把脸抵在他的胸膛上,再问:
“你没有答我。”
“女人爱明知故问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你看呢?”
“势必要男人把你们的自尊捧到半天去,才叫甘心,是不是?”
“你不愿意?”
“我已经以行动履行了我的心意。”
我昂起头,用手指扫着邱仿尧的鼻尖,欲言又止。
“别诱惑我!”邱仿尧说:“你可以想象到后果。”
说罢,捉住了我的手指。
我吃吃笑地挣脱开了,说:
“不,不,我有很多正经事要跟你说。”
“不是时候吧?”
“为什么不?你不是等待了这些年,才得着这个可以跟我一诉衷情的机会?”
“我的理想跟你的略有出入,我着重实效。”
“可恶!”我啐了他一口,再问:“如果我不到坟地去呢?”
“你不会。”
“何以见得?”然后我立即俏皮地说:“因为我孝顺。”
邱仿尧斜眼看我,忍不住笑。
这个稍微带不屑的表情,是多年前的邱仿尧所没有的。
那段日子内的他,是个没有棱角,只有纯情的男人。
岁月往往为人带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磨难,而使人棱角顿生,好比刺猬,一遇有风吹草动,自然耸立起坚挺的锐刺来,以作防范。
我完全明白邱仿尧从前受创有多深。
就算今时不同往日,也不能责怪他。
当然,我对仿尧的深情令我心甘情愿的予以谅解。
邱仿尧并没有附和我的说法,他的表情甚至否定我自以为孝顺的说法。
我于是追问:
“那么,你为什么认为我是必会到坟地上去?”
仿尧答:
“你会去祈福,因为你知道蒋帼眉和你父亲会保佑你。”
太一针见血了。人总是会从利己的角度出发去处事待人,也只有从这个角度去揣测,才最可靠与可信。
对亡父亡母挂念,需要拨出时间与心情应付。
为自己的福荫祈求,则会刻意而专心地安排。
邱仿尧的推断其实只不过把我的心意宣泄于口而已。
下意识地,人总会在愁苦与困扰之时,求庇神灵。
父亲生前视我如瑰宝,他的红颜知己蒋帼眉在遗作的序言亦曾赤诚地表示,她和父亲疼爱我。
为我的幸福,表示愿意赔上生命。
死而有知,他们会护庇仍庸碌在世的亲人。
心灵与精神上的互相需求与援引,仍会将殊途的人与鬼拉近。
因而,邱仿尧相信我会有日到坟场上去。
我不能否认这种推断没有准绳,我抿着嘴,默不做声。
邱仿尧拉起了我的手,放到自己的唇边去,轻柔地吻了一下,才说:
“不要生一个愿意在风露之中为你伫立终宵的人的气。”
“仿尧!”我重新地怀抱着对方:“生气的人其实是你,你一直不能予我谅解,并不知道我的委屈。所有人与周围环境都把我迫到墙角去,一旦反抗了,就都说我无情无义。”
多少年来,我不曾如此发泄过,如此苦水一吐,一泻千里。
“我不用谅解你,我只需要爱你。”
邱仿尧把身翻过来,面对面地对我说:
“我以为自己可以忘掉过去,为公义而离弃我的挚爱,原来我高估了人性。回菲律宾后,我一直惦记着你,清晨、黄昏、日夜,只要我孤独,就更难忘情。”
“即使有小葛在你身边?”
邱仿尧不打算回答这个令他神经蓦然紧张的问话,他不要在这个时候,这个环境内提起葛懿德。唯一彻底的解决办法是令我分神到别的销魂事上去。
一切都是如此真实的,并不是梦。
为此,世界在我的心上突然发光发亮,美好得似踏进神话之中。
我开始了生命上崭新的一页。
差不多跟我有往来的人,都渐渐感染到自我身上传来的愉快与轻松。
即使在利通银行庄严的会议室内,议论着严肃至极的公事,我这位年青的主席穿着得很保守,打扮得很踏实,依然流露的笑意与甜蜜得忍不住外泄的语气中,令满座生辉,顿觉活力充沛。
没有人明白这个转变的幕后理由。
或许应该说,人们仍然下意识地认为这只不过是女性,尤其是口含银匙而生的职业女性所特有的情绪化现象,时而激动、时而亢奋、时而喜、时而忧、时而怒,总是无常。
连我身边两位算谈得来的异性朋友,宋滔与陈家辉,都只觉得我整个人都精神了、轻松了,而不明白底细,亦没有意识到需要追查原委。
宋滔一直照顾着惘然轩的工程,明显非常顺逐。
本城建筑工程的快速,闻名于世。
对于一个则师来说,尤其喜欢这种万丈高楼从地起,也只不过像平地一声雷般,转瞬就已成事的计划。
曾为本城兴筑银行大厦,勇夺国际荣誉的知名画则师卡本能就曾谈他的工作感受。
“从工作开始到完工,相当迅速,让我在短时间内看得见自己的心血,那种兴奋好比一个怀孕的女人,希望老早就瓜熟蒂落,知道生男还是生女的心态一样。须知道怀孕期可能发生很多意外,会令做母亲的胆战心惊,恨不得在获悉了将为人母的翌日,孩子就已呱呱堕地,晓得叫母亲。”
“在海外兴建一间小平房都需时,不像本城,天时地利人和配合得天衣无缝,参与工作的人,上至总指挥,下至地盘小工,都以能在三天内建成罗马的效率办事。”
结果呢,罗马当然不会在三天内建成。然而,为了这个意欲,肯定会加一大把劲,于是效率高,成果好,是顺势发生的事。
宋滔在这一天邀约了我到地盘去巡视,工程比预期进展还要快。
我开心到了不得,也顾不得还有建筑经理站在一旁侍候,就一把抱住了宋滔,吻在他的脸上,说:
“你永远是能令我喜出望外的人,自从替我兴建那娃娃屋时开始。”
宋滔腼腆而期期艾艾地应着,心上其实是顶欢喜的,嘴里只道:
“相信比预期早一个月,就会兴建到顶层你的那间云顶复式别墅了,到时我再请你来看。”
“好,滔叔,我要站在那园子里伸手向天空摘星星。”当我说着这话时,神情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