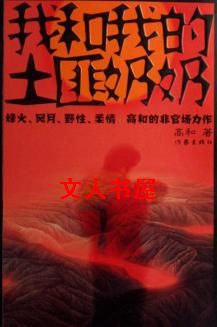我和她们-贾宝玉自白书-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把这个梦讲给晴雯听,晴雯说她喜欢我的这个梦,她说梦里的那个美少年就是我贾宝玉,而她愿意做一个陪着那花王一起游玩的花仙子。
我把这个梦讲给黛玉听,她先是捂着嘴笑了笑说,有趣,好梦啊,好梦!但随后她就发了怔,又流了泪,不知为什么。
我把这个梦讲给宝钗姐姐听,宝钗姐姐蹙了一下眉头,微微一笑说,宝兄弟,以后你就又多了个名号,绛洞花王。
于是,在我头上顶有诸多的名号之外,又多了顶绛洞花王的帽子。实话说,我真的很喜欢这顶红帽子(我觉得这顶帽子很漂亮),就像我很喜欢我那个美妙无比的梦一样。
而今,我的那些花仙子,一个个,飞天了,我的那些花儿们,一朵朵,凋零了。我这位当年的花王,望着眼前这流水,这落花,犹如一个老国王面对着那破碎了的江山,他真不知是该说悲哀,还是说悲伤,抑或是说悲凉。我这个写过那么多诗篇的诗人,时常吟味着这种一点也不像是诗的句子:花王看花亡,更是痛断肠……
是啊,人说故园不堪回首,可你总是时常会念想故园与故事的。许多年前,已不记得是多少年前了,我离家出走,投奔到这座山庙里,是想寻找我梦中的那个深红色的大岩洞么,是想与那些美丽的花仙子们相遇么?我不知道,也说不清楚。当年那个爱花、惜花、侍候花的花王,如今只剩下对花的缅怀与悼念了。
现在,我站在山岗上,遥望着山下的世界,思想着那些遥远的故事,怀念那些比远方更远,比眼前还要近的鲜花一样的女儿……
哦,花儿,我的花儿们,你们还好么?我时常雾里看花,喃喃自语。一年,又一年,花开了,花又落,花落了,花又开。但在我的眼里,她们这些美丽的鲜花永不会凋谢,无论春秋与寒暑,她们一直都盛开在我灵魂的原野上,绽放在我情爱的花园里。哦,花儿啊,你们这些鲜艳的花儿,你们这些美丽的女子,一个,又一个,一朵,又一朵,就在我眼前,就在我心上……
说一千道一万,人们还是叫我贾宝玉,尤其是在贾府里,尤其是与我亲近的那些人,总是宝玉长、宝玉短地称呼我。我知道,大家叫我宝玉,我叫贾宝玉,当然是跟传说之中的那枚通灵宝玉有关,对于许多人来说,那枚宝玉是相当奇异的,甚至很有些莫名其妙。作为这枚通灵宝玉的佩戴者,看来我是要说说它了。得承认,在我贾宝玉一生的故事里,那枚宝玉显然是个绕不过去的物件。其实,说那枚宝玉,就是在说我贾宝玉的故事。
在《红楼梦》这部书里,我是和那枚通灵宝玉一起来到尘世上的。也就是说,我贾宝玉是衔玉而生的。呵呵,衔玉而生,这显然是曹雪芹先生给世人玩的一个圈套。我相信,他自己也不会相信这样的荒诞事。衔玉而生?你想这怎么可能呢?简直是个神话,其实也就是一个精心编制的大瞎话。我猜想,他之所以在我贾宝玉身上安了这么一桩荒诞事,是想教人知道贾宝玉天生就是个怪物,是个异类,或者说得好听些,贾宝玉生来就与众不同。
与曹雪芹先生一同编排这个神话的,还有我的父母和老祖宗。他们编得圆圆扁扁的,短短长长的,就是想要让人相信,贾宝玉这个孩子真是衔玉而生的。其结果呢?贾府内外的许多人还似乎真的就信了,甚至连朝廷里那个风流潇洒的北静王水溶也信以为真了。然而,他们真的都信了么?我不敢肯定。一时间,贾府里的一个小男孩衔玉而生,就成了一则美妙的传说。那衔玉而生的小男孩儿自然就成了贾家的宝贝疙瘩,而我所衔的那枚玉当然也就是件宝物了。
那我究竟是不是衔玉而生的呢?这种事情我本人显然不可能知道,反正曹雪芹先生就是这么写的,贾府里的人都是这么说的,我的亲人们也都是这么跟我讲的。小时候,我还真以为我这个小人儿就是衔玉而生的呢,为此我得意极了,整天佩戴着它到处显摆。等我长大了些,便开始怀疑衔玉而生这件事的真实性了。当我把这种怀疑说给我那酷爱读书、想来应该很有学问的父亲贾政时,遭到的却是劈头盖脸一顿责骂,他警告我以后再提此事就大棒伺候,并要我好生保护那枚通灵宝玉,得像保护自己的眼珠子,乃至生命一样保护它,不能摔了,不能碰了,更不能丢了!对于严父的训诫,我只有点头的分儿,从不敢多嘴,哪怕我心里有团团不服和不解。父亲不让我问,我就不问了,便私下里跟那些和我亲近的人探讨这个问题,但大家一个个仿佛商量好了似的,全都很忌讳和我谈论那宝玉之事,就连和我最亲近的黛玉也是如此,只要一提起那块宝玉,她就蹙眉,就流眼泪,就一脸不痛快。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一直很纳闷,也很苦闷。想问不让问,想谈没人跟你谈,但在我心里它终归是个问题。
后来,我才慢慢地明白了,那枚所谓的通灵宝玉,其实是个符号,是个象征,它是件宝贝,也是种魔咒(我琢磨着,它有点像孙悟空头上的那个紧箍咒)。他们之所以给我安排了个衔玉而生的出身,不过是一种“借喻”——借那块宝玉,在我身上寄托他们殷切的希望,至少是要我做一个荣国府合格的继承人(他们觉得,除了我,贾府里其他的晚辈男儿更指望不上)。他们就是想让我做他们的宝贝——宝玉。呵呵,我哪是什么宝玉呢,倒像一块荒山野岭上的硬石头。对,我曾多次梦见自己曾是一块石头变成的,那是一个漫长的梦,我一直把这个梦藏在心里,从未跟人提起过。我原本就是一块顽石,可他们偏偏总想把我雕琢成什么宝玉,哪知顽石不可雕也。说到底,于贾府,我可不是什么宝贝——宝玉,也不是一个传承者,而是一个窝囊废。
但话说回来,我还是很喜欢那枚宝玉的。单看那它形状和色泽,就令人十分爱恋。它大如雀卵,灿若明霞,莹润如酥,底色血红,五彩花纹缠护。这样一件小宝贝儿,谁都想看看、摸摸、玩玩,就连那珍宝多多的北静王水溶,见了它也啧啧称奇。当然啦,它惹人眼的不光是样子漂亮,更有那正反两面镌刻着的数个蝇头篆字,除了标明其通灵宝玉之外,正面有这样两行字: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反面有这样三行字,一除邪祟,二疗冤疾,三知祸福。实话说,这玉,倒是枚难得一见的好玉,但上头的这些字真是俗不可耐(我承认,我也是俗人一个,但是过于俗的东西,我向来是很不喜欢的),对于它们,我只有摇头,还有苦笑。
佩玉避邪,这是古已有之的迷信,或者说是风俗之一。至于我的那枚通灵宝玉,是否具有知祸福、疗冤疾、除邪祟这三大功效,它真的灵验与否,我都不怎么在意。现在我最想说的是,此玉于我的另外两种意义。说白了,就是两个不大不小的秘密。而这两个秘密,是后来我不经意时才发现的。
先说第一个秘密:我的那枚玉,它是件可生梦的好玩意呢,它给了我无数个梦。不管是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我只要戴着它、摸着它、枕着它、想着它,就能做梦,做各种各样的梦,哪怕是大白天也是如此,甚至我醒着时也能梦到许多人与事。我是个喜欢做梦的男儿,当然也就会喜欢这能陪我做梦的好宝贝。哦,忽然想到,我梦里梦见了曹雪芹先生的《红楼梦》,没准儿也跟我身上一直佩戴着的这枚宝玉有关呢。
再说第二个秘密:我的那枚玉里面,有瑰丽的花儿,有如花的女子。说来难以置信,有一天,在正午的阳光下,我无意发现那枚玉里有一朵花,一朵很美丽的花,再细细地看,仿佛有一簇花,很灿烂的一簇花;实话说,当时我是十分惊喜的,但未敢跟任何人透露过。于是,我就经常在无人时,独自对着阳光观看它。又有一天,也是在正午的阳光下,我看见那玉里有位花样美丽的女子,再细看,似乎有一群如花似玉的女子,她们像这个,又像那个,比如像黛玉,像宝钗,比如像晴雯,也像袭人,等等,是啊,越看她们越像我那些亲爱的姐妹,而且全都婀娜多姿的样子,像是在向我招手。还有一天,我对着正午的阳光端详那块宝玉,只见它时而闪耀着一朵花,或一簇花,时而活现出一个女子,或一群女子。天哪!我的这块玉里有美女一样的花儿和花儿一样的美女,而且只有在正午的阳光下才能看到,这简直是太奇妙了!更奇妙的是,即使在正午的阳光下,也不一定就能看到花儿和她们,花儿和她们会藏猫猫呢。很有趣的是,这玉里面的花儿和女子,我贾宝玉能看得见,别人却看不到。我曾经几次试着让我的书童茗烟看过,他也全都按照我所说的样子,对着正午的阳光瞅了半晌,摇了摇头,说是除了五彩花纹,什么也没有呀。我也请袭人姐姐这样看过,她的回答跟茗烟是一样的。茗烟和袭人都同样追问过我,你到底要我看什么呀?我只是笑笑,没有点破其中的奥妙。我只是让他们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而没说那里面究竟有的是什么,可惜他们什么也没有看到。于是,这块玉里有花儿和女子,就更是我自己的秘密了。
我的这两个秘密,从未向人提起过,哪怕是和我最亲近的人,比如袭人,比如茗烟。有好几次,我禁不住想跟他们透露一下,但最后还是吞了回去。我怕说出来他们也不会信,没准儿还会说我有病呢,甚至还可能由此惹出些意想不到的麻烦来。于是,我就把这两个秘密深藏在心底,而且一藏就是很多年,很多年。
现在我不怕了,说出来这两个秘密也没什么要紧了,因为我早就离开了贾府,离开了他们和她们。
多年以前我就把家丢了,我把家里的一切都丢了,就只戴着这枚宝玉,来到这座山上的寺庙里,不管是福是祸吧,我一直带着这块玉,它一直陪伴着我,我带着它,就可以一直做我的梦,就能够看到那些美丽的花儿和女子……
我似乎这么说过,而且我愿意一再这么说:从某种意义上讲,男人的一生,不过是和一些美妙而难忘的女子之间的情感故事罢了。什么国家大事啦,仕途经济啦,功名利禄啦,全不入我眼,或者说都是过眼云烟,更不入我心,干脆说令我恶心,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反正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想说的是,我一生的故事只与花一样的女子有关。说白了,我贾宝玉的故事,就是和那些女子的故事。没有她们,也就没有我贾宝玉的故事了。或者说,如果没有一个个美丽的女性,我这个名叫贾宝玉的男子的故事,也就没什么趣味了。现在,我只想追忆和她们之间那些美妙的故事。其实,哪需要什么追忆呢?她们,和她们的那些美妙的故事,尽管已经离我很远,很远了,但闭上眼睛我也能看得一清二楚,就像眼前这烂漫的山花一样。
第三章 我和可卿的秘密
说书的,讲故事的,面对繁复的人物和故事,往往都会用这一招:花开两朵,先表一枝。其实,他也只能这么做,谁也没有更妙的招数。可我眼下面临的问题是,这一招已经远远不够了。要知道,此生与我贾宝玉有关系的那些美丽可人的好女子,她们就是我心目中的鲜花,一朵又一朵,花团簇拥着,一直盛开在我灵魂的原野上,或者说她们永远绽放于我情感的花园里。现在,我究竟该先表哪一枝呢?这显然是个难题,让我颇费了些踟躇。
没有想到,后来帮我解决这个难题的,竟是我的唐人本家贾耽。那天早晨,我坐在山庙前一片花丛中,闲翻他的《花谱》,翻到了关于芍药的这一页。不消说,我当然是很喜欢芍药花的。这种花卉不寻常(在我看来,很多花儿都是不寻常的),它花形那么妩媚,风姿那么绰约,色泽那么丰盈,它那么神秘,那么艳丽,且芳香四溢,集色、香、韵三美于一身,有着“花相”之美称。我知道,芍药还有两个颇具诗意的别名,绰约,将离。在我早已熟读过的《诗经》里头,有这样的句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那时候,人们就把芍药作为离草,情人惜别时常以其相赠。或许,芍药乃因此而被另称之为将离的吧。哦,芍药,芍药,我所喜欢的许多诗词名家人都赞美过它,柳宗元说它,欹红醉浓露,窈窕留余香;元稹说它,剪刻彤云片,开张赤霞裹;苏东坡说它,倚竹佳人翠袖长,天寒犹着薄罗裳;李清照说它,容华淡伫,绰约俱见天真;秦少游说它,有情芍药含春泪……我怀想着芍药花的形象和神韵,吟味着这些关于芍药花的佳句,很自然地就记念起一个芍药花样儿的女子——可儿,可卿,秦可卿。于是,我决定了,就先写写我和她的故事吧。
其实,我之所以要先讲讲我和可卿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