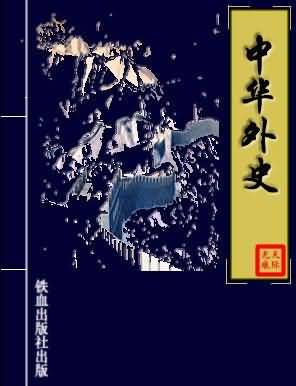春明外史-第20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抗战时期,他已入川,上海却出版了好几种黄色下流的小说,伪托他的名字,
他恨得不得了。这几种小说,泛滥在沦陷区,华北、东北,都非常流行。抗战胜利
后,他回到北京,预备追究,而书已绝版,找不着主名了,他只好拉倒。——现在,
这些小说已经很难找到。倘若有人能给编一张“伪书目”,也是很有意义的事。
他正式从事著作小说生涯,是1924年在《世界晚报》写《春明外史》起。那时,
他编一个副刊,一天写几百字小说,兼写杂文,还很从容。及至1925年《世界日报》
出版,他编两个副刊,一天写两篇小说,杂文照写,工作量加了一倍,他依然不在
乎。后来,又兼给《益世报》、《晨报》写小说,应该很忙了,朋友们却看不出,
只觉得他好像还是优游自在。一直到后来,他同时编副刊、写几篇小说,他嘴里从
没有吐出一个“忙”字。他规定了每天上午是写作时间,这是雷打不动的。如果约
稿太多,或者别有要事耽搁了,上午写不完,下午准得再写,非得完成事先订的计
划不可。他有坚强的毅力,严格的有纪律的生活,数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恐怕
这就是他的“成功秘诀”吧!
最初写小说,他是不用提纲的。脑子好像一台计算机,人物故事都储存在里面,
用到时就取出来,非常之现成。也不用复写纸,一支毛笔就是他的纺织器,每天织
出许多五颜六色好看的彩网。后来,约稿多了,经常一天同时在报刊上连载六七篇
小说,混淆缠夹了怎么办?平日不用提纲的,这时也不得不用了,至少不至把这一
部小说中的人物错到那一部,不至把这个人的故事接榫在那一个人的身上。有几部
小说,事先言明,一稿两用,分刊在南北不同地区的报刊上,这就有必要复写,于
是改用了铅笔。案头常常放着四五支削好的、半长的铅笔头。磨磨笔尖,削两下软
木,既是休息,也是娱乐,而归结于构思。
他每天的写作的能量总在五千字左右。在各报上连载的作品,合计也不超过这
个数字,所以他能应付裕如。有人奇怪:他每天都写那么多篇,头绪纷繁,纵有提
纲,也难免错乱,何以他能井井有条呢?其实,他每天只是写一篇,而不是同时写
那么多篇。今天这一篇,明天那一篇,轮流着写,周而复始。他的安排,有时也有
改变,但基本上写作数字是不变的。
他的写作态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香港有个刊物,说他常常一面打牌,一面
写小说;有时电话来催,他就在牌桌上写。这是没有的事。他对打牌根本无兴趣,
既不会打,朋友也不带他打。说起来,他小说中所描写的牌局,都欠缺精采,不是
没有原因的。如今倒有人把他和牌连在一起,简直是笑话。
他所写的,是他熟悉的人和事;遇有所不熟悉的也要他写时,他就不辞劳苦地
深入到生活中去。写《啼笑因缘》,背景是天桥,好多日子,他都泡在那里,沈凤
喜、关秀站以及沈三弦、关寿峰,就是从那里体验出来的。写关氏父女,原本不在
计划之内,是报纸主编人提出的要求:“加点‘噱头’吧,上海读者喜欢武侠的。”
他岂肯向壁虚造说什么“口吐白光”,他要塑出入情入理、有血有肉的形象。他曾
和我说过,他的祖父是有武功的,用筷子夹苍蝇是他亲眼所见。他写武侠,是有限
度的武侠,决不出人情之外。
报纸刊登长篇连载,最忌的是中断。有些作家偏偏老犯这个毛病,报上常见
“续稿未到暂停”字样。破坏了读者情趣,影响了编者安排,非常不好。只因连载
的长篇,动辄几十万字,甚至更长,作家们很少有全部写完后再拿去发表的,一般
是随登随写、随写随登,这就难保中间有个耽搁。他注意到这一点,总不让自己的
作品在连载中有一天脱节。在《金粉世家》的自序中,他说:“当我写到《金粉世
家》最后一页的时候,家里遭了一件不幸的事件,我‘最小偏怜’岁半的女孩子康
儿,她害猩红热死了。我虽二十分的负责任,在这样大结束的时候,实在不能按住
悲恸和书中人去收场,没有法子,只好让发表的报纸,停登一天。过了二十四小时
以后,究竟为责任的关系,把最后一页作完了。”一部连载五六年的作品,因为死
了女儿中断了一天,抱恨不已,他对于著作小说的事业心、责任感,看有多么强烈!
1937年在南京,1949年在北京,他得过两次重病,坐不起身,提不动笔,无可
抗拒地停止了写作。至于平常,有什么头疼发烧,那是不在话下,他总挣扎着照写
无误。抗战时期在重庆,敌机日来空袭,大家“入土为安”,都要下防空洞。他却
不管那些,空袭警报尽管响着,敌机在头顶上转,他写他的,只当没有那回事。有
一次,炸弹在他家附近开了花,他的夫人急了,跑出防空洞,要和他共生死存亡。
没法子,为了一家老小的安全,也只好下洞。就凭这样,他还是一听敌机飞过头顶
就回家去写;家人等解除警报的汽笛声响出洞时,他已写了几页纸了。
写小说是他的职业。人们有个通病,“吃一行,怨一行”,常会把自己的职业
当包袱,干久了时就感觉苦恼厌倦。他可不是这样。他是越写越来劲,没有个满足,
总想新写的一部超过所有的旧作。他热爱生活,把写作当成自己生活中最重要部分,
不仅仅是为了趣味。有一天不动笔,就忽忽如有所失,好像欠了一笔大债。他说:
“除了生病和旅行,如果一天不写,比不吃饭都难受。”大病初愈时,他又在写,
家里人和朋友都劝他,不要动脑子吧!他却说:“脑子总归要动的,不动在这里,
就动在别的地方。动在别的地方,岂不浪费吗?”他是1967年2月15日早上去世的,
14日的早上他还是坐在座位上写哩。
他的一生,就是写小说的一生!金字塔是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垒起来的,他的成
功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世间事业是没有幸致的。在写作的过程中,早期被老
先生们说成是不务正业,歪门邪道;后来出名了,又被青年人给他戴上这一派那一
派的“桂冠”,硬派他做“异教徒”。他不为这些讥评而有丝毫动摇。坚持写他的
作品。一百一十多部长篇,就从高压的石头缝中窜出来的。这种精神,难道不值得
人们的尊敬和学习吗?
五
对于张恨水的小说,从来就有一些不公正的误解。
其一是说:张恨水的小说是黄色小说。
黄色小说,意味着作品诲淫诲盗,荒诞绝伦。张恨水生平没有写过这样的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抗战期间,沦陷区里,有人盗用他的名字出版的,倒的确是黄色小
说。我们不能把“假张恨水”的黑锅叫“真张恨水”去背。五十年代,文化部曾发
出内部通报,说张恨水的小说属于一般社会言情小说,不是淫秽、荒诞的作品。当
然不是黄色小说。这是强有力的辩诬。
其二是说;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
鸳鸯蝴蝶派,指的是那些作家,专写才子佳人,男欢女爱,风花雪月,无病呻
吟,自命为“衷感顽艳”的作品。一般应用文言文,杂以诗词。那个流派,意志消
沉,脱离实际,是文学史上一股逆流。不幸的是,张恨水也被某些人纳入那个流派。
无庸讳言,张恨水初期习作,确实是走的这条路子。我们虽然没有见到那些作品,
而那些作品的题目却把信息告诉我们了。他自己也承认,“曾受民初蝴蝶鸳鸯派的
影响”。但是,仅仅根据这一点就说他属于那个流派,这就很不恰当了。因为当初
他走这条路子并没有走通,从正式发表长篇连载起,着眼于对旧社会的讽刺、谴责,
就和那个流派分道扬镳了。我们现在读到的他的作品,没有一部是符合那个流派的
特征的。当然,他的作品中,传奇性的爱情故事是占有一定的比重;同时,也应指
出,他写这些故事,都有特定的时代背景,揭露和批判封建、半封建的罪恶。我们
决不能说,凡是写爱情的小说都是鸳鸯蝴蝶派。那样,就会在文学批评史上造成一
片混乱了。他生前不服这样的“裁决”,曾经提出抗议:“‘五四’运动之后,本
来对于一切非新文艺形式的文字,完全予以否定了的。而章回小说,不论它的前因
后果,以及它的内容如何,当时都是指为鸳鸯蝴蝶派。有些朋友很奇怪,我的思想
也并不太腐化,为什么甘心作鸳鸯蝴蝶派?而我对于这个,也没有加以回答。我想,
事实最为雄辩,让事实来答复这些吧?”是的,作品具在,不难覆案。把这顶帽子
强加于张恨水,不足贬低张恨水,倒是抬高了鸳鸯蝴蝶派了。
第三是说,张恨水是礼拜六派。
《礼拜六》是在上海发行的一种文艺周刊,泛滥于二十年代。这个刊物所刊登
的作品,以小说为主,间杂一些毫无意义的所谓“游戏文章”,趣味低级。文字规
格,是旧体裁、旧形式。它的作者主要在江浙一带,成为一个无形的集团,当时视
为“海派”。那时正当新文艺萌芽时期,它是鸳鸯蝴蝶派之后另一股逆流,阻碍着
新生事物的成长。后来人们便把那一流派的作家及其作品,称之为“礼拜六派”。
有些人认为,张恨水也就是礼拜六派。我们知道:他人在北京,写小说是“单干户”,
不是靠别人吹捧成名的;他从来没有写像《礼拜六》上刊登的那些无聊作品;他大
量发表作品,是在礼拜六派已经衰歇之后。用这些来说明他不是礼拜六派,自然是
不够的,辨认一位作家属于哪个流派,还得看他的作品形式和思想内容,主要并不
在这些人事关系上。古之人,论流派不是往往把一些作家论定属于前几世纪的某一
流派吗?那么,我们检查一下张恨水的作品。
张恨水是章回小说作家。作为通俗文艺,必然采用习惯的大众口语,组织结构,
一切服从于传统的旧体裁、旧形式。在这方面,他和礼拜六派的作品、包括那些小
说在内,是近似的,或者说简直相同。不同之处,仅仅是艺术技巧,有高低之别罢
了。只根据这一点,辨认他是不是礼拜六派,容易模糊了眼睛,陷入了形式主义。
我们应该说,礼拜六派利用了旧体裁、旧形式;却不应该说,利用旧体裁、旧形式
的都是礼拜六派。
有人也许会问;从新文艺萌芽直到成熟、壮大,为什么张恨水不用新体裁、新
形式写作,却偏要和礼拜六派走同一的旧道路呢?关于这个问题,他有个明确答复。
1944年,他五十岁生日,在重庆,许多朋友祝贺他创作生活三十年。事后,他写了
一篇《总答谢》,其中说道:
……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
普通民众所能接受。正如雅颂之诗,高则高矣,美则美矣,而匹夫匹妇对之莫名其
妙。我们没有理由遗弃这一班人;也无法把西洋文法组织的文字,硬灌入这一批人
的脑袋。窃不自量,我愿为这班人工作。有人说,中国旧章回小说,浩如烟海,尽
够这班人享受了,何劳你再去多事?但这个有个问题,那浩如烟海的东西,它不是
现代的反映;那班人需要一点写现代事物的小说,他们从何见取呢?大家若都鄙弃
章回小说而不为,让这班人永远去看侠客口中吐白光、才子中状元、佳人后花园私
订终身的故事,拿笔杆的人,似乎要负一点责任。我非大言不惭,能负这个责任,
可是不妨抛砖引玉,来试一试。
这是他的抱负。一些作家薄章回小说而不为,市民层文化生活十分贫乏,他捡
起了这个武器,被人指斥为“异端”而不辞。他拥有广大读者。从他创作的动机和
取得的效果而言,应该被承认是一致的。有位很了不起的大作家,他的老母亲就爱
看张恨水的小说,他不止一次用高价去买张恨水的作品。老母亲说:“你为什么不
写张恨水”这样的小说给我看看呢?”这是文艺界流传的很有趣的故事。难道说那
位大作家的作品不如张恨水吗?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引出这个故事意在说明,进步
作品的新体裁、新形式,在当时只能适合于知识分子,而为市民层所不能接受。所
以1930年“左联”成立时,就有“创作革命的大众文艺”的号召。鲁迅说:“应该
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人家能懂爱看。”冯雪峰
(洛扬)说:“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利用这种大众文艺的旧形式,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