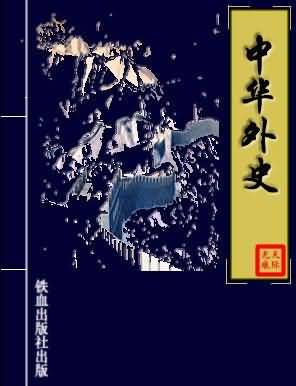春明外史-第19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李冬青在屋子里和杨杏园说话时,富氏兄弟几次要进来,又退了出去。富家驹
站在窗子外,把身子一闪,只见李冬青在地板上跪下去,很是诧异。及至她起来时,
只见她伏在床沿上,已哭成泪人儿了。便隔了窗子问道:“李女士,杨先生怎么样?”
李冬青原还不曾放出声来。有人一问,就哽咽着道:“他……他……他去了。”只
这一声“去了”,再禁不住,就放声大哭起来。富家驹嚷道:“你们快来啊,杨先
生过去了。”本来这里的人,都提心吊胆,一听说杨杏园死了,大家都走进房来。
连听差厨子车夫都站在屋子里,望着床上垂泪。富氏兄弟,总算是学生,就各念着
愁容,对杨杏园三鞠躬。接上在屋子里乱转,不住跌脚叹气。听差忙得去打电话,
到处报告。还是厨子说:“大家别乱。问问李小姐,杨先生过去多少时候了,也好
记个时辰。”李冬青道:“大概有十分钟了。他是清清楚楚,放心过去的。你们瞧,
瞧,瞧!他……他……他不是象参禅的样子吗?”说时,用手指着那涅槃的杨杏园。
富家驹道:“我以为他学佛,是可以解除烦恼的,不料他先生竟是这样撒手西归。”
说毕,也是牵线般的流泪。一面掀袖口看了一看手表说道:“正是十点刚过去,十
二时辰之末。”一言未了,只听院子外,有一种颤动的声浪,由远而近。喊道:
“杏园老弟,好朋友,你你你就这样去了吗?”那何剑尘满脸是泪珠,跌跌倒倒,
撞了进屋来。他一见杨杏园这样,反不能言语,就走上前执着富家驹的手,相视放
声大哭。这一哭,李冬青更是伤心了。大家哭了一阵子,何剑尘见杨杏园的尸身,
还是坐着,因对李冬青道:“他虽皈依佛教,究竟未曾出家,这样不成样子。”李
冬青点点头,大家就走上前,牵开被褥,将杨杏园的尸身放下。
这个时候,一班故友,男男女女都来了。何剑尘有事走出院子去,顶头碰到吴
碧波。电灯光下,见他愁容满面。何剑尘叫了他一声,他倒放声哭起来了。何剑尘
牵了他的手进屋,他看见纱帐低垂,里面躺着个其白如纸的面孔,不住顿脚问何剑
尘道:“你是什么时候接到电话的?”何剑尘道:“我没有接到电话。我编稿子的
时候,只是心神不宁,我心里一动,莫是杏园不好吧?于是我丢了事不办,特意走
来看看。不料一进门,就听到里面一片哭声,人已经过去多时了。”吴碧波道:
“他的后事怎么样呢?”何剑尘道:“他是一点积蓄没有。但是有我们这些朋友,
还有两家报馆东家,几百元是不成问题。可怜他卖文半生;殡殓虽不必从丰,也不
可太薄。也用不着阴阳生僧道之类,也不用得焚化纸钱,只是给他开一个追悼会就
行了。他虽没有遗嘱,他生前的论调,就是这样。照他的主张去办,我想他英灵不
远,一定同情的。”李冬青不等吴碧波答话,就插嘴道:“就是这样好。依我说,
连杠夫都不用。只用一辆长途汽车,把灵柩送到义园,然后由朋友抬到地上去。我,
我,我就愿抬一个。我对他是无可报答,只有这一点敬意了。”说着又哭起来。何
剑尘道:“这话很对,我们也主张这样办。这些后事,我们朋友都竭全力去办,你
不要挂心,我们总会办得好好的。”李冬青什么话也不说,蓬着一头的头发,坐在
杨杏园素日坐了写字的椅上,只是流泪。大家分头去办衣衾棺木,闹了一夜到天亮,
大家都乏了。李冬青哭得成了一个傻子一样,什么话也不说,而且嗓子也哭哑了。
说一句话,一大半是嗳嗳之声。她把两只胳膊,放在椅靠上,十指互相交叉,头偏
了靠着右肩,就是这样望了床上,目不转睛。何剑尘见她那种样子,脸子黄黄的,
煞是可怜。便道:“李女士由汉口来,在火车上已经累了两晚。昨晚又是哭了一宿,
精神实在困倦了,不如去睡一会子罢。”李冬青摇摇头。何剑尘道:“这时没有什
么事,不如休息一会。回头寿材来了,就可以预备收殓,应该由李女士在旁边照应,
所以这时还是先睡的好。”李冬青一听这话也是,现在也顾不到什么仪节,就在外
面沙发椅子上斜躺下。不多一会工夫,就睡着了。醒来时,已经挤了满屋子的人,
何太太和朱伯桐女士也来了。
李冬青和朱韵桐还是别后初见面。都不能有笑容,只是拉了一拉手。朱韵桐叹
气道:“想不到杨先生就是这样下场。前几天我们在西山请客,他也到了,还逗着
我们说笑话呢。”李冬青昨天曾听到何太太说,朱韵桐和吴碧波订了婚,现在她左
一句我们,右一句我们,当然是兼指吴碧波而言。人家多们亲密。也叹了一口气道:
“人生如朝露,真是一点意思没有。我现在觉得他学佛,大有理由在里面了。”何
太太和朱韵桐极力的劝她一顿,她也觉心里宽慰一点,偶然站起来,只见七八个人
吆吆唤唤。抬着一口棺材,直送进里面院子里来。李冬青看见棺材,不由得又是一
阵心酸,泪珠向下直滚。何太太拉着她的手道:“人已去了,伤心也是枉然。你不
要这样闹,苦苦的伤坏了自己的身子。本来呢,大家相处得很好的人,忽然分手起
来,心里自然难过。莫说是你和杨先生象手足一样。就是我们,也觉可……”可字
下还不曾说出,劝人的也哭起来了。那屋子里,何剑尘早已指挥人将杨杏园殓好。
本来用不着等时候,所以即刻就预备人格。吴碧波悄悄对何剑尘道:“入棺时候,
我看最好是避开李女士。不然,她看见把人送进去,格外伤心,也许出什么意外。”
何剑尘道:“这个时候,要她离开这里,是不可能的,有什么法子,让她避开呢?”
吴碧波道:“我倒有个法子。可以把杏园的书件文稿,一齐送到前面屋子里去,请
她去清理出来。就说我们要把他的得意之作,列个目录,登在明日的报上。如此一
说,她必然尽心尽意去清理的。那时候就可以轻轻悄悄把杏园入棺了。”何剑尘道:
“很好很好,就是这样办罢。”于是把话对李冬青说了,还要朱女士何太太二人去
帮忙。
李冬青信以为真,在杨杏园屋子里,搜罗了两篮子文件,到前面去清理。李冬
青认为这事很是重要,仔仔细细的在前面料理。检了约有一个钟头,忽然听到隐隐
有一片啜泣之声。心里一动,忽然想到要到后面去看看,于是就走出来。何太太一
把拉住道:“那面乱七八糟,人很多,你不要去罢。”这样一来,她更是疑心,把
手一摔,向后院子就跑。走进那篱笆门,就看见上面屋中间,用板凳将棺材架起,
许多朋友,围了棺材流泪。几个粗人抬了棺材盖,正向上面盖住。李冬青忘其所以
了,将手一举,乱嚷道:“慢着,慢着。”一面如飞似的就向里面跑。不问好歹,
一头就向棺材头上撞去。何剑尘见她跑进来的时候,情形不同,早就防备着。等她
向前一奔,身子向前一隔,李冬青这一撞,正撞在何剑尘胸口上,把他倒撞得倒退
了几步。何太太和朱女士都赶上前,各执着她一只手,苦苦的相劝。李冬青哭着道:
“何先生吴先生都是朋友呀,为什么不让我和他最后见一面呢。打开盖来啊,打开
盖来呀,我要看一看。”说时,尽管向前奔,别人哪里拉得开。吴碧波拦住道:
“李女士,您别忙,请听我两句话。这话,我也对杏园说过的,就是亲在不许友以
死。李女士这样的苦恼,就不替老太太想吗?见一面的话,原无不可。但是要知道,
不见是可惨,见他睡在那里面,更可惨了。我们都不忍多看呢,况是李女士吗?”
这几句话,倒打入了她的心坎,她把两只手掩住了眼睛,猛然一转身,跑进里面屋
子里去,伏在桌上放声大哭。大家和杨杏园都是朋友,自然都不免有些伤感,所以
李冬青那样哀哭,不但禁止不住,引得各人自己反哭泣起来。混闹了一日,大家都
疲乏已极,一大半朋友,都在这里住下。因为李冬青不肯走,朱韵桐女士也在这里
陪着她。
又过了一天,正中屋里已布置了灵位。棺材头上,便挂了李冬青所献的加大花
圈。花圈中间,是原来杨杏园的半身相片。屋子半空,正中悬了一根绳,挂着杨杏
园自挽的两副对联。灵位前的桌子上,挂着白桌围,上面只有一个古钢炉,焚着檀
香。一只青磁海,盛了一杯清茶。一列摆着四大盘鲜果,两瓶鲜花。李冬青穿了一
件黑布夹袄,一条黑裙子,一身都是黑。蓬蓬的头发,在左鬓下夹着一条白头绳编
的菊花。她本来是个很温柔沉静的人,这样素净的打扮,越发是凄楚欲绝。她不言
不语,端了一张小方凳,就坐在灵位旁边。两三天的工夫,就只喝了一碗百合粉,
两碗稀溜溜的粥,不但是精神颓废,而且那张清秀的面孔,也瘦得减小一个圈圈儿
了。这日下午,何太太自家里来,看见正屋里那种陈设,旁边坐了这样一个如醉如
痴的女子,也替她十分可怜。走进来,李冬青望着她,只点了点头。一手撑着灵桌,
托了腮,依然是不言语。何太太道:“李先生,我看你这样终日发愁,恐怕会退出
病来。今天下午,到我家里去谈谈罢。”李冬青摆了一摆头,轻轻的说道:“我一
点气力没有,懒于说得话,我不去了。”何太太道:“我是天天望您到北京来。好
容易望得您来了,一下车,就到这儿来了没走。我有许多话要和您说,可是一句也
没有谈上。您瞧,我可也门得难受。您就瞧我这一点惦记您的情分,也不好意思不
去。”李冬青明知道她这话是激将法。无奈她说得入情入理,未便过于拂逆。便道:
“不是我不和你去谈谈。但是我丧魂失魄,语无伦次,要我谈也谈不上来的。”何
太太道:“就是因为您精神不好,才要您去谈谈。也好解一解闷。”
李冬青心里虽然十分难受,表面上也不能不敷衍何太太。只得和朱女士一路,
一块儿到何剑尘家去。当时也不觉得怎样,不料在吃晚饭的时候,李冬青手上的筷
子,落在桌上,人已坐不住,就向旁边一歪,倒在地板上。何太太和朱女士连忙过
来将她搀起,只见脸色白里变青,双目紧闭,嘴唇带了紫色。何太太跳脚道:“不
好哟!不好哟!”何剑尘道:“不要紧,这是她两天劳累过分了,人发晕。”就叫
老妈子搀她到床上去安息,一面打电话叫医生来看病。据医生说,也是不要紧,不
过精神过于疲倦,要多休息几天。何剑尘是格外体谅,自己搬到书房里去住,却在
何太太隔壁屋子里,另外设立了一张小铁床,让李冬青在那里睡。
李冬青当天晕倒以后,到晚上八九点钟,也就清醒过来。无如人是累极了,竟
抬不起头来,眼睛里看的东西,仿佛都有些晃动,只好微微的闭着眼。何太太几次
进房看她,见她闭着眼睡着,也就不作声。不过枕头上湿着两大片,她的眼角,也
是水汪汪的。何太太叹了一口气道:“也难怪人家伤心。”说到这个字回头一见她
两颗泪珠流到脸上,就不敢作声了。当时拿了一点女红,就坐在这屋子里做,陪伴
着她。一直做到十二点钟,李冬青才缓缓的睁开眼来。何太太便问道:“李先生要
喝点茶吗?”李冬青摇摇头。“眼睛却尽管望着窗户出神。何太太问道:“李先生,
你望什么?”李冬青道:“很奇怪,我似乎听到有人在窗户外面叫我的名字。”何
太太道:“没有,谁有那么大胆呢?”李冬青道:“刚才有谁进了屋子吗?”何太
太道:“没有。我坐在这里也没有动身。”李冬青道:“那大概是梦了。我看见杏
园走进来,摸着我的额角。他说病不要紧,不过小烧热罢了。他还是那个样子……”
李冬青只见何太太听了,脸色都呆了,只是睁着眼看人。她想起来了,她是害怕,
就不向下说。何太太道:“怎么样,杨先生说了什么吗?”李冬青道:“我看你有
些害怕,我不说了。”何太太道:“怕什么?我和杨先生也熟得象家里小叔子一样。
只因是刚才李先生说话,我也仿佛听见有杨先生说话的声音,所以我听下去呆了。”
李冬青道:“咳!人死如灯灭,哪里还有什么影响?这不过我们的心理作用罢了。”
何太太见她说话渐渐有些气力,就让她喝了一碗稀饭。何太太因为大夫说,李冬青
的病并不怎样重要,所以也不主张她进医院。以为在家里养病,究竟比在医院里便
利,而且也不至于感到孤寂。李冬青自己是精神衰败极了,哪管病在哪里养,所以
静静的在何家养病,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