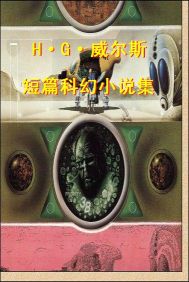外国中短篇科幻小说1000篇 (一)-第3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上一次我来到这里,发现的是一个死人。我于是急忙闯了进去。
丽莎·傅正坐在电脑前的一只钢琴凳上,我只看到她体形轮廓:背脊笔直,棕色的双腿像莲座似的盘着,手指悬在键上,而她面前的荧屏上字符在迅速地映现着。她抬起头来,闪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
“有人告诉我,你的名字叫维克托·埃帕菲尔。”她说。
“是的。呃,门开着……”
“天太热,”她合情合理地说,一边拎着颈旁的汗衫,上下扇动着,就和你在大汗淋漓时的动作一模一样,“有什么事吗?”
“没有什么事,真的。”我走在暗处,脚下碰到一样东西。是只纸板盒,大而扁平,装比萨饼的那一种。
“我正在准备晚餐,看上去够两个人吃的,于是我想你也许……”我突然发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于是下面的话也就咽了下去。我原以为她穿着短裤。而事实上,她只穿了一件汗衫和极短小的粉红色游泳裤。她看来倒并不感到难堪。
“……你愿意和我共进晚餐吗?”
她笑得更欢了。
“好极了,”她说。她轻松地收起盘着的双腿,跳下地来,和我擦肩而过,身后留下汗水和香皂的气味,“稍等片刻。”
我朝屋子四周又扫了一眼,但是脑中却总想着她。她喜欢百事可乐和烘馅饼,屋里就堆着好几打空瓶。她膝部和大腿上有个深深的伤疤。烟灰缸是空的……她走路时小腿上的长长肌肉鼓得结实有力。克鲁格想必抽烟,而丽莎不抽。她腰背部长着纤细的茸毛,在电脑的绿光下隐约可见。我听到浴池里放水的声音,又看了看一本黄色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的书写体我几十年未曾见过。我又闻到了肥皂的香味?又联想起她那黄褐色的皮肤和从容的步伐。
她出现在门厅里,紧身牛仔裤、拖鞋和一件新的T恤衫。那件旧的汗衫上面作的是巴勒斯办公系统的广告,而这一件印着米老鼠和白雪公主城堡,还散发出新漂白棉布的气味。米老鼠耳朵正搁在她那大得出奇的乳房的上峰。
我尾随着走出了大门。廷克贝尔城堡在她汗衫后背衬托下,在尘埃里闪闪发光。
“我喜欢这间厨房。”她说。
如果没有人对你说上一句这样的话,你对这个地方是不会认认真真地看上一眼的。
厨房是个能够体现时代风貌的斗室,简直好像是从五十年代《生活》杂志某一期上照搬下来的。一台肩头隆起的弗里吉代尔牌电冰箱,人们就叫它弗里吉代尔,犹如叫皱纸手帕为克里耐克斯,称可卡因为可卡一样,商标成了商品的属名。这些都是同一时代的产品。桌面砌着黄色瓷砖,是现在浴室里才能找见的那一种。整个地方没有一块防蚀防热的热固塑料。没有使用洗碟机,但是有一个放碟子的网夹和双缸洗涤槽。这里没有电动开罐刀,没有烹饪手册,没有厨房垃圾压实机或微波炉。整个房间里最新的玩意儿还是用了十五年的食品搅拌器。
我的手艺不错,挺喜欢修修补补。
“这面包好吃极了。”她说。
这是我亲手烘的。我望着她用一片面包刮着碟子,而她则问我可否再来一份。
用面包擦干净碟子是个坏习惯,这我完全知道,但我并不介意,我自己也是这么干的,而更主要的原因却是她的举动并无过失。我把蒸锅里的菜给她添了三回,当她饱餐之后,她的碟子几乎不必去洗。我勉强抑止住一种馋涎欲滴的感觉。
她又背靠在椅子上,我则在她的杯子里斟满白酒。
“你真的不想再吃些豌豆了?”
“我再吃就要胀破肚皮了,”她心满意足地拍了拍肚皮,“埃帕菲尔先生,非常感谢。我很久很久没有尝过家里做的饭菜了。”
“就叫我维克托吧。”
“我就爱吃美国食品。”
“我不知道竟会有这种情况,我是说,不像中国人或者……你是美国人,是吗?”她笑而不答。“我的意思是——”
“我知道你的意思,维克托。我是个美国公民,但不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对不起,等我一会儿。我知道吃完就离开桌子是不礼貌的,但是我的牙齿里夹着矫正钢丝,吃了东西之后必须立刻刷牙。”
我在收拾桌子的时候,能够听到她刷牙漱口的声音。我往洗涤槽里放水,洗起碟子来。她很快就过来帮忙,抓起一条洗涤巾,把网夹里的餐具擦得干干净净,而我却老劝她别动手。
“你独自一个人住在这里?”
“是的,父母故世后我一直一个人生活。”
“结过婚吗?如果不该问,你就直说。”
“没关系,我没结过婚。”
“没有女人在身边还能这么干,你真行呀!”
“熟能生巧嘛。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说吧。”
“你是哪里人?台湾人?”
“我会说各种话。在家里,我说洋泾浜美语,但我来到这里之后就改正了过来。我也说蹩脚的法语,四五种中国方言,越南脏话,还能用泰国语叫喊‘我要见美国领事,快快,你!’”
我笑了。她说话的时候,嗓音很粗。
“我在这儿已经八年了。你猜得出我是哪里人了吗?”
“越南?”我试了一下。
“我来自西贡街头,真的,或称胡志明市,那是穿睡衣的头头给它改的名字。让他们的酒发臭,让他们的屁股扎满参差不齐的竹签吧。原谅我用了法语。”
她窘迫地低下了头。极其轻松愉快的谈话很快就变得十分令人难堪了,我感到她那内心的伤痕至少和我的一般深。我们两人于是避开了这个话题。
“我还以为你是日本人呢。”我说。
“是颇费猜测的吧?我总有一天会全都告诉你的。维克托,穿过那边房门是洗衣间吗?有洗衣机吗?”
“是的,有洗衣机。”
“如果我拿一大包衣服来洗,不会太麻烦吧?”
根本谈不上什么麻烦。她有七条褪色的牛仔裤,其中有几条的裤腿已经剪掉,外加二十四件T恤衫。若不是内衣饰边,简直都是男孩子的衣服。
我们走到后院,在夕阳的余辉下坐着,后来她又想参观我的花园。那个花园我倒总是十分引以自豪的。我身体健康的话,每天都要在那儿干上四五个小时,一年到头都是这样,一般是在上午。你在南加利福尼亚完全能够这样干。我有一小间自己盖的玻璃暖房。
尽管花园眼下的景色不是最美,但是她却十分喜欢。这个星期大多数时间我都躺在床上或者泡在浴池里,故而花园里的野草已向四处蔓延了。
“小时候,我们家也有一个花园,”她说,“我在稻田里还躺过两年。”
“那和这里一定是迥然不同的。”
“当然罗,害得我好几年都不想吃米饭。”
她发现了蚜虫的侵扰,所以我们蹲下身去剔除它们。她蹲的姿势是亚洲农民式的,前后左右都可自由活动。这种姿势我记得非常清楚,却怎么也学不会。她的手指纤长,指尖很快就被捏死的蚜虫染得碧绿碧绿的。
我们东拉西扯地闲聊着,我不记得话题是怎么转的,然而我把自己在朝鲜打仗的事情告诉了她。我也知道了她现年二十五岁,凑巧得很,我们两人的生日相同,因此再过几个月,我的岁数恰好是她的一倍。
只有当她说起喜欢烹调的时候,克鲁格的名字才重被提起。她在他的住宅里是无法烧饭煮菜的。
“他车库的冰箱里装满了冷冻餐,”她说,“他有一只碟子,一把叉子,一只调羹和一只玻璃杯。他的微波炉是市场上最好的货。就这些。他厨房里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她摇了摇头,又捏死一只蚜虫,“他是个古怪的花花公子。”
她洗完衣服的时候,已经暮色深沉,几乎一片漆黑了。她把衣服装在我的柳条篮里,我们随后提着篮子走向晒衣绳。这简直像做游戏一样,我每抖开一件T恤衫,总要思考一下上面的图案和字符。有时候我猜对了,有时候却猜错了。图案有摇滚乐队、洛杉矶地图、《星际旅行》上映的拍卖品……真是五花八门。
“什么是L5社会?”我问她。
“想在太空里建造那些了不起的大农场的人们。我问他们是否打算种稻子。他们说,零度的天气种稻子不够理想,所以我就买了那件T恤。”
“这种衣服你一共有多少?”
“呵,该有四五百件。一般穿上两三回就扔掉了。”
我拿起另一件汗衫,里面掉下一只胸罩。这种胸罩和我年轻时代的姑娘们用的不同。它薄得透明,但很实惠。
“喜欢吗,美国佬?”她的嗓音很粗,“你真该见见我的妹妹。”
我瞥了她一眼。她的脸色突然阴沉了下来。
“维克托,对不起,”她说,“你不必脸红。”她从我手中接过胸罩,夹在晒衣绳上。
她一定对我的神色有了误解。不错,我有点窘,但奇怪的是我也暗自高兴。长期以来,人们只叫我维克托或者埃帕菲尔先生。
第二天的邮件里有一封芝加哥某律师事务所发来的信件,谈的就是那笔七十万美元的款子。信上说,钱是由1933年建立的特拉华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给我养老的,而且我的父母也是该公司的发起人。某些长期投资的票据业已到期,所以我可以说是发了一笔意外的大财。可我银行里现在的存款还付不起这笔大财应交的税呢!
乍看起来,这真是可笑。我父母根本就没有什么股份,我也根本不想发那个财。如果我能够发现克鲁格是偷了谁的,我会原封不动地如数奉还。
我决定,明年这个时候如果我还没进监牢,一定把这笔钱全部用于慈善事业。也许去拯救鲸鱼,或者支持L5社会。
上午在花园里忙碌了一阵,又到菜场买了一些新鲜的牛肉末和猪肉末。我把买来的东西放在可折合的网篮里,提着它高高兴兴地回家。当我在那辆银色弗拉里轿车前面走过的时候,我还笑了笑。
她没有过来取衣服。我从晒衣绳上一件件收下,折好,然后去敲克鲁格的大门。
“是我,维克托。”
“美国佬,请进。”
她还呆在老地方,但这一次衣冠整齐。她对我微微一笑。当她看到放着衣服的篮子,就拍了一下额头,赶忙上前接了过去。
“对不起,维克托。我只想——”
“放心吧,”我说,“不费事。这也给了我一个机会来问你一声,愿不愿意再和我共进晚餐。”
她的脸色有些细微的变化,但是很快就被掩饰了过去。也许她并不像嘴上说的那么喜欢“美国”食品,也许问题出在烹调上。
“当然,维克托,我太乐意了。让我来动手吧。你为什么不撩开窗帘?这里简直像个坟墓。”
她匆匆地走开了。我望了望她用的电脑,荧屏上几乎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单词:做爱—P。我估计是个打字错误。
我拉开窗帘,正巧看见奥斯本的汽车停在路边。丽莎回来时,已穿了一件新的T恤,上面印着《霍比特人的变化》,还画着一个矮胖的、脚上长满毛的人。她向窗外望去,正好瞧见奥斯本走上过道。
“呵,好一个华生,”她说,“警察局的。务必请他进来。”
她的口气不甚友好。奥斯本进屋的时候,对我射来怀疑的目光。我忍俊不禁。丽莎坐在钢琴凳上,脸上不露一丝表情。她无精打采地歪着身体,一只胳膊搁在键盘旁。
“我说埃帕菲尔,”奥斯本开始说,“我们终于弄清了克鲁格是何许人也。”
“帕特里克·威廉·加文。”丽莎立即接口说。
奥斯本听了目瞪口呆,好一阵之后才闭上了嘴。但是他随即又把它张开了。
“你究竟是怎么发现的呢?”
她懒洋洋地抚弄着身旁的键盘。
“这个名字今天上午传到你办公室的时候,我当然也听到了。在你的电脑里藏有一个小小密探程序,你的电脑每次提起克鲁格的名字,它就会给我通风报信,可我不需要通风报信。我五天前就知道他的真姓大名了。”
“那为什么……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你并没有问过我呀!”
他们怒目对视了一阵子。我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才导致现在这个局面,但有一点是明摆着的,他们之间不存在一丝好感。丽莎此刻占着上风,看来正沾沾自喜呢。她随后朝荧屏瞥一眼,露出惊讶的神色,迅速按了一个键钮,荧屏上的字符立即消失。她向我投来令人费解的目光,然后又把脸转向奥斯本。
“请回忆一下,你请我来是因为你自己的人摆弄这机器只能听到一片撞击声。我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个系统的电脑损坏,简直像得了紧张症。机器大部分不能运转,而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