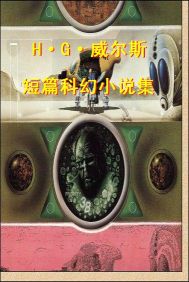外国中短篇科幻小说1000篇 (一)-第19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多余的。
我们来到了被达克称作“腹部”的地方。这是一个像机库一样的巨大舱室,被一片片巨大而透明的肌肉所分隔,里面还有一丝丝肥肉,像大理石上的花纹。墙壁凹陷处还吊着一只只像水袋一样的东西,里面的液体是云一样的绿水。
我戳了戳一只口袋。它荡起了微波。我看见里面有漂浮的水草、游动的鱼、爬行的蜗牛,还有一些小鱼。“简直是个水族宫。”我说。
“是的。一个微型海洋。那种绿色植物叫羊角草:无根,可以食用。你还可以看到海蜗牛、剑尾鱼,及各种微生物。这是一个完全的、自给自足的生物圈。这些生物都是从地球上弄来的。你看,我们一边和高科技的埃克希里人作战,一边又在战船中心装几滴原始的水。你不觉得这很浪漫吗?”
“怎么才能不让它们繁殖得过多过快?”
“水草可以自我控制。蜗牛以死鱼为食。鱼通过吃它们的幼仔来控制数目。”
估计我脸上的表情不太兴奋。
“你太神经质了。”她严厉地说,“我不记得我以前是那样的。”
我们很快穿过飞船那奇妙的内脏。
事实是,我一直在努力使自己保持镇定。肯定还会遇到一些令人惊讶的事。人类本来就不是被设计来承受这些矛盾的,诸如末来的自我啦,未出生的婴儿啦,等等。
然而,我最难以接受的还是法庭质询。这次质询是古老而传统的海军部质询程序和委员会法庭辩论方式的结合。瓦森委员是主席,我既当起诉官,又当书记员。法庭的其他成员——法官和陪审员组成的评判小组——由一些委员和海军部的官员及平民担任,甚至还请了一位学者以示公正。在我看来,这标志着海军部和委员会之间的某种政治妥协。
法庭质询只是第一步。如果指控成立的话,达克将面临很多麻烦,很有可能上军事法庭。所以,这次质询相当关键。
这些指控——其实是对未来的我的指控——非常不利:玩忽职守致使海军部战船陷入危险;执行任务不力;违抗命令贻误战机;怂恿船员违背教义……
而且证据确凿。有当时的情景虚拟再现为证。它是基于“火炬”的记录以及从船员身上提取出来的记忆液制作出来的。还有很多证人,大都是“火炬”的受伤者。但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证词会不利于她,真要知道了这一点,他们准会大为气恼。所有的人都表达了对达克舰长的忠诚和尊敬——但在委员们的眼里,这种偶像崇拜只能给他们的舰长惹来更多的麻烦。
到此为止,所缺的只有动机了。我始终不明白达克为什么要那样做。
是鄙视她,还是为她辩护?我很犹豫——我一直感到我和她是一对难以排解的矛盾。她也有这样的感觉。有时她对我很不耐烦,就像对一个刚招募的新兵;有时她又试图把我保护在她的羽翼之下。看得出她也很不自在,因为我使她想起了她自己曾经那么微不足道。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同一个人的两个阶段的话,我们就不会完全相同。很久以前,她曾经是我;我注定会在将来成为她;这就好像她提前为我付了账单。
我请求休庭,因为需要花点时间去了解达克。必须去了解她——虽然我很不愿意卷入她那黯淡的未来。
她把我带进一个以前没来过的舱房。一根半透明的、紫红色绳子做成的柱子占满了整个空间,上面交叉支撑着一些软骨。一股臭氧的恶臭直冲鼻子。
我突然明白了自己在哪里,“这是超光速推进舱。”
“是的。”她边说边碰了碰那些纤维,“很壮观,对吗?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推进舱肌肉时的情景——”
“你当然记得。”
“为什么?”
“因为那就是现在呀。”我垂头丧气地想,我总有一天会站在这间房子里的另一边,回忆我自己第一次看到推进舱肌肉时的情景,“难道你不记得了?你是我,刚满二十岁,遇到了——你?”
她的回答使我迷惑不解。“事情不是那样的。”她瞪着我,“你明不明白我是怎样回到过去,来瞪着你这张长满青春痘的脸的?”
“不知道。”我不情愿地说。
“用的是托尔曼法。”她看着我的脸,“每一艘超光速飞船都是一台时光机器。明白了吧,少尉。只是狭义相对论。就连‘托尔曼’也是死去很久的前毁灭时期科学家的名字。这东西四岁小孩都会学。”
我耸耸肩。“长大后你就会忘掉的,除非你想当航天员。”
“就这种态度,还有雄心当舰长?”
“我不想。”我慢慢地说,“我没有当舰长的野心。”
她停了一会儿,又说:“如果你和超光速飞船开战,时间就会移动,你必须预料到这点。这么说吧……并不存在真正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在。比如说这儿是午夜。我们距离基地是一光分。那么在529基地上,你那满是跳蚤的兵营里的时间是多少?如果你能有一架望远镜的话,看看地球上的时间又是多少?”
我想了想。基地上的图像要到达我们这儿,以光速计,需要一分钟。所以图像会在午夜前一分钟呈现……“我懂了。但如果只是因为信号传输时间延迟的话,你完全可以调整一下,定出一个标准的‘现在’——能做到吗?”
“如果每个人都一动不动,就可以做到。但是,想想这个嘎嘎作响的、正在以半光速的速度移动的老旧飞船吧。连你也听到了时间在它体内膨胀的声音。如果从基地上看,我们的时钟慢了。从我们这儿看,他们的时钟慢了。
“好好想想吧。整个舰队都在以不同的速度行动,时间当然会不同。而且永远都会不同。知道吗?从总体上看,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有事件——就像一幅巨型图画上的小点。轴线就是空间和时间。这就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事件像鱼一样到处游动着;离我们越远,游动得越快。所以,无论在基地上,在地球,或者任何其他的地方,都不可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发生在你所谓的‘现在’。
“正因为如此,历史才变得模糊不清。自然,地球本身是有一定历史的,基地同样也有历史。地球也许离我们有上万光年,因此不能以基地的日期来计算地球上某个事件的日期;它们可能会相差上千年。你甚至可以在基地上重新看到地球的过去。
“现在你明白了吧,超光速把一切都搅得乱七八糟。人员伤亡多大?这是超光速控制的。有了超光速,你就可以回溯事件。有了超光速飞船,你可以在时空图上随意跳跃。我驾驶着超光速飞船到了‘雾’。我到那儿之后,从我的角度看,基地这儿这几十年的历史一片模糊……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只是跳回发生在我出发之前的某个事件。如果谨慎使用托尔曼法,我们还可以把很多资料,如飞行记录,战斗日志等带回过去。”
我恍然大悟,“你是说,这是一个把战争情报送回过去的办法?”
“那当然啦。如果情报表明有胜利的可能性,就得抓住这个机会。还有比这个更聪明的办法吗?这些都由海军部去协调。我们得抓住每一个有利的战机。”
“但埃克希里人难道不会采取同样的办法吗?”
“当然会。诀窍是想办法阻止他们。过去和现在的混合依赖于相对速度。关键是要想办法设计出一场有利于我们的战斗。”达克狡黯地笑笑,“这是一场智慧的较量,我们略胜一筹。”
我想竭力抓住重点。“那么,”我说,“给我透露一点未来战争的情报吧。告诉我,你们是怎样突破冲锋线的。”
她瞪了我一眼,随后在舱房里踱来踱去,几乎能听见推进舱的脉搏跳动发出的奇怪声响。
“撤退命令下来的时候,我们刚刚遭到了重创。你能体会那是什么感受吗?第一反应是震惊,搞不懂这样的情况怎么会发生在你的身上。然后是不相信、愤怒。飞船是你的家——也是船上的一员。这就好像有人入侵了你的家园。船员们都坚守着岗位,尽忠职守。没有恐慌。是的,只是有点混乱,但没有恐慌。”
“你决定违抗撤退命令。”
她看着我的眼睛,“我必须立即作出决定。于是我们继续向前,冲过了冲锋线,一直到达埃克希里人控制的中心。经历了十几次炮击,我们的战船已经是浑身战火,鲜血淋漓。我们就这样和他们战斗着。他们比我们聪明,也比我们强壮。但我们只是不顺一切地冲过去。既然他们把我们看作歹徒,我们就要作出歹徒的样子。”
“你发射了‘日出’。”
“哈玛是驾驶员。”就是我那没有出生,甚至还没有怀上的孩子,“他驾驶着一枚单极鱼雷:一种新式武器。埃克希里人的每一个‘糖块’都是一个立方形的要塞,绵延几千米,有边沿和转角。我们在它上面凿开一个洞,打进去了。
“我们也挨了一顿痛打,遭受了一次次炮击。
“为了躲避爆炸,我们不得不撤到外面的甲板上。人们爬在船壳上,像挤在垃圾上的苍蝇。一边拿着武器,一边抓住船上的各种支柱和救生索什么的,拼命往上爬。”她的脸抽搐着,“一些人被救生舱救起来了,但还是有上百人失去了生命……你知道为什么把这种鱼雷命名为‘日出’吗?因为它是地球上的东西。埃克希里人居住在太空,根本没有白天和黑夜之分。每一个黎明都是我们的,而不是他们的。你不认为这个名字非常合适吗?你真该看看‘日出’飞行员走上甲板,准备发动进攻时的场面。”
“像哈玛。”
“鱼雷艇从泊位驶出来。整个船队,包括民用船只和海军部的船只,都来为它们送行。当驾驶员登上‘日出’的时候,船员们让出一条通道,呼喊着他们的名字。”她微笑着说,“你看见他时,你的心都会跳出来。”
我努力使自己保持平静,“也就是说,这些驾驶员被偶像化了。”
“上帝,没想到我从前竟然是这么一个混帐。战争中有比遵守教条更重要的东西。‘日出’驾驶员当然是人类大扩张中涌现的英雄典范。短暂的生命发出耀眼的光芒——‘日出’驾驶员用实际行动实践了这一点。”
“那么,”我小心翼翼地说,“你是船员们眼中的英雄?”
她绷着脸。经过那么多年,皱纹已经刻进了我的肌肤。“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太老了,很惭愧我还活着。听我说,十年之后你将参加一场发生在中子星附近的战争,叫‘开普勒之战’。那场战争就是你的船员为什么尊敬你的原因。至于冲锋线的事,我一点也不后悔。该死的,我们给了敌人致命的一击。我说的是希望。这些讨厌的委员们永远不会明白。我给予船员的,就是希望……”她流泪了,“不过,这些已经不重要了。现在,我已经突破了另一道冲锋线,对吗?一道时间中的冲锋线,回到了过去,在这里面临审判。”
“不是我来判决你。”
“我知道。你是因为好奇,对吗?”
我无话可说,非常痛苦。我对她既爱又恨。她对我肯定也是这样。但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可能分开。
也许,来自两个不同时期的同一个人再也不能合在一起,毕竟,我们人类不应该这样。
沉默了一会之后,我们回到达克的房间。塔科在那儿等着我们。
“大桶脸。”他照样叫我的绰号。
“猪油桶。”我也回敬他。
在这艘来自未来的船上,我俩相互凝视着,感到迷惑,也许是惶恐。自从我俩会生小孩的消息传出后,我们还没有单独待在一起。就是现在,也有达克舰长坐在那里,代表着命运。
德鲁兹教义并不禁止恋爱。但我关心的不是这个。很多人在远离家乡的前线牺牲了,事情并不像我受到的训练和教导那么简单。
我问:“你来这儿干什么?”
“你请我来的。未来的那个更聪明、更好看的你要我来这儿。”
舰长干巴巴地说:“你们俩很显然有些——问题——要讨论。但恐怕我要说的事更急迫。”
塔科转身对着她,“你找我有什么事?”
达克说:“海军部情报部门分析了‘火炬’上的资料。开始联系那些即将在这只飞船上服役的战士——如果他们是婴儿,或者还没有出生的话,就和他们的家属或部队联系——给他们传达未来的战斗任务。这是规定。”
塔科好像有些明白了,“所以你们来联系我?”
达克没有直接回答。“还有另外一些规定。战船每次返回的时候,幸存的舰长或高级官员通常会把唁电发给牺牲战士的家属或所在部队,有时还上门慰问。”
塔科点点头,“我曾经和伊恩那艇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