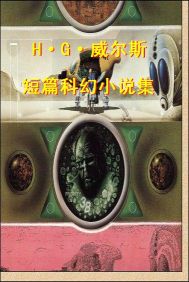外国中短篇科幻小说1000篇 (一)-第19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这些我只是模模糊糊意识到的。
她是达克舰长,哦,看在上帝份上!
她又盯着我看了看,“少尉,别紧张。我们俩不会分开的。只是,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的生活会变得很复杂。情况总是这样的,慢慢你就会明白。”
“长官——”
她有些恼怒。“别胡思乱想。我不会骗你的。”
“是,长官。”
“这种事,我和你一样不喜欢。记住。”
我们发现了一排受伤的士兵。船员们正把他们抬进“卡特”。但通道太狭窄了,拥挤不堪,一片混乱,四周充斥着呻吟、哭喊和可怕的恶臭。
达克找到一个军官。他穿着一套安全员的制服。“凯德,这儿出了什么事?”
“是通道,长官。通道坏了,不能用机器把伤员们送出去。我们只能用手。”他看起来绝望而悲伤,“长官,是我的责任。”
“你做得很好。”她严肃地说,“但是,至少把这儿弄得干净一点。你们两个,”她停下来看着我们,“在这儿帮忙。”
她大踏步走进自己的飞船,迅速把“火炬”和“卡特”上的船员组织起来,形成一条人链,用手把伤员传递出通道,送进“卡特”的装卸区。
“真让人印象深刻呀。”塔科说,“未来的二十四年里,你肯定被换了一副脑子。”
“去你的。”
通道又堵住了。我们发现了一个伤员,还是个孩子,只有十六七岁。他还很清醒,正在东张西望。
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按照我对时间的推断,他应该还没有出生吧。
他和我们谈了起来。“你们是‘卡特’号上的?”
“是的。”
他谢了我们。我表示不用客气。“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塔科悄悄对我说:“嗨,你没听说过时间悖论吗?我敢打赌委员会对这方面肯定是有规定的。”
我耸耸肩,“我都和二十四年后的自己见过面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糟的?”
这个伤员并不知道我们来自他的过去,他也不关心这个。他简单地告诉了我们“火炬”如何深入“雾”,卷入这场战争。他是一个炮手,从发射舱可以清楚地看到所发生的一切。
“我们向‘糖块’冲去。你知道‘糖块’吗?就是埃克希里人的重型炮台。但那儿到处都是夜行战船。我们被打垮了,上头命令撤退。我都能看到那该死的‘糖块’了,几乎能摸到它。但舰长根本不理会撤退的命令。”
塔科怀疑地说:“她不理会命令?”
“我们越过了‘冲锋线’。埃克希里人被主力的撤退迷惑了,‘火炬’冲破了他们的防线。”“冲锋线”通常指一个面,即宇宙空间中的军事分界线。这里特指“雾”里那段双方争夺的区域和埃克希里人控制的区域之间的界面,“我们只坚持了几分钟。但我们发射了一枚‘日出。’”
塔科说:“一枚什么?”我踢了踢他,他住了嘴。
那孩子猛地抓住我的手臂。“我们眼看就回不来了。但是,老天,‘日出’击中了敌人。我们拼命呐喊,这条老鱼差点被我们的呐喊声震裂了。”
塔科不怀好意地问:“达克舰长这人怎么样?”
“她是个了不起的指挥官。我愿意跟随她到天涯海角。”
这一切都令我感到惴惴不安。德鲁兹教义教导我们不要搞英雄主义,这个信条已经被人类信奉了一万五千年,委员会成功地把它深深植入了人们的脑海。如果未来的我要违背这条信仰的话,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炮手定定地看着我。我意识到自己正下意识地用拇指擦揉着脸颊。我放下手,把脸转了过去。
达克舰长站在我面前,“你最好习惯这样。”
“可我不想。”我咕哝着,开始抱怨起来。
达克舰长只是笑了笑。“我认为你,或者说是我,不需要很努力就能做到自己想做的事,少尉。”
我悄悄向塔科说:“我有那么自负吗?”
“哦,是的。”
达克说:“该行动起来了。一会儿我就回来,我们好好想想如何减少损失。还有,已经给你准备了一间舰长室,我们两人共有的。”
塔科犹豫地问:“长官——什么是‘日出’?”
她有些惊讶地看着他,“对了,你们还没有‘日出’。它是一种由人驾驶的鱼雷。自杀性武器。”她又看了看我,“想必你已经听说‘雾’上发生的事了。”
“听说了一点。”
她碰了碰我的脸颊。这是她第一次碰我。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像姐妹之间的触碰。“到时候你会明白的。真是无比辉煌啊。”
我们又回到了“卡特”号,瓦森委员在等着我们。
这儿,宽宽的甲板已经被分成了几格,作为医院和疗养间。船员们正处于恢复期。一些人虚弱地躺在床上,眼神空空洞洞。很多人似乎在向卫生员请求回到“火炬”继续战斗,尽管他们已经受伤——在战区,一旦被自己的船抛下,你就再也别想回到那艘船上去了。他们询问“火炬”现在怎么样了,真诚地关心着这只有生命的战船。那艘破破烂烂的老旧飞船是他们的战友啊。
他们都扎着马尾,无论男女。很明显是在模仿他们的舰长。
达克出现的时候,他们欢呼着,吹着口哨。能走动的伤员都簇拥在达克身边,亲热地碰碰她,达克两眼发光;她虽然笑容满面,面对满屋的人,但还是能看出她已经精疲力竭了。
我看着塔科。怎么会这样?不应该呀。
我注意到了一个头剃得光光的卫生员,穿着一件委员会的长袍,在伤员之间来回穿行。但她只给他们扎针,并不进行治疗。实际上,她只是从他们身上抽取血液样本,放进她身边的一只小背包里。
但在这里收集血液样本,时间和地点都很不合适。我想走过去制止她。这只是我的自然反应。幸好塔科阻止了我。
瓦森委员干巴巴地说:“由此可知,未来的你是很鲁莽的,少尉。卫生员只是在做她该做的事。这种工作无疑让她很不愉快,跟你一样。要知道,委员会的人也是人。”
“那么,为什么——”
“每一个船员在战前都要注射有助于记忆的针剂。这样我们就可以追忆一些事情。从战斗中得到的情报越多,就越能更好地预测未来的战事。此外,我们还要仔细搜寻飞船的数据库和飞行记录。”
就算我的想像力差劲吧,可我就是弄不明白,是哪些不可能的一连串因素把未来的我送进了现在的生活。但是,那是我第一次感到我们手中掌握着一件多么强有力的武器。
“天哪,”我说,“这就是保证我们取得胜利的武器。如果知道未来战争的进程的话——”
“你需要了解的东西还多着呢,少尉。”瓦森的语气很和善,“一步步来吧。”
不用说,我也是这样劝自己的。
达克终于离开了她的船员,我多少松了口气。瓦森领着我们穿过几条走道,到了艇长伊恩那的房间。
我和塔科脏兮兮地站在地毯中央,生怕从活体飞船上带来的黏液玷污了伊恩那的家具。但瓦森叫我们坐。我们于是局促不安地坐下了。
我看了看达克。她蜷缩在一张大椅子里,微微晃动着。离开了她的船员,她显得很疲惫。她就是我。那张脸就是我从小到大从镜子里看到的、我自己的脸。
我非常迷惑。我恨我自己会变得如此苍老、自负、极端。但达克也有很多值得尊敬的地方:坚定有力,有指挥才能,赢得了很多人的忠诚。我很矛盾,既想帮助她,又想把她推得远远的。
最重要的是,我俩的身体已经联在一起,其密切的程度超过骨肉至亲。我喜不喜欢她都没有关系;不管怎样,她会在我的余生中永远存在。真不是一件舒服的事儿。
瓦森观察着我,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但随后他又继续着话题,同时摇晃着手指。
“事情就是这样。我们要赶紧下载数据,把连贯的图片汇编到一起。那些图片说明了下游到底发生了什么。”下游——这不是我听到的最后一个莫名其妙的词汇,我得习惯这些胡言乱语,“让你惊讶的事还多着呢,达克少尉。”
我向舰长一摆手,“有比这更令人惊讶的?说出来吧。”
达克厌恶地四下瞧瞧。塔科把手放在我背上以示安慰。
瓦森说:“首先,你——更确切地说是达克舰长——将被指控。还会有一次法庭质询。”
“被指控?什么罪名?”
瓦森耸耸肩,“玩忽职守,草率地把战船置于危险境地。”他看行达克,“还有其他一些罪名,与违反德鲁兹教义有关。”
达克微笑着,冷森森地。真奇怪,我竟会变得如此玩世不恭。
瓦森继续说:“少尉,你被卷进去了。”
我点点头,“自然,她是未来的我嘛。”
“你不明白。是直接卷进去。我们想让你做案件的起诉人。”
“我?长官——”我屏住呼吸,“你们想让我指控我自己犯了所谓的罪,而那种罪是我二十四年之后才犯的?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你是受过专业培训的,对吗?”
达克嘲弄地笑笑,“他们就是这么干的,孩子。谁能更了解我呢?”
我站了起来。“委员,我不想干。”
“坐下,少尉。”
“我去找伊恩那艇长。”
“坐——下。”
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严厉的命令。我惶恐地坐下了。
“少尉,你不成熟,也没有经验,还有点鲁莽,要完成这个任务,你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但是你没有别的选择。
“更重要的是。”委员那冷酷的脸上又有了点人性,“你将在四个月之内向592基地汇报你的妊娠情况。你将怀上哈玛·塔科少尉。”
塔科的手从我的背上突然滑落。
“我们将同意你的妊娠,”瓦森说,“我保证。”
简直难以置信。我很愤怒,感到自己陷入了某个圈套。“你怎么知道我想和塔科生孩子?塔科,我怪的不是你。”
“没关系。”塔科说,声音听起来有点发呆。
委员发火了,“你觉得我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你现在还不明白吗?‘火炬’上有记载,你将生下的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将上‘火炬’,和我待在一块。”达克说。
“他的名字曾经叫哈玛。”委员说。我敢肯定,塔科的脸刷地变红了。
“曾经?”我感到一阵恐慌。也许是出于母亲对孩子天然的牵挂,虽然这孩子现在还不存在,而且我也刚刚才听说,但我仍然开始担心起他的安危来。“他死了,对吗?他死了,就死在‘雾’上。”
瓦森喃喃地说:“一步步来,慢慢会明白的,少尉。”
达克向前倾了倾,“是的,他死了。他驾驶着‘日出’,带着一枚单极炸弹冲进埃克希里人的‘糖块’。你知道吗?你的孩子,达克。也是我们的孩子。他是一个英雄。”
等等,慢慢就会弄明白的。我不断对自己重复着这句话。但我仍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
(二)
我和达克驾驶着快艇查看“歼击火炬”的两翼。一些卫生员在附近巡视,不时用软管把止渗剂涂在那些大伤口上。
“火炬”已经被编进了它的同类组成的舰队。这些飞船都是活生生的有机体。像城市那样庞大的生物行动起来当然优美不了,但它们的运动协调一致,像在跳巨型舞蹈。它们相互偎依着,仿佛一群彼此碰来碰去的大鱼。
达克喃喃地说:“这些受伤的巨兽有的已经被人类雇用一千多年了。我们剥去了他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切断了他们的思维——但他们的自我仍然徘徊着,渴望着同类的慰藉。”
我心不在焉地听着。
达克和我。自己和自己。我总忍不住时时打量她。
快艇停下来了,我们上了“火炬”。这是个像山洞一样的地方,四周用软骨组织支撑着。穿过一个洞口和一个有着弧形墙壁的通道,我们来到飞船的中心。灯已经装好了,重力也恢复了。但我们没有看见“火炬”的船员,只有些基地派来的维修工人。
“你从来没有在活体飞船上干过,对吗?记住,这船是有生命的。它是热的。它睡觉的时候,你甚至可以听见它的脉搏和心跳,像远处的铜锣。还有老鼠,窸窸窣窣到处爬。”
听上去真是个挺舒服的地方,但跟我知道的飞船简直太不一样了。“老鼠?”
她笑了,“小杂种到处都是。”
我们继续往前走。仿佛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子宫。还好,比开头那黑暗和混乱的一个小时稍强些。我不知道未来的我怎么适应这一切。但达克好像很高兴回来。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我们来到了被达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