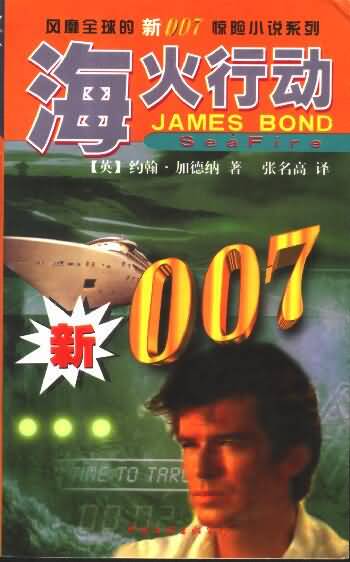寒鸦行动-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在这附近出生。”珀西回答。
保罗一时来了兴趣,他知道,一个贫穷家庭的孩子最后当上英国陆军上校,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你父亲是靠什么为生呢?”
“用马车拉煤卖。”
“他有自己的生意?”
“没有,他给煤炭商人干活。”
“你是在附近上的学吗?”
珀西笑着,他知道,对方在查他的老底,但他似乎并不介意。“当地的一位牧师帮我获得助学金,上了一所好学校。我在学校那儿改掉了伦敦口音。”
“是有意的吗?”
“算不上是有意的。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在战争爆发前我从事过政治。有人总是问我,‘像你带有这种口音的人,怎么成了一个社会党党员呢?’我解释说,我是受学校的鞭打才改掉原来的口音的。这么回答总能让那些自高自大的家伙闭嘴。”
珀西把车停在一条树木夹围的街道上。保罗向外望去,看见一座梦幻般的城堡,有城垛、塔楼和高高的尖塔。“这是监狱?”
珀西做出一个无奈的手势。“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
弗立克站在门口等候,她穿着急救护士队的制服,有四个口袋的束腰外衣和一条裙裤,戴了一只小翻沿帽子。皮带束紧她纤细的腰身,让她看上去更加娇小,一缕漂亮的卷发从帽子下面逸散出来。保罗惊讶地看了好一会儿。“她可真是个漂亮姑娘。”他说。
“她是结了婚的。”珀西直截了当地说。
他还提前警告我一下,保罗觉得这挺有意思,便问:“跟谁?”
珀西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我觉得你也应该知道。是法国抵抗组织的米歇尔,波林格尔小组的领导人。”
“哦,谢谢。”保罗下了车,珀西继续开车离开。他想,看到他和珀西从档案里只筛选出这么几个人,弗立克也许会生气。保罗只见过她两次,两次她都对他大嚷大叫。不过,这会儿她看来挺高兴,他跟她提起莫德,她说:“看来我们已经有了三名队员,包括我在内,这么说工作已经完成一半了,而现在刚下午两点。”
保罗点点头,这也是看问题的一种角度。他很着急,但这么说也没解决什么问题。
霍洛威的入口处是一个中世纪的门房,有几个箭头形的狭长窗户。“为什么没有整个统一起来,建一扇铁闸门和一座吊桥呢?”保罗说。通过门房进入院子,有几个穿着深色衣服的女人在种蔬菜。在伦敦,每一小片荒置的土地都种上了蔬菜。
监狱赫然出现在他们面前,门边守着石头怪物,身形巨大、长着翅膀的狮身鹰首兽用爪子抓着钥匙和镣铐。正门的房子两侧连着四层的楼房,每层都有一长排狭窄的尖角窗户。“这是什么鬼地方啊!”保罗惊叹道。
“女权参政者曾在这里进行绝食,”弗立克告诉他,“珀西的妻子就在这儿被强行灌食。”
“我的上帝。”
他们走了进去,空气中带着刺鼻的漂白粉味道,就好像当权者指望用消毒剂杀灭犯罪的细菌。保罗和弗立克找到了林德莱小姐的办公室,她是一个桶形身材、长着一张坚硬的胖脸的主管助理。“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见罗曼,”她说,接着又不满地加了一句,“显然你们也不打算告诉我。”
弗立克的脸上浮上一丝轻蔑之色,保罗看出她似乎要开口挖苦对方,便连忙插嘴说:“我很抱歉,但这是秘密。”他带着迷人的微笑说,“我们只是奉命行事。”
“我们大家都是公事公办,”林德莱小姐稍稍缓和地说,“不管怎样,我必须警告你们,罗曼是个很暴力的囚犯。”
“我明白,她是个杀人犯。”
“不错。她应该吊死,可眼下法律太宽松了。”
“的确是。”保罗说,虽然他一点儿也不这么认为。
“一开始她是因为醉酒进来的,后来,她在操场上打架,杀了另一个囚犯,所以正在等待谋杀判决。”
“一个难对付的家伙。”弗立克很有兴致地说。
“是的,少校。她乍看上去挺讲道理,但不要被她骗了。她很容易被激怒,一眨眼就能发作。”
“她一发作就要命。”保罗说。
“你说的一点儿不错。”
“我们时间很紧,”弗立克不耐烦地说,“我想现在就见她。”
保罗急忙补充说:“如果你方便的话,林德莱小姐。”
“好吧。”主管助理领他们出来。坚硬的地面和光秃秃的墙壁让这里发出教堂一般的回声,远处的喊叫声、关门声和靴子在铁制过道上发出的叮当声组成了持续的声音背景。他们通过一条狭窄的走廊和一段陡峭的楼梯,来到会面室。
鲁比?罗曼已经等在那里。她的皮肤呈深棕色,直发是暗黑色的,还长着一双凶猛的黑眼睛。不过,她不是那种传统的吉卜赛美女,她的钩鼻子和往上翘的下巴让她看上去倒像个侏儒。
林德莱小姐离开了,留下一名看守在隔壁房间透过玻璃门监视着。弗立克、保罗和囚犯围着一张破破烂烂的桌子坐下,桌子上面有个肮脏的烟灰缸。保罗随身带了一包好彩香烟,他把香烟放在桌子上,用法语说:“请随便用。”鲁比拿了两支,一支叼在嘴上,另一支夹在耳朵后面。
保罗问了几个一般性的问题,以打破沉默。她回答得既清楚、又有礼貌,但是口音很重。“我父亲到处旅行,”她说,“我还是小姑娘那会儿,我们跟随一个大游艺戏团在法国到处走。我父亲有个气枪打靶摊子,我母亲卖带巧克力沙司的热烤饼。”
“你是怎么来英国的?”
“我十四岁时,爱上了在加来遇到的一个英国水手,他叫弗雷迪。我们结了婚——当然,我撒谎说我已经够了岁数——然后就来伦敦了。几年前他丧了命,他的船在大西洋被德国潜艇打沉了。”她颤抖着说,“冷冰冰的坟墓。可怜的弗雷迪。”
弗立克对这些家史不感兴趣,便问:“说说你是怎么进来的。”
“我自己弄了个炭火盆,在街上卖烤薄饼。可是警察不断来骚扰我。有天晚上,我喝了点儿白兰地——我承认,我就好这个——不知怎么的,我就跟人争吵起来了。”她换成了伦敦腔的英语,“警察说让我滚远点儿,我也就破口大骂。他使劲推我,我就干倒了他。”
保罗看着她,觉得很有趣。她只有中等个头,身材结实,但她长着一双大手,两条腿上满是肌肉。他能想象得出伦敦警察被她放平了的样子。
弗立克问:“后来呢?”
“他的两个哥们儿从街角赶了过来,我没能赶紧离开,因为喝了白兰地,他们踢我,抓我进了号子。”见保罗不解地皱起了眉头,她加了一句,“也就是警察局。总之,那第一个警察不好意思说我攻击警察,不愿意承认让一个女孩家给搁地上了,就按酗酒和妨碍治安关了我十四天。”
“接着你又干了一架。”
她瞥了弗立克一眼。“我不知道怎么对你们这类人解释这里面的事儿。有一半的姑娘都疯了,她们全都有武器。你可以把勺子磨得像把刀子;或者找根铁丝磨尖了,做成一把锥子;也可以用线拧成一根绞索。看守从来不干涉犯人之间的打斗,他们宁愿看着我们互相揪扯。所以不少人身上都是伤痕累累。”
保罗感到震惊,他以前从未接触过监牢里的人。鲁比描述的这幅场景十分可怕。或许她有所夸大,但她看上去平静、诚实。她并不在乎别人是否相信她的话,只是在干巴巴、慢悠悠地讲述事实,看上去似乎兴趣缺缺,但也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
弗立克问:“什么事让你杀了那个女人?”
“她偷了我的东西。”
“什么东西?”
“一块肥皂。”
我的上帝,保罗想,她为了一块肥皂就能杀人。
弗立克问:“你是怎么做的呢?”
“我把肥皂拿了回来。”
“然后呢?”
“她找上门来,手里拿了一根用椅子腿做的棍子,上面箍了个水管接头,她用那东西打我脑袋。我看她是要杀了我。可我有刀。我捡到过一长条碎玻璃片,把宽的一头用旧自行车轮胎捆成了刀把。我把刀往她喉咙里一插,她就再也打不了我第二下了。”
弗立克忍着没有发抖,说:“这应该算是自卫吧。”
“不算,因为你得证明你当时不可能跑开。再说我拿一块玻璃做了刀,这就算预谋杀人。”
保罗站了起来。“请你跟看守在这儿等一会儿,”他对鲁比说,“我们出去一下。”
鲁比对他笑了一笑,这是她第一次显得让人愉快,尽管不太漂亮。“你真客气。”她感激地说。
到了走廊,保罗说:“多恐怖的故事!”
“别忘了,这里的人都说自己是无辜的。”弗立克审慎地说。
“不管怎样,我看她可能受罚过重了。”
“我说不准,我觉得她是一个杀手。”
“所以我们不要她。”
“正相反,”弗立克说,“我要的就是她。”
他们回到房间里面。弗立克对鲁比说:“如果你能从这儿出去,愿不愿意做一种危险的工作?”
她以问代答:“我们是要去法国吗?”
弗立克眉毛一挑。“你怎么想起问这个问题?”
“你们一开始跟我说法国话,我估计是考查我会不会说法语。”
“这种工作我不能讲得太细。”
“我敢打赌是有关敌后破坏活动。”
保罗感到震惊,鲁比理解问题相当快。见他如此惊奇,鲁比便接着说:“一开始我以为你们想要我给你们当翻译,但这并没什么危险。所以我们可能是去法国。可英国部队除了轰炸桥梁和铁路线,还能干什么呢?”
保罗一言不发,但十分惊叹她的推理能力。鲁比皱起了眉头说:“我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要弄一个清一色的女人队伍。”
弗立克瞪大了眼睛。“你是怎么想到这个的?”
“如果你们需要男人,干吗还来找我?你们肯定是走投无路了。把一个女凶犯从牢里弄出去并不容易,哪怕为了某种要紧的战争任务。那么,我到底哪里特别?我敢来硬的,可是能说法语的硬汉子成百上千,早就准备好参加这种秘密活动了。所以,挑上我的唯一原因就是我是个女的,大概女人不太可能引起盖世太保的怀疑……我说得对吗?”
“我无可奉告。”弗立克说。
“好吧,如果你们要我,我就干。我能再拿一支香烟吗?”
“当然。”保罗说。
弗立克说:“你要明白这工作很危险。”
“明白,”鲁比说,点燃一支好彩,“总不会比待在这个该死的监狱更危险吧。”
离开鲁比以后,他们回到主管助理办公室。“我需要你的帮助,林德莱小姐,”保罗说,再一次表示奉承,“告诉我你需要什么手续才能释放鲁比?罗曼。”
“放了她?她可是个杀人犯!为什么要释放她?”
“恐怕我无法告诉你。但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你知道她要去什么地方的话,你不会认为那是什么幸运的逃生,而是恰好相反。”
“明白了。”她说,但并未完全平静下来。
“我要让她今晚就离开这里,”保罗接着说,“但我不想让你处于任何一种尴尬的境地。因此我要知道你需要哪个部门的批准。”他真正想弄清的是她能找出什么借口阻碍这件事。
“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释放她,”林德莱小姐说,“她已经被地方裁判法院押回这儿,所以只有法院可以释放她。”
保罗很有耐心地问:“那么,你觉得需要什么手续?”
“她必须由警察押解,押到地方法官面前,公诉人或者公诉人代表,需要告诉地方法官,对罗曼的所有指控都被撤销,然后法官就会开恩宣布她获得自由。”
想到面前有这么多麻烦,保罗皱起了眉头。“她应该先签署加入部队的文件,然后才能去见法官,这样,一旦法院放了她,她就处于军事纪律的约束下……否则她可能会一走了之。”
林德莱小姐仍然将信将疑。“他们为什么要撤销指控?”
“检察官是政府官员不是?”
“是。”
“那就不成问题了。”保罗站了起来,“我晚上再回到这儿来,带着地方法官,还有检察部门的人,还有军队的司机,把鲁比带到……她的下一个驿站。你看还有什么障碍吗?”
林德莱小姐摇着头说:“我遵命行事,少校,就跟你一样。”
“好吧。”
他们离开了那里。到了外面,保罗停住脚望了望身后。“我还从未到过监狱,”他说,“我不知道我指望自己看到什么,但这可不像神话传说里的东西。”
他对这幢建筑的品评听上去不合时宜,弗立克脸色阴沉。“这里吊死过好几个女人,”她说,“根本就不是什么神话。”
保罗好奇为什么她的脾气变得如此糟糕。“我猜你是把自己当成这里的犯人了,”他说,忽然他明白过来,“这是因为你有可能在法国蹲进大牢。”
弗立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