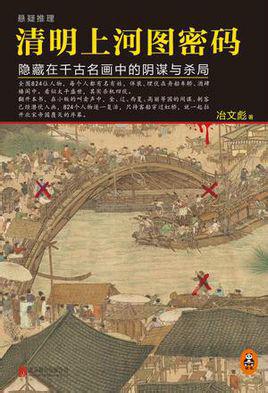清明上河图密码2:隐藏在千古名画中的阴谋与杀局-第4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气恨之极,连连捶打自己的老腿,几乎哭出来。挨着痛,又左右寻了好半天,根本看不到那车的踪影,只能不住声怨骂着,一路瘸着回去,把面钱付给了那摊主,苦叹着慢慢回家去了。
冯赛回去时,乌鹭禅师已经安歇,小和尚弈心还替他留着门,独自坐在佛殿前的台阶上看月亮。冯赛心下愧疚,忙低声致歉,弈心却和声细语吟了句:“空院留月影,虚门待归人。”
两人一起回房,各自脱衣歇息。弈心不久便睡着了,冯赛虽然疲累,却睡不着,看着月光透过窗纸洒进屋中,一片霜寒。念起妻女,忧闷难禁,默念着吟了一阙《乌夜啼》:
一窗明月如盐,洒心间。离恨无端催取,枕边咸。
更与漏,骨与肉,两熬煎。半夜风吹花去,半床寒。
反复默诵了几道,越诵越悲,不由得滴下泪来。良久,心绪才渐渐平复,却依然难眠。他想起周长清所言的信己,信所当为与能为,这样苦思无益,还是该尽力收神,尽快理清楚汪石的事,这才是当为与能为。
于是,他止住悲绪,将念头移到孙献身上。若孙献所言属实,这汪石就越发诡秘难测了。他难道真和左藏库飞钱有关?连库监在内十几个人亲眼目睹钱飞走,又是怎么一回事?
不过,他随即想到汪石在正月间就已经有十万石粮和八万匹绢,按时价,当时已经至少有几十万贯家底。而库钱飞走却是二月底,他的本钱并不是靠左藏库飞钱才有的。何况二月初他又贷到了百万贯,何必再冒天大风险去打那十万贯国库的主意?何况,飞钱这件事太过离奇,就让孙献自己先去查着,百万贯官贷更紧迫。
他又细细回想今天和秦广河、黄三娘、鲍川三人的对话,汪石是借助现钱短缺、粮荒、绢荒三件事,分别打动了那三人,先施恩,后求报,让三人心甘情愿替他担保。看起来都是凑巧遇到,但这“凑巧”无论如何都像是事先有意设计。就如他低价抢断我的盐钞、茶引主顾,让我卖不出去,而后又来向我收买,救了我的急,让我不知不觉便感激信赖他。
不过,盐钞、茶引还好设计拦断,汪石又怎么可能设计出秦广河缺现钱?至于粮荒、绢荒,是由于方腊闹事,水路受阻,更不是区区汪石能够设计得了的。他反复琢磨,但对汪石所知太少,始终无法猜破其中隐秘,便转而想到秦广河、黄三娘、鲍川三人的态度。
按理来说,这三人都是京城顶尖的豪商,不论才智还是手段,都是世间一等,绝不会轻易受骗,受骗之后也绝不会轻易罢休。然而,三人却都是一副听之任之的态度。
秦广河还好说,汪石先用两万贯现钱替他救了急,又替他找回了“母钱”,他迷信“母钱”之说,这一恩情在他心中,比前一件更重。他又信佛,深信因果,得之于汪石,又失之于汪石,于他而言,也是一桩因果,因而能自我解释,不太执着。但黄三娘和鲍川呢?汪石虽然救了粮荒和绢荒,但其中公义远大于私恩,他们两人却也同样听之任之。这多少有些不合常情。
黄三娘、鲍川与汪石之间,恐怕并非仅止于此,其间应该还藏着些什么……
邱迁被一阵唰唰声惊醒。
声音其实不大,是从小院外的巷道传来,由于他揣着心事,梦寐中仍自警醒,所以才听到了。
他悄悄支起身子,将耳朵靠近窗户细听,是脚步声。比常日来回巡视的家丁脚步要重许多,虽然是多个人,但很齐整,应该是几个人抬着重物在行走。一组人过去后,又一组人经过,前后大约一共有五组。这些人都不出声,只隐约听到使力时发出的气哼声。
五组人全部走过后,外面顿时沉寂。半晌,才又响起松散的脚步声,是那几个值夜家丁在来回巡走。
邱迁透过窗纸破缝向上望,一轮圆月正悬高空,清辉如银,此时大约是子夜时分。这么晚,那些人抬什么东西出去?难道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天才亮,孙献还在睡,外面忽然传来敲门声。
他本不想管,但外面不住地敲,扭头一看,妻子也被吵醒,却在装睡。他只得起身披了件衫子,下床出去,打着哈欠开门一看,是皮二。
皮二眼里冒着光:“孙哥儿,我查出来那人是谁了!你根本想不到!”
“哦?你先进来,堂屋里坐坐,我去穿了衣服来。”
孙献一看皮二他那神情,便知道他的确查出汪石来了。居然这么快?孙献苦笑着进去穿衣。等他穿好再出去时,外面又传来敲门声,开门一看,是黄胖。
“孙哥儿起来了?我还怕自己来早了。那人我已经查出来了。”
“哦?先进来。”
孙献才要关门,外面又一个声音嚷起来,是管杆儿:“莫关!我来了!咦?黄胖也来了?”
看管杆儿那兴头,也是查问出汪石了。一瞧三人,自然都是来趁早饭的。妻子见了绝不乐意。
孙献只好对三人道:“家里说话不便,咱们还是出去吧。”
三人跟着他来到巷口的茶肆,孙献边走心里边苦笑,他是听说冯赛和京城三大巨商也被汪石套了进去,而且事关一百万贯官贷。那四人各个不简单,贴着他们一定能找见汪石。他原想用这件事做由头,支开身边这三个癞汉,谁知这三个人一个比一个神通。不过这样也好,冯赛那里也还没有什么线索。既然答应了还要给这三个癞汉一人三贯钱,就先尽着使唤。等查明白这件事,找见汪石,再设法甩脱。
到茶肆坐下后,孙献笑着道:“你们三人居然全都查出来了?那人是……”
“汪石!”三人抢着道。
“哦?那个正月救了粮荒的?”
“正是。”三人又一起点头。
“这事越来越有意思了。”
“可不是?逮到这样一个巨富,随便蹭点皮屑下来,也是几十上百贯。”皮二眼睛又冒出光来。
“这汪石现在哪里,你们可查出来了?”
管杆儿和皮二一起摇头,黄胖却道:“我还听说一件事,牙绝冯赛和粮行、绢行、钱行的三大行首也被汪石骗了,还闹到了大理寺,他们也正到处找汪石。”
“哦?”孙献暗暗叫苦。
“昨晚我跑到半夜,虽没找见汪石,却问出一件古怪来。”皮二道。
“什么古怪?”
“汪石是外路州的人,年初才来京城,还没置买宅院。他那样的人,自然不会住一般客栈,我把城里城外几十家上等客栈跑遍了,可你们猜怎么着?”
“快说!”管杆儿不耐烦。
“他没住任何一家客栈!”
“那他住哪里?”
“不知道。”
“难道是住在朋友家中?”
“妓馆?”
“这个还不知道。”
孙献听了,暗暗纳闷,看来这汪石行事果然诡秘。于是他道:“三位老哥先饱饱把饭吃好,而后再分头去打问这汪石的落脚处。”
冯赛想到了一个疑点,一早爬起来,便匆匆赶到黄三娘的绢店。
这虽然是京城最大的绢店,门脸却并不宏阔,只比街市普通店面大一些,也不零卖,常年只往各大绢铺送货。因此店里不见绢匹陈列,只设了二十几张檀木桌椅,正面靠墙一大幅荆浩山水画屏,两边墙上悬挂名家字画,像是大户人家的堂屋一般,一派淳雅。
冯赛知道黄三娘近年来已经很少亲自到店里来,便径直走了进去。迎客的仆役认得,笑着上前拜问,冯赛问道:“范先生可在?”
“冯二哥!”范籍正已经笑着从后面走了出来。
范籍正四十来岁,样貌温朴,是黄三娘家的账房。他原先是个儒生,屡考不中后便断了这念头,转而替人做账。自从黄三娘招赘了方聪后,方聪便不再做账房。黄三娘托冯赛替他寻个稳靠的人,冯赛和范籍正一向亲熟,便举荐了他。范籍正来这里已经多年,事事稳重谨细,很得黄三娘倚重。
两人互相拜问过后,范籍正引着冯赛走到后面的书房,落座上茶。冯赛等仆人出去后,才道:“范兄,我是来打问一件事。按理来说,这种事不该多嘴动问,不过此事关系重大,不得不问。”
“可是汪石的事?”
“嗯。不过我要问的是三娘宅中私事。”
“她丈夫?”
“嗯。”
“冯二哥认为她丈夫的事和汪石官贷有关?”
“我只是猜测。”
“其实我也在疑心,不过这事又不好多言。”
“是。我也是犹豫再三,才来向范兄打问。今日所说的话,仅止于你我之间,还望范兄多担待。”
“那是自然。其实……三娘撵逐丈夫一事,的确和汪石有关。”
“哦?”
“方聪在外面养那小妾其实已经有两年多了,宅中上下许多人都已知晓。但你也知道三娘为人,从来以礼自持,自重敬人,最不喜底下人传三传四。方聪又惯会笼络人,一向待下人和气。因此,这事宅里宅外从来没人敢告诉三娘……”
“是汪石透露给三娘的?”
“应该是。汪石
第二回拜访三娘后,他才走,三娘就命几个仆妇撵到那小妾宅子里,要了件东西回来。”
“什么东西?”
“一枚铜钱。”
“一枚铜钱?”
“是。那几个仆妇去了那小妾宅子,既没骂,更没打,只从她身上搜出来一枚铜钱,而后就走了。不但我们,连那几个仆妇也不知道其中原委,大家都很纳闷。”
冯赛顿时想起黄三娘颈上挂着一枚铜钱,“母钱”?
范籍正继续道:“当天晚上,三娘就给了方聪一箱银子,撵他走了。方聪没脸再在京城待下去,听说第二天就搭船回乡去了。那小妾原是个妓女,又回妓馆去了。汪石先是救了绢荒,又把方聪养妾的事透露给三娘。三娘心肠最柔善,感念他两番恩德,便替他担保了那笔官贷。若汪石真是仁人君子,倒也好。若他居心不良,三娘这回便要大大伤元气了。”
冯赛一边听,一边暗暗吃惊:又和“母钱”有关?
黄三娘的“母钱”为何会在那小妾手里?恐怕是方聪偷去给了她,他想把黄三娘的财气转给那小妾。黄三娘又为何知道“母钱”在那小妾手中?应该是汪石透露的。不过——那个小妾偷得黄三娘的“母钱”,这是极隐秘的事,汪石又是如何得知的?
汪石的计谋是“施恩术”,为了打动黄三娘,必定四处打探她的弱处。许多人都知道方聪在外面养妾,这个还好打探。但方聪将黄三娘的“母钱”偷给小妾,自然无比小心。黄三娘虽然性情和善,毕竟是汴京绢行行首,方聪和那小妾绝不敢轻易告诉别人,除非……
冯赛忙问:“昨天我去拜见三娘,见她脖颈上挂着一枚铜钱,可是从那小妾手中夺来的那枚?”
“是。听仆妇说,夺回来后,三娘就挂在了颈上。”
“这之前三娘没有挂过?”
“没有。”
“夺回那铜钱是哪一天?”
“元宵节才过完没几天,我记得那天汪石的那些绢运过来后,开始往外发卖,我忙乱了一整天,回家后才听浑家说起这事,我查一查……”范籍正从旁边架子上找出一本簿记,翻检了一阵,确认道,“是正月十九。”
冯赛听后心里一震,隐约看出了其中惊人计谋。
第十四章
做戏、替身
知敝,则所以待人者尽矣。
——王安石
孙献打发走黄胖三人,慢慢踱了回家。
才一进门,他妻子就竖起眉毛问:“那三个混赖货又来骗吃?”
孙献不愿搭理,那妇人却仍叨念个不停。孙献见家也没扫,水也没烧,心里顿时火起,抓起墙边的扫帚就朝妻子扔去。妇人没躲及,小腿被砸到,趁势坐倒在地上,双手拍着地哭起来。
孙献不耐烦,懒得多说什么,转身摔门就出去了,心里气闷无比。想当日每天有银钱进袋,家里虽请了两个仆婢,妻子却仍勤快得不得了,凡孙献吃穿动使,她嫌仆婢不干净,都要亲自打理。每日回去,夫妻两个谈谈说说,何等和气?这银钱才断了十来天,她就变成这副模样。
想起昨天傍晚去蓝威酒肆,那两口子亲亲甜甜的情景,他心里越发不痛快。闷走了半天,才想,若不查出那十万贯飞钱的下落,生计没有着落,这往后恐怕天天都是如此。于是他走进一间茶肆,要了碗茶,一个人坐着收神细想。黄胖三人分头去找汪石的下落,我这里还是该再查问一下库监蓝猛的底细。从昨天蓝威的言谈看,他满心认定弟弟蓝猛是冤死,似乎并不相信蓝猛和飞钱有什么关联。
之前从他家隔壁郑家食店打问的情形看,这两兄弟似乎情谊甚好,出事前一晚蓝猛还去了哥哥店里,和兄嫂一起坐着吃酒说笑。但第二天,户部的人就要去左藏库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