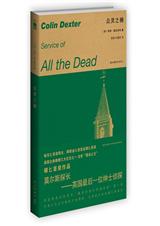众灵之祷-第1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样。有两次,她看见他非常体面:头发梳得很整齐,面颊刚刚刮过,指甲清理干净,身上穿着一件体面的西装。
那些时候,两个兄弟看上去才很像一家人……“……如果他们问我,他们肯定不会……”
罗林森夫人一直在喋喋不休,她的话最后飘到了鲁思的头脑里。
“你会怎么跟他们说?”
“我告诉过你了。你没在听我说吗,亲爱的?
有什么不对吗?”
是的,很多不对的地方,开始你就是错的。
还有,亲爱的妈妈,如果你不当心一点,这几天我就掐死你,然后给你穿上别人的衣服,把你皮包骨头的尸体抬到塔楼顶上去,再让那些鸟饱餐一顿!“不对?当然没有。我去把茶端过来。”
她削的第一个土豆皮下面出现了腐烂的黑色霉斑,她又从袋子里拿出一个自己刚买的——袋子上的大幅英国国旗下面标着“购买国货”的字样。
红色、白色和蓝色……她想到了保罗·默里斯坐在风琴手的位子上,披着红色斗篷,穿着白色衬衫,戴着蓝色领带;保罗·默里斯,那个众所周知和布伦达·约瑟夫斯私奔的人。但是他没有,不是吗?有个人非常、非常肯定他没有,那个人当时就坐在某个地方——甚至现在也是!——谋划,幸灾乐祸,用某种方式从整个肮脏的交易里获利。
麻烦在于剩下的人并不多。其实,如果你数数那些剩下来的人,只有一个人或许能够……不过,当然不能。布伦达·约瑟夫斯肯定与这件事无关。
鲁思肯定地摇了摇头,开始削下一个土豆。
21虽然丈夫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用他们在沃尔福库特的房子做了抵押,不过布伦达·约瑟夫斯夫人现在经济还算宽裕,而且什鲁斯伯里郊区的综合医院给的护士宿舍相当宽敞。根据保罗的专门指示,她一直没有给他写信,而且只从他那里收到过一封信,她把这封信虔诚地放在手袋的内衬里,大部分内容她都烂熟于心:“……最重要的是不要着急,亲爱的。这需要时间,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要谨慎。在我看来,我们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们必须维持现状。只要耐心,一切都会好的。我渴望再次见到你,感到你美丽的胴体就在我身边。我爱你,布伦达,你知道,很快我们就可以一起开始新的生活。一定要谨慎,收到我的信之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把这封信烧掉——现在!”
布伦达从早上七点半开始在妇外科病房工作,现在是下午四点一刻。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全天她都不用上班,她靠在护士休息室的靠椅上,点燃一支香烟。离开牛津之后,虽然保罗不在身边,但生活比她原先期望或者想象的更加充实和自由。
她结交了新的朋友,培养了新的爱好。她已经意识到——非常欣喜地意识到——自己对异性有多大的吸引力。她提供了自己在拉德克利夫医院做护士之前的护士长作为推荐人,在被任命后一个星期,一位年轻的已婚男医生对她说:“你愿意和我上床吗,布伦达?”就像那样!她现在想起这件事的时候笑了起来,可耻的念头不由自主地划过她理智的边缘,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她现在真的那样迫切地需要保罗吗?还有他的那个儿子,彼得?他是个很好的小家伙,不过……她掐灭烟头,伸手拿过《卫报》。离晚餐还有一个半小时,她坐下来,慢慢浏览当天的新闻。通货膨胀率好像意外地令人鼓舞,然而失业率却不是,她相当清楚失业对人的心灵会有怎样的影响。中东和平会谈还在进行,但是非洲各地的内战好像正在威胁超级大国之间的微妙平衡。国内新闻版面第三页的底部有一条简讯,牛津某个教堂的塔楼上发现了一具尸体,但是布伦达没有读。年轻的男医生就坐在她身边,近得有些不必要,但是并不令她讨厌。
“嗨,美女!我们一起玩填字游戏怎么样?”
他从她手上拿过报纸,翻到填字游戏那一页,然后从白色外套的口袋里拿出一支圆珠笔。
“填字游戏我玩得不好。”布伦达说。
“不过我猜你的床上功夫一定不错。”
“如果你要——”
“横向的词,六个字母。‘姑娘把枪拿给地方检察官。’你觉得是什么词?”
“不知道。”
“等一下!‘布伦达’怎么样?很合适,不是吗?枪——‘布伦式轻机枪’;地方检察官——‘DA’。就是这个!”1布伦达抓过报纸,看到上面的提示:床上的姑娘——受到审查的。“是你编出来的。”她哈哈笑道。
“‘ 床’ 是 个 美 妙 的 词, 不 是 吗?” 他 把“布伦达”这个词写在报纸的边缘,然后依次把“b”“e”“d”三个字母利落地圈出来。“我有1 在英语中,“布伦达”拼作“Brenda”,“布伦式轻机枪”
拼作“Bren”,“地方检察官”拼作“District Attorney”,通常缩写为“DA”。
希望吗?”
“你已经结婚了。”
“而你离家出走了。”他在剩下的三个字母“r”“a”“n”划出来 1,调皮地转向她。“没有人会知道。我们只要赶快去你的房间,然后——”
“别犯傻了!”
“我没犯傻。我就是忍不住,每次看到你穿着制服,我就对你垂涎欲滴。”他的声音轻佻而戏谑,但是当房门打开,两位年轻的护士走进来的时候,他突然严肃起来。现在他轻轻地说道:“如果我继续尝试,你别生气,好吗?答应我?”
“我答应。”布伦达轻声说道。
他在横排第一个方框里写下“禁止的”这个词,然后读出竖行第一个词的提示。但是布伦达没有在听。她不想别人看到自己和年轻医生靠得1 Bed,意为“床”,ran,意为“跑掉,离开”。
这么近,很快就找了个借口回到房间,躺在自己的单人床上,久久地盯着天花板。她进来之后把门锁上了,没有人会知道,不是吗?就像他说得那样。只要……她几乎无法解读自己的心思。只要他走上楼梯,敲敲门,再问她一次,用他简单而满怀希望的方式,她知道自己会请他进来,然后躺下——就像现在这样躺着——他解开自己制服前面的白色纽扣的时候,她会欣然接受,不做任何抵抗。
她感到疲倦,房间里非常闷——暖气热得不能碰。她渐渐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感到口干舌燥。
有什么惊醒了她,她现在听到有人不住地轻轻敲门。她睡了多久?她的手表告诉她现在是下午五点三刻。她理了理头发,整理好制服,轻轻抹了一点唇膏,带着一点兴奋的忐忑,走到了房门的旁边,房门最近才涂过晃眼的白漆。
第二天早晨,一位清洁工发现她就躺在那扇门边。她不知怎么从屋子中间爬了过来,显然是要伸手去摸索门把,但是没有够到,因为门的下半部分沾满了她喉咙里喷出的血污。好像没有人知道她是哪里的人,但是警方在她手袋的夹层里面找到的一封信明显表明她和——或者曾经和——一个叫保罗的人关系非常亲密,他的地址只写着“基德灵顿”,而且催促收信人立刻把证据烧掉。
22星期天的早晨,莫尔斯正在读塔楼上那具尸体的验尸报告,这份报告耽搁了很久,他读到第二页中间的时候,终于认定自己就像是在读中国的《人民日报》一样。他当然理解报告需要使用一些专业名词,但是医学专业以外的人根本无法厘清这一堆生理学标签。不过报告的第一段还比较通顺,莫尔斯把报告递给了刘易斯:尸体属于成年白人男性,头颅较短。
身高:五英尺八又二分之一英寸。年龄:
很难精确估算,但是最有可能在三十五至四十岁之间。头发:浅棕色,死亡前一星期左右很可能理过发。眼睛:颜色难以确定。
牙齿:非常好,珐琅质坚固,只有一处镶补(左后方第六颗)。体貌异常:据观察没有,但是无法认定没有任何异常体貌特征,因为左脚内侧下部最大的一块皮肤长度只有……刘易斯把报告递了回去,因为他根本不愿回想自己不久之前拿着教堂管理人的电筒,用狭窄的光束照到的清晰景象。另外,今天早晨他的第二项任务实在有些阴森可怕,接下来半个小时,他把装着死者衣物残片的五六个半透明塑料袋仔细翻了一遍。莫尔斯本人拒绝协助这种气味难闻的工作,直到他听见自己的部下轻轻吹了声胜利的口哨,他才表现出一丝兴趣。
“我猜猜看,刘易斯。你找到了一个标签,上面有他的姓名和电话号码。”
“和这个一样好,长官。”他用镊子夹着一张长方形的小车票,“就在夹克的内袋里——十月二十六日,三十便士。我估计基德灵顿到牛津的车费就是三十便士——”
“现在可能涨价了。”莫尔斯低声说道。
“——肯定(刘易斯的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就是保罗·默里斯失踪的日子,不是吗?”
“我一直不大记得住——日期。”莫尔斯说。
不过现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打消刘易斯的积极性,“遗憾的是他的牙齿很好,长官。他可能很多年都没去看过牙医了。不过,我们还是应该能——”
“你真是太想当然了。我们两个人都没有找到任何能表明他身份的证据,同意吗?直到——”
“是的,我们没有。但是我们不应该对眼皮底下的事情视而不见。”
“什么事情?”
“我们找到的人就是保罗·默里斯。”刘易斯非常肯定地答道。
“就因为他班上的一个女生说他曾经穿过一件暗色西装——”
“还有一条蓝色领带。”
“——还有一条蓝色领带,好吧,你是说,那么他就是保罗·默里斯?刘易斯!你正在变得和我一样糊涂。”
“您觉得我说错了吗?”
“不,不。我不会这样说。我只是比你更谨慎一点。”
这非常可笑。刘易斯很了解莫尔斯,他是最敢在黑暗中大步前行的人,然而现在他却——对青天白日之下这些显而易见的简单事实视而不见。
还是忘了吧!
刘易斯只花了不到十分钟时间就查出保罗·默里斯曾经在基德灵顿健康中心就医,在一点平静而迫切的压力之下,中心的高级合伙人仔细查阅了他的病例。
“怎么样?”刘易斯挂上电话的时候,莫尔斯问道。
“相当吻合。三十五岁,五英尺九英寸,浅棕色头发——”
“很多人都吻合。中等身材,浅色头发,中等——”
“您不想查出他是谁吗?”刘易斯站起来,俯身看着莫尔斯,声音里带着不同寻常的愠怒,“我很遗憾这些都不能和您想到的那些天才理论相吻合,但是我们必须得起个头,不是吗?”
有一会儿,莫尔斯没有说话,再度开口的时候,他平静的语气让刘易斯为自己的急躁而感到羞愧。
“你肯定能理解,刘易斯,为什么我希望那具腐烂的尸体不是保罗·默里斯?你明白,如果那是他,恐怕我们最好赶紧开始搜寻,不是吗?
我们最好开始搜寻另一具尸体,我的老朋友——一具十二岁男童的尸体。”同贝尔一样,基德灵顿霍姆巷三号的房东也得了流感,但他还是打着喷嚏欢迎莫尔斯查看他的房子,默里斯离开后,这幢房子租给了一对女儿出生不久的年轻夫妇。
刘易斯敲了几下门,但是没有人应答。“可能出去买东西了。”他坐回警车前排莫尔斯身边的时候,这样说道。
莫尔斯点了点头,茫然地望着四周。这一小片月牙形的居民区始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十几座红砖的半独立式住宅,现在开始显得有些陈旧,木板栅栏的支撑已经腐烂脱落。“告诉我,刘易斯。”他突然说,“你觉得是谁谋杀了约瑟夫斯?”
“我知道这不是多么新奇的想法,长官,但是我必须认真,肯定是这个一无所有的家伙干的。
可能是他准备从献祭盘里偷钱,约瑟夫斯发现了他,就被他捅死了。还有一种可能——”
“约瑟夫斯为什么不大声呼救?”
“他肯定呼救过,长官,如果你还记得。可能无法压过风琴声音。”
“你可能是对的。”莫尔斯说道,认真的样子就像他突然发觉,看待问题最明显的方式未必是错误的方式,“那么劳森呢?是谁杀了他?”
“您比我更了解,长官,大部分的谋杀犯不是自首就是自杀了。劳森自杀了,这一点没什么好怀疑的。”
“但是劳森没有杀害约瑟夫斯,不是吗?你刚才说——”
“我正要说,长官,还有另一种可能。我觉得劳森本人没有杀害约瑟夫斯,但是我觉得他可能要对他的被害负责。”
“是吗?”莫尔斯怀着极大的兴趣望着自己的下属,“我想你最好慢点说,刘易斯。恐怕我完全没有跟上你的想法。”
刘易斯咧嘴一笑,带着些许满足。莫尔斯通常不会跟不上——其实正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