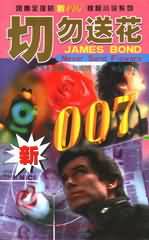切勿送花-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们作了安排。德拉贡波尔告诉他们,要沿着他认为最好的路线走:“这无论如何是风景最优美的路线,走山路,你们首次从上面俯视德拉赫堡最富戏剧性。”
现在他们从一个观景点俯瞰德拉赫堡,这个观景点就在路边,用栅栏隔开,其空间可放下6辆轿车。 他们肩并肩靠在栏杆上,饱览那个峡谷的景色:莱茵河气势雄浑,两岸耸立着突兀峥嵘的石山和墨绿色的冷杉树。
“阴森可怕!”弗莉克皱着眉头说道,“我原以为它像奥兰多的峡谷那样既庄严又优美呢!”
“或者以为像加利福尼亚的峡谷那样深邃雄奇。”
“甚至以为像现在的法国巴黎的峡谷那样美不胜收!”
“我们不走运呀,弗莉克!我认为不会有睡美人住在这条峡谷里。”
就在他们的下方赫然出现一座用灰色岩石建成的庞大的四方形城堡,它依山而建,与山并峙。邦德原先以为德拉赫堡可能只是用一个大院子围起来的;然而,它显然是用大约10英尺厚的雉堞墙围起来的,雉堪墙内石路纵横交错,里面的建筑物原先有一段时间是用红灰色的石板顶的。那些窗子表明那座庞大的建筑至少有五层楼高,邦德猜想,房间一定也很大。在雉堞墙的每个角都矗立着一个圆型的塔楼,拱卫着城墙。甚至从远处望去都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塔楼至少有两三间很大的房间那么大。
在那座主楼西北端矗立着一座坚固的方塔,其形状像在英国教堂上看见的诺曼时期的许多方塔一样,只是体积要大得多;塔顶四周排列着雉堞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由塔顶四周望去,可眺望数英里远。
一眼看去,整座城堡仿佛是从山岩中长出来的,但是从观景点望下去就发现这显然是不正确的。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堵厚实的城墙从山岩的背后拔地而起,把一座位于山岩中的大花园围了起来。弗莉克和邦德可看见大大小小的石路,各种颜色的闪光,树丛,甚至还可以看见使那个并不理想的环境美化的树木和喷泉。
“她是不是在这里栽培那些玫瑰花的?”弗莉克把头靠在他的肩上,他转过头来轻轻吻了一吻她的前额,闻到了她秀发上新鲜香水的芬芳味道。一时,他的心如脱缰野马,想到了其他地方。他曾两次发誓永远再也不与女人胡混,因为与她们胡混总是导致灾难。然而弗莉克与其他女人不大一样。她无求于他而只付出情爱。他们彼此之间从来没有过山盟海誓,也没有过天长地久之类的承诺。他紧紧拥抱她一下,然后两人一起慢慢走回到小轿车那儿。
沿着大路行驶一公里左右他们碰到了一个用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和英语五种语言书写的布告版:“私人用路,只通往德拉赫堡。未经允许,不得上路。”再往前走不远,出现一条支路,那里也有同样的布告版。他们把车开上这条支路,发现他们朝着河走下坡路,这条路很窄,而且弯弯曲曲,十分危险。走完这段路他们的小轿车就驶入莱茵河畔一个黑黝黝的松树丛中,再拐个弯,那座城堡才巍然屹立在他们的面前。它那像山一样高大的雉堞墙似乎倚在苍穹上——这是浮云飘荡时仰望高大建筑物产生的奇特的幻觉。
“真是叫人不禁要问,建造这些建筑物究竟死了多少人!”弗莉克丝毫不想掩饰自己的敬畏。
“肯定使金字塔的建筑工程自愧不如了!”他把车慢慢开着往前走。路越来越窄,一直通到一座小桥,小桥后面是一个石砌的圆形场地,圆形场地的正后方就是两扇高约30英尺的拱形大门。那两扇拱门已经很古老,但是它们巨大的黄铜铰链和附件却闪闪发光,好像有人定时把它们磨亮似的;门板本身由于漆上某种木头防腐剂也是光滑可鉴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竟这么惹人注意?难道你拉动门铃的拉索了?难道伊戈尔来把门推开啦?”弗莉克一边说着话,那两扇拱门就一边开始移动了,门慢慢向里面打开,现出了一个露天的大院子。
“我想他们已经知道我们到了。”邦德慢慢驾车穿过大门,开入院子。院子里停放着两辆小轿车,一辆黑色的默尔克牌小轿车,一辆是豪华型的勒克斯牌小轿车。邦德把自己的车停放在勒克斯牌小轿车的旁边,他们一进去,大门也随即关上。他匆匆看了一眼周围的情况。用作停车的入口处三面酷似古典的修道院的回廊,完全是拱形结构,有滴水嘴。迎面的那堵墙也没有回廊,回廊把墙一分为二,在中间穿过,回廊里有条长长的石阶通上另一扇很大的门。这扇门的样子倒隐约显示了维多利亚时期建筑的风格,全用彩色玻璃做嵌板。
他们刚从车里钻出来,一位身穿燕尾服的男管家和两个身穿仆役号衣、年纪较轻的男人就从门里走出来。那两个仆役连忙打开车上的行李箱,把行李拿了出来,动作像惯偷那么熟练、快捷。
“先生——太太,欢迎光临德拉赫堡!”男管家从讲话的腔调到一举一动,特别是他对手下的那副颐指气使的派头都基本上是英国式的,一言一行都跟现代格格不入,好像倒退了几个世纪似的。
“请往这儿走,主人正在藏书室等你们。”男管家领着他们走进门厅,门厅里有被磨光的木头散发出来的味道。邦德马上注意到装在玻璃柜里的纪念品、高高地蹲在墙上的鹿头装饰和一些油画。那些油画中的人物栩栩如生,一眼看去,会令人疑为特纳的真迹。
男管家领着他们拾阶而上,走完了一段短短的台阶后,沿着两侧挂满画的走廊往前走;那些画中的人比较容易辨认。那些画也是油画,但画上的人哪怕是最漫不经心的人一看就知道是谁,因为他们全是著名的男女演员,有的是很久以前的演员,有的是不久以前的演员,有的则是现在仍活跃在舞台上的演员。邦德从中认出了奥森·韦尔斯、奥利维尔、理查森、吉尔古德、吉米·斯图尔特、约翰·韦恩、门罗和一大群其他的演员。他们的画像是用醒目的颜色绘制的,画中还配有舞台和帷幕。
那条走廊一直通到一个很长的通风的房间;房间里排列着一层层叠起来的装潢美观的皮装书;书是按颜色排列的,使人望着它们便产生一种奇异的幻觉,好像一条彩虹经天而过。在房间的远端有几个很高的铅条窗子,突然一道强光从窗子上射到房里的地面上,好像落在一个早已排列好的图案里似的;一束束亮得令人目眩的光线照在邦德和弗莉克的身上,使他们两人一时目眩眼花;为了保护眼睛,弗莉克只得抬起手遮住眼睛。
照射到他们身上的光线来得快,消失得也快,接着就只剩下通过巨大的窗子射进来的真正的阳光。
“欢迎,邦德先生,也欢迎你,冯·格鲁塞小姐。”这声音与众不同,只有一点点戴维·德拉贡波尔真正声音的痕迹。
他站在一个地球仪的后面,表情像一个专业演员在演戏,他一只手摸着地球仪,另一只手放在胸脯上。这时他变成了一个迥然不同的人,难以辨认,满头又长又黑的头发披在肩上,然而,实际上人人都知道戴维的头发是浅黄色的,近乎沙色的。以往显得那么高贵的鼻子现在变成了鹰钩鼻,使他显得像只啄食同类的猛禽。深陷的眼睛像燃烧的煤炭一样闪闪发光;他的嘴唇变成奇形怪状的曲线,使嘴唇两旁像有两个“S” 嵌在脸上。他上身穿着黑色的紧身衣,下身穿着黑色的紧身裤。紧身衣的开叉处用金线镶边,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锭,金链上有一枚状似野猪的巨大纪念章。
放在地球仪上的那只手与其说是只手,不如说是只爪,指甲又长又弯又污秽,令人恶心;镶着宝石的几枚金戒指光芒四射,他那瘦骨嶙嶙的手指似乎不堪重负。
“在这里看见你们真是太好了。”他现在的声音又陌生得很了。“我是谁你们还不知道吧!我是格洛斯特的理查,英格兰的理查三世就是我!”
“疯狗狂吠!”邦德轻声地说,但其声音显然还不够轻。
“汪汪,汪汪!”那个怪物学着狗吠,紧接着大笑起来,那格格的可怕笑声使邦德毛发耸然,使弗莉克害怕得紧紧抓住邦德的手,指甲都扎进他的肉里了。
“理查复活了!”那怪物尖叫着。叫完他就敲打了一下地球仪,地球仪开始飞快旋转,每转一圈就重重地“喀嚓”一响。
第十节 德拉赫堡
格格的刺耳的笑声渐渐变成了嘻嘻的柔和的笑声。那个怪物的双手老在动,不时合在一起,长爪般的手指一次又一次地互相抓住手腕,仿佛要把皮肤,骨头和指甲都撕下来。现在,一只手的指尖拎着乳白色的胶质薄手套,而另一只手则伸上去把那长长的黑发扯了下来。整个身躯突然在弗莉克和邦德的眼前变了样,身躯直立起来,魔术般在增高。
“啊!对不起,但我不得不这样表演一番。你们该看看自己的脸,竟吓成这个样子,脸都变了!我的名字叫戴维·德拉贡波尔。冯·格鲁塞小姐和邦德先生,欢迎你们光临德拉赫堡。”
他用手摆弄一下鼻子,把那个用油灰做成的化装品扯下来,那个化装品的形状像奇怪的鸟喙,有点弯曲。这么一摆弄,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俨然是德拉贡波尔本人了。甚至声音也恢复正常了。
“你们明白了吧!霍特①自以为是个画家,因此我正在摆好姿势让她画,她认为,把我扮演得最成功的角色画成油画,将来放在博物馆的一个展览室时,形象一定很好看。她这个观点我不敢苟同。霍特,来,来,来,见见咱们的稀客。”
①霍特是梅芙·霍顿的昵称,——译者
他们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这才发现有个女人坐在有点像壁龛的小房间里的画架的后面;那个小房间位于左边的一堵很长的墙壁的一侧;墙壁旁边摞着许多书。她放下调色板,姿态优美地款款站起来——她是个稳重的女主人;她身穿被颜料弄得斑斑点点的牛仔裤和T恤衫, 衣前印着“加油干!生活不是彩排。”她微笑着姗姗向他们走来,伸出一只手让他们去吻或者握。
“梅芙·霍顿。”她自我介绍道。“我在电话里已经跟你说过了,邦德先生。”
她泰然自若,那双漆黑的大眼睛怔怔地盯着邦德,似乎要使他情不自禁地把衣服脱下来。 她身材颀长,几乎有6英尺高;她身躯像舞蹈演员一样苗条、灵活;五官匀称,皮肤光洁,具有道地的爱尔兰姑娘的特色。“要是我知道你长得这么英俊,在电话上会跟你谈久一点的……”
“得啦,得啦!霍特,别说那么多奉承话了!”除了紧身衣和紧身裤以外,德拉贡波尔完全可以认得出来了;他用手指梳着他那又长又密的稻草色的头发,露出了那张曾使千千万万人遐思的俊脸;他是一位能随心所欲使自己变成任何角色的名演员。“我家有着爱尔兰人的血统,这一点你们可能知道吧!”他向他们两人迷人地微笑,洋溢着明显的领袖人物感人的超凡魅力。“霍特一言一行都完全模仿爱尔兰女子。人人都叫她霍特,从不叫她梅芙。”
梅芙·霍顿听了这番话后,不耐烦地“啧”了一声,其意思介乎“别说了”与“讨厌”之间。接着她转过身朝着弗莉克,而德拉贡波尔则挽着邦德的胳膊,引着他离开那两个妇女。他小声地说:“在这些事情上我总是力图做得细致。现在这年月,说话不得不直率点。关于睡觉问题该怎么安排我还拿不准。邦德先生……”
“叫我詹姆斯好了!”他正试图尽可能多了解一些情况,从霍特为什么明显地献媚讨好,到书架周围和高大的窗子前面隐藏的照明设备都要了解清楚。他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他们进入藏书室时眼睛几乎被眩目的光线弄瞎了,原来窗帘上面的框架里整齐地隐藏着两排小小的聚光灯,一排向下照射,另一排集中照射藏书室的门口。
“詹姆斯,我要知道的是……好吧,直话直说,睡觉的安排……你与冯·格鲁塞小塞小姐究竟仅仅是同事,还是像他们说的那样是一对情人?”
“是情人,戴维——我可以叫你戴维吗?可以吧?”
“当然可以!问清楚我就高兴了,因为我现在可以让你俩住在东边塔楼的房子里了。那通常是用作新婚洞房的正规套间。霍特曾在那儿度过她蜜月的大部分时间。唉,可怜的亲爱的人儿呀……”
“我想,霍顿夫人现在守寡了,是不是?”
德拉贡波尔无可奈何地向他苦笑一下。“是的,说起来真叫人伤心!她的丈夫是,啊,难说得很。你们要是有时间,我以后也许可以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告诉你们。”他转过身朝向那两个女人,他们在喋喋不休地闲聊,似乎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