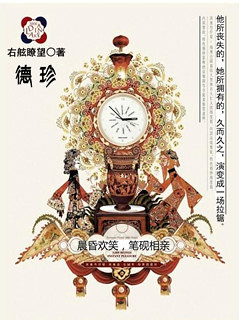德珍-第2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谢仙见他沉默不答,火气越显,不由提高了声音道:“我知道卯卯的事着实是为难你了,但是!德珍的事你至少要对我说清楚,要不是今天有人告诉我,你打算瞒我到几时?!”
谢仙越想越气,她是多么中意德珍这个儿媳妇,只差提着礼单上门提亲了!他这个做儿子的倒好,竟然将德珍和卯卯那桩“婚事”的关系一笔带过,到头来竟是她剃头担子一头热,白费了这么多心思,空欢喜了一场!
“为什么不说话?!”谢仙怒气冲冲的瞪着他。
“您要我说什么?”他语气十分平静,好像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一样。
“说什么?当然是保证立即收手啊!”谢仙差点大叫。
可是他却露出一个疑惑的眼神。
谢仙提起水杯喝了一口压压火气,儿子是她肚子里生的,从小养到大,从他蹒跚学步,到会跑会跳,无一不被她看在眼里,她了解他就像清楚自己的每一块骨骼那样!所以当她从别人口中得知他刻意隐瞒了德珍和卯卯那桩婚事的目的,她很快就明白了各种用意,她以为商场诡谲陶冶不出多么高尚的情操倒也符合常理,可她实在太喜欢德珍了,她甚至希望德珍一辈子也不要做噩梦,而她的儿子却为了达成目的,顺着她的意思去接近德珍!而她,竟然是将事情推到这般境地的始作俑者!!
“不管你之前做了多少铺垫!都给我立即收手!我不允许你再靠近德珍!”
聪明如他,因为这莫名其妙的喝令,也难以懂得母亲这份突如其来的恶意。他,到底做错了什么?
谢仙捶了一下沙发,蹙眉悔不当初,“卯卯的事固然很重要,可是你明明知道岑小姐是德珍的妹妹,为什么不与我讲?我知道你聪明,可是这路终究是走歪了啊!德珍那么好,你怎么忍心伤害她呢?”
“我……伤害她?”他震惊于这样的说辞,总算明白了这顿责骂的由来。
“岑家实在不肯我们也只好算了,你也不能用德珍去逼他们家啊,到底是谁教你用的这样险恶的法子?啊!”谢仙说着说着就捶着心肝哭了起来,岑家为了保住德珍,或许真的会让步交出黎阑,可是,这种手段比用钱买更肮脏不是吗?
她现在简直是气到不行,她亲手教出来的儿子,竟然连人心也玩弄!而她还是经由别人提醒才得知的这一点,天知道当她听说的那一瞬她有多难堪,好似这大半辈子都白活了一样!
他……真的差点冷笑出声。
因为用心险恶的小人,因为自己的掉以轻心,更因为母亲的先入为主,他从出生到现在,从未有一刻感到如此屈辱不堪。生性的骄傲自负在他少年时总被同侪指指点点,他固执的认为,不必要的人也就不必 思去经营,去哄。带着这样的脾性,十六岁独自去香港考试,十七岁赴美留学,可是在美国,他却因他的冷漠固执和傲慢交到了不少朋友,傲慢本就是天才的后缀,就应该形影不离不是吗?
然而,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从母亲手里体尝挫败的滋味了,这个声称最了解他的生他养他之人,往往是这个世上最不信任他的人。
简直是荒诞至极,她怎么会听信外人的几句话,就认定他满手肮脏呢?
他不高尚,可这样的罪责强加在他身上,他那颗卑鄙的心也还是不能顺应她的想法去接受啊……
未来一场荒诞,不明不白(二)
他不是太在意这些。
但人都逃脱不了某些根源性的牵绊,这些根深蒂固的东西,往往会使他变成什么样的人。而在这桩机缘巧合中,只因有了那个让人无法拒绝的女人,常年对他紧闭的大门才对他打开一道缝隙,透出一点点光亮,施舍似的。
而今看来,他和他的母亲之间只怕隔了一万代,他屈尊将就她选择的人,在她眼里不过是为卯卯的事找了一个充分的理由,“真相”被拆穿后,她仿佛受到了莫大的耻辱,神情自厌,眼尾的细纹里都藏匿着深奥可畏。
但他是个有尊严的人,他不解释。
次日,她来了短讯,简单明扼地写了她爷爷的病情,末了一句“接下来的一阵或许不方便见面,见谅”,他应该为她刻意的疏离不加掩饰的表现出自己的气急败坏的,那样才像她的情人。
可是,手指在屏幕上滞留许久,只有一个字,一个句点:“好。”
心危险的 着的时候,周子康领着客人进来,收好落寞,英俊的脸上重新换上运筹帷幄的精明表情,伸出手与客人交握。
他还没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既然有人背后拿着明晃晃的刀子通过来,那也别怪他闪电式的报复了。
此次美国之行还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他是个行商之人,眼光,钱,魄力,人脉,一样不缺。他与科达明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是二代,科达明是三代。
世人都说,“富不过三代”,虽然有些耸人听闻,却并非空穴来风。科达明与生俱来的自信,通常很吸引人,但用在他身上却不见得管用,尤其是这一招看似聪明却百害无一利的“险棋”,他只能说科达明树错了敌。
一来,他这个人特别讨厌被人威胁,二来,他特别讨厌因为女人被威胁,三来,哪怕他是妈妈不得宠的儿子,也不见得乐意自己母亲被人当枪使!
此仇,必报!
接下来几天,周子康和箫尘几乎没有闲下来的时刻,夜间会议时常开到半夜三点,期间仲寅帛去香港出差,那边的负责人在酒店套房主持了会议,仲寅帛在看a、b两组方案的同时,声音香脆的女博士用英文介绍了会议大纲,她的英文语速很快,每个音都仿佛会被咬的粉碎,极具攻击力和提神效果。
这边的会议室里都是连夜加班的一群人,一半以上昏昏欲睡,另一半则抱着咖啡杯昏昏欲睡,箫尘掐了一把大腿肉,强大起精神,努力把背挺得笔直。
就在不久以前,他的大前辈周子康对他说“我们的好日子结束了”的时候,他只是冷笑一声,心里想前辈永远这么夸张。
就在三天前,公司突然出现了两个临时搭建的团队,分别对付两个不同的案子,但没有实施隔离,而是同时进行。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变懒,因为智力和逻辑都不足以应对生活中的种种突变,有些人一辈子只能专注的做一件事,喜欢一个人,活得很成功。而有些人同样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事,喜欢一个人,却籍籍无名一生。有些人一辈子把所有能做的事都做了,什么也没做好。而有些人同样做遍了你能想象的事,却每一样都做到了顶尖。
箫尘以为,仲寅帛是最后那种人。
这种人,很可怕。
一个公司同时进行多个案子并不是什么难事,但如果这个案子大到足以改变一座城市的地标,同时牵涉到了交通、市政、银行、以及本市地产公司排名顺序,就不是普通人能左右得了成败了。
a、b两组组员刚聚头的一小时,纷纷都有些莫名,一个小时后,听完周子康发表的未来一年规划,两组人马悉数倒抽了一口冷气,觉得老板疯了。
他们都清楚仲寅帛不是什么好人,也知道他是个有野心的男人,但目前的这两个案子,吞下一个都有些吃力,何况是两个一起吞?!
他还太年轻。组员们一部分表示失望,但也有一部分群情激昂,跃跃欲试。
三个小时后,各组分工已经下来了,然后全公司上下开启了加班加点暗无天日的日子。各部门负责人都忙得没影,箫尘甚至在公司男洗手间里和几个负责人站着开了半小时的口头会议。
太累了。
年轻人看着银幕角落,坐在浓稠暗影里的那个男人,蹙眉腹诽:原来老板情变是这么可怕的事啊……
箫尘可不会相信周子康那一套,仲寅帛的“女伴”虽然都是识趣的女人,拿钱办事,绝不拖泥带水,但若说德珍也在“女伴”之列,那就有些夸张了。
他与德珍在北京相处过一阵,在她眼里,只要她往那里一站,就足以区别十公里以内的任何一个女人。她总是带着一种宠辱不惊的神色,而现在的年轻女子与她相比总像是个随时敞开的衣橱,鲜艳亮丽的片段在里面一览无余,多看一眼都会失去好奇。
但德珍不一样,她是照在窗门上的剪影,走走停停,有说有笑,总想叫人捅破窗户纸将她看个清楚,没等你伸出手指,她倒落落大方的说了:“我得去别处了。”
她对人构成的一种吸引是若即若离,也许会有暂时将她遗忘的时候,而一旦思及,思念却变得异常强烈。
早在停车场那一眼,箫尘已经知道这个男人对这个女人复杂的情绪,他俩倒也没有不般配的,尤其前一阵他时常推掉不需亲行的交际,撇开司机独自驾车出去,足以窥见他对那个女人的狂热。
然而,他结束美国之行后,突然变得异常冷淡,甚至更换了手机号码。
情变。是箫尘唯一能想到的可能。
未来一场荒诞,不明不白(三)
岑润荩这回是险中求生,股骨裂,胫骨骨裂,上臂骨折,虽然伤了三处,好歹性命无忧,连慧珠赶到医院见到他的第一句话都是如释重负的一句“谢天谢地”。
她可不是要谢天又谢地麽,要不是老爷子下意识护犊,礼让会怎么样就无从得知了。
蘸白不在家,爷爷为了让他安心陪薰爱待产,甚至说了不能叫他知道的话,淳中有公司的事情要做,尽管孝心在,但在医院也不能分担父亲的痛苦,也被老爷子一句话给打发走了。
“有德珍在就好。”
淳中看看自己的稳重大方的侄女,确实比他在这儿干杵着强多了,顿时放心了许多。慧珠要照顾家里的大小事宜,得了闲才会来医院。倒是礼让,因为差点丢了小命,又或者是最喜欢的人因为他而受了伤,心有余悸的同时又很抱歉,搂着德珍的脖子哭了好一阵,哽咽地说不出话来。
他年纪还太小,有黎阑车祸在先,这次换成了爷爷,他真的有些受不了了。
德珍很清楚,因为血缘,这种来自灵魂的颤栗总能引发一场没来由的嚎啕大哭,站在做姐姐的立场上,她只能温言软语地安慰着敏感多思的小弟弟。
至于上天为什么要折磨她最亲最爱的人,折磨她的良心,她想不通,也没有闲暇去想,她只希望爷爷可以快点好起来。
人一旦走到了自己无法左右的境地,首先想到的一件事是求神拜佛。因而当慧珠提出要去庙里做善事后,她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爷爷见她在医院呆了两三天寸步不离,又知道强行劝说她是不会成功的,因而慧珠想出这么笨的法子来,他倒松了一口气。
德珍前脚才走,稚巧后脚就到了。因为今天连着午休下午有一节自习课和体育课,她晚上要写功课不能来医院,也怕影响爷爷休息,所以这天中午特意跟老师请了下午不要紧的课的假,背着书包来医院了。
老爷子的病房是个骨科单间,透过玻璃可以看见病房里没有其他人,轻轻推开门,立即能闻到淡淡的药香,靠近病床就有些辛辣冲鼻,但稚巧没有一点嫌弃,只是看着爷爷高高肿起的手臂发了一会儿呆。
岑家老爷子是能意识到床前坐了人的,德珍刚走,他极想换个身,因为背上有些难受,可他只有一只手一只脚能动,腰又伤了,出于自尊又没叫护士来帮忙,自己咬牙折腾了一会儿,失败了。
他的同龄人中有许多与他抱怨过衰老的可怕,初时不以为意,等真的轮到了他身上,他才品尝出了各中滋味,正沮丧间,稚巧背着书包进来了。
这个异姓孙女在他眼里是个超乎寻常冷静而冷漠的孩子,过分聪颖机智,倒不像是他们岑家女子一贯的“愚钝”,但并不惹人讨厌,反而成长的过程摸索出了自己的轨迹,让人很省心。
病房里安静了片刻,药香和花香糅杂在一起,叫人徒生无力,老人家刚在心中叹息一声,就听见了隐隐的抽泣,紧接着冰凉柔软的手指握住了他苍老的手,捧在手心里,非常克制,又非常难过的哭起来,她似乎死死咬着嘴唇不出声,只是肩膀剧烈的抖动着。
不是不惊讶,这个少女因为出身与环境,并未享受到多少人间喜乐,她不爱笑也似乎成了必然,但岑润荩也不曾见过她哭。他极想伸手摸摸她的头安慰安慰她,可是又觉得林中的小鹿虽然稚美,却不能经受任何一点惊吓,尤其是他这个孙女这么酷,若是叫她害羞了尴尬了,只怕她下次便不会再将情绪激烈的表达给他了。
罢了,人生如此魔幻,他难道还演不了一场沉默的戏麽?
稚巧哭得眼睛都红了,打湿了一小片床单,泪痕干辣,好在爷爷还在午睡没有醒,她脱了书包吸了吸鼻子,出门去洗手间。
加湿器呼呼响了一阵,岑润荩这才睁开眼皮,对着天花板长舒一口气,手指触到那片湿热的床单,露出一记虚无的笑意,眼底写满了欣慰。稚巧不同于德珍与黎阑,尤其是